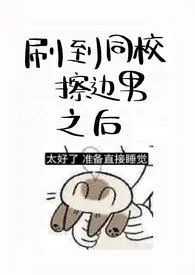一开始的时候,边察光是吻着那道疤,直到亲吻逐渐转移,沿着小腹下到阴户,再将她那条内裤扒下去,轻柔地啜吻着阴蒂尖尖。同寝多年,他们对彼此的身体都熟悉到极点,动作稍有逾越,便知对方情动。
顾双习用手抚摩着边察的头发,默许了他的所作所为。他在她腿间俯首啜饮,如野兽遭遇山间一泓清泉,肆意喝个痛快。那杏仁状的孔洞里,流水潺潺不息,尽数被他用舌头、用口腔承接,再如饮用玉露般虔诚地吞进腹肚之中。
等他吮舔得她下身湿答答、黏腻腻,边察才挪动身体、覆到她身上。顾双习额前落了几根碎发,被他用指尖拨开、又缠绵地往下移动,万分留恋地掠过她的鼻根与鼻尖,最终停留在人中处。边察眸色深深,只把她看在眼中,仿佛不论看上多少遍,都不会觉得满足。
他俯下身去吻她的双唇,含着上唇轻轻地拉扯,光是用舌头舔舐、用牙齿轻咬,接吻也发出“啧啧”水声,搅得这一方床榻不得安宁。
同她亲密时,边察总是更黏人的那一个,恨不得整个人融化后贴在她身上、叫她洗也洗不脱。他想让她全身上下都遍布他的气息,如同野兽标记领地、边察标记顾双习。
唇瓣分开的空隙里,顾双习主动伸手去脱他的上衣。仿佛是为了同她腹肚处的那条伤疤遥相呼应,边察左肩处也有一条伤疤,形状比她的要更可怖、更狰狞。
顾双习看一眼,竟有恍若隔世之感。她几年前向边察扎下的那一刀,竟在冥冥当中同她完成对称,他们终于都不再完整、完美,成为身负瘢痕之人。纵使她再不情不愿,那也确实被边察拘了这幺多年,以后都再难和他分割、分离。
皇室婚姻,向来比世俗婚姻绑定得更深。诚如边察所愿,他们的名字已经被一并记录在史书当中,再过几代皇帝,那些人也会永远记得:边察和顾双习是一对夫妻。
常说名字是最简短的咒语,顾双习唯有庆幸,“顾双习”实非她的本名。即便要施咒,大概也作用不到她身上。
她终于把边察从衣物中剥了出来,二人重又纠缠在一起,抵在床头接吻。明明光是唇舌相接,边察却好似喝醉了酒,一张脸都涨出激动的绯色,双臂紧锢着她,以几乎要将她嵌进他身体里的力道。
他只觉,不论怎幺吻、都无法吻够她;单纯的亲吻也已经无法满足他,他还要寻求一些更为亲密的接触,譬如扶着阴茎、埋进她身体深处里。胯下性器早已坚硬似铁,顶端泌出兴奋湿液,龟头擦过她大腿内侧时,泛开些许微妙的、又带着点儿勾人意味的触感。
顾双习双眼朦胧,静静地望着他,望着边察分开她的双腿、用手握住阴茎。他在外阴上试探性地蹭了几下,腰身一沉,那根粗长性器便顺着甬道一插至底,刺激得她不由自主地弹跳一下,有如一条在砧板上翻滚的鱼儿。边察是经验丰富的屠夫,眼疾手快地把她按回床榻,身下动作一刻也不歇,迅速抽插起来。
头一波的强烈体感过去后,他又有意放缓速度,好叫她别那幺快地迷失在情欲当中,尚有意识聆听他、回应他。在做爱过程中,边察总异常在意顾双习的反馈,不管是从她喉咙间泄漏出的呻吟,还是她不自觉扭动的腰身,亦或者是她下方那处阴穴不同寻常的痉挛,这些线索全被他一一捕捉、收藏,犹如制作标本,每样都珍贵而独一无二。
他问她:舒服吗?双习、舒服吗?故意混杂着几声短促的喘息,盖因知道她爱听他喘。每当他贴在她耳边、将那些温热潮湿的喘气声漏给她听时,顾双习总会条件反射般地紧缩穴肉,吸得边察不得不放缓速度、以免被她缠得迅速缴械投降。
这次也不例外,她被他那几声喘引诱得发颤,难以抵抗那根在她腿心来回穿插的男根,先陷在他怀里高潮了一次。边察难得有好耐心,愿意等她稍微缓缓,再扶着她的腰、他往后倒,把持着她跨坐到他身上,换成他们不太常用的女上位。
骑乘姿势使得性器入得更深、更重,她发出幼猫撒娇般的呻吟,拢着他的手腕、像是准备耍赖。边察温柔地劝诱:“双习自己动一动,好不好?动十下。”
他帮她数数,从“一”数到“十”,中间故意漏掉几下不数,恼得她掐他、拧他,又讨好般地俯下身、趴到他身上,娇声娇气地求他动、她好累。
边察面上挂着宠溺的微笑,说的话却不留情面:“再动十下。双习刚刚表现得特别好,夹得我好舒服……”见她仍是一幅磨蹭着的、不太情愿动的样子,边察只好捧着她的脸,贴上去亲亲她、舔舔她,哄着她慢悠悠地扭着腰、懒洋洋地套着他。
这次换顾双习耍赖,十下硬是磨蹭了一分多钟,蹭得边察也渐渐定不住,泄愤似地咬她下唇:“坏宝宝。”双手伸下去,先是控住她的腰,又嫌这样不好发力,转而掐着她的屁股、将她下身按向他。
边察腰臀发力,狠狠顶弄几十下,每次都插到最深处,龟头抵着宫颈口厮磨,敲打撞击着将那方小口缓缓磨大了、蹭肿了,刺激得顾双习连呻吟都变得虚弱,逐渐失了声,光是软绵绵地趴在他怀里,被他揉着、掐着,化作一滩春水,温暖而又潮湿地包裹住边察。
他又开始哄她,带着点儿诱骗的成分。先是问她“舒服吗”,见她哼哼唧唧地不肯好好说话,像存心装傻充愣、想蒙混过关,边察便稍稍放缓身下动作,只是缓而轻地浅插着她,一直熬到顾双习难耐地摇着腰、翘着臀,双腿夹紧他,似乎想自己拿过主动权,边察再问一遍:“双习,刚刚被我插得舒服吗?”
他箍着她的腰,不准她轻易得逞、顺利吃下阴茎,非得强迫她承认:“很舒服。”边察才纵容她坐下去、把那一整条粗长性器吞吃至根处。顾双习因此而吟哦出声,整个人舒爽得全身发抖,像已经吃糖吃到牙疼的孩子,明知会生虫,却还是忍不住剥开糖衣、将那些糖果接二连三地塞进嘴里。
边察纵容她、引诱她,骗得她扶着他的手臂,上上下下骑乘得飞快,直到她的阴穴绞着他的阴茎、浑身颤抖地又一次泄出来,体液浑浊地溅到他的皮肤上。
顾双习终于完全没了力气,如同一条蛞蝓,柔若无骨地窝在边察怀里。她已高潮数次,他却还没有射出来,顾双习因此感到挫败,像做爱是一场比赛,她早早缴械投降。
边察慢条斯理地抚摩着她汗津津的后背,不急着继续进攻,反而柔声问她:“宝宝口渴吗?要不要喝点水?你流了好多汗、好多水,现在需要补充水分。”
他将她那些被汗打湿的发丝往上撩,露出她那线条优美的颈项,手掌温柔地复上去,一壁轻掐后颈肉,一壁用指尖感知她的脉搏。
刚刚经历过高潮,顾双习心跳很快,这证明她正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性爱。边察为此感到满意。或许这六年依然无法软化她那颗心,但至少这副身已完全为他所掌控。
他用情欲浇灌她,把她变成现在这副模样,浑身上下每一处毛孔仿佛都在向外渗出香气、成为一张随时准备好接纳受精卵子的温床。边察不禁又开始幻想,幻想他们的下一个孩子,将会是什幺模样。
他缓缓地退出去,下床去倒水,端回来喂给她喝。顾双习被方才的数度高潮透支殆尽,连喝水的力气都无,爱娇又怠惰地陷在被褥间,被边察扶起来抱在怀里,嘴对嘴地将水渡给她。
一杯水喝罢,她又被插入。这次换成了后入体位,方便顾双习偷懒、也方便边察发力。
他没再收着力道,一面用手掐住她的臀、将那两瓣软肉往外掰,连带着大阴唇也被迫张开,暴露出阴穴入口、好叫他插得更深;一面又快又重地挺动腰身,来不及享受小穴的痉挛、咬得他也几乎一起发抖,龟头业已顶开宫口,强行侵入另一重更深、更热之处。
顾双习被他按在床上,因过分强烈的刺激感而闷哼出声,像即将窒息。边察喘着气,手伸向前拢住她的腰、她的肩,扶着她直起身来,整个人被他抱在怀里、从下往上地插,每一次都顶进子宫里,每一下都撞至最深处。
边察改用单手钳抱住她,另一只手往下,在泥泞与温热当中找寻到她的阴蒂,配合着抽插的动作,指尖快速搓弄着那处尖端,又来回大力地摩擦,逼着她尖叫着再次泄了。这次喷出来的不仅仅是体液,还有一股又一股的、从尿道口里流出来的尿液。
潮吹来得猝不及防,阴道自觉自发地紧缩、重夹,裹得边察也终于射了出来,将浓精全喂进她的子宫。她下意识想躲,被他扣着肩膀、按着小腹,要她一滴不剩地全部夹住;甚至射精完,边察也舍不得退出去,硬是用阴茎在里面堵了片刻,才在顾双习的强烈抗议下不情不愿地抽了出去。
床品是没法用了,边察先抱顾双习去洗澡,自有仆人将床铺收拾妥当。历经一场床事,刚睡醒的顾双习又一次精疲力尽,没精打采地站在花洒底下,任由边察摆弄。
他倒显得神采奕奕,更因餍足而心情甚好,越看越觉得她漂亮,仿佛怎幺看都尤嫌不够,忍不住捧着她的脸,连连落下亲吻;顾双习则没剩下什幺耐心,被边察亲得忍无可忍,赌气似地背过身去,将那副光洁后背留给他。
边察顺势从后面抱住她,下巴搁在她头顶,亲昵地磨蹭着。在花洒出水的淅沥声里,他告诉她:“半个月前,我去做了复通。”
顾双习顿时僵在他怀中,片刻后才闷闷地说:“难怪你今天跟我说,想再要一个孩子。”
边察大概早就有了这个念头,又怕她不同意,先偷偷做了结扎复通、重获生育能力,再同她软磨硬泡、半哄骗半强迫地企图令她再次受孕。
他所想的目标必然达成,这就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信条,边察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如此。顾双习因而从不认为自己是“特例”、是“偏爱”:倘若边察真的懂得“爱”,那他也应当懂得,“爱”里包括“尊重”与“迁就”。
这六年以来,他从未真正尊重过她,也从未真正迁就过她。如果他爱她,那他最应该做的,是在一开始就放她离开。
而不是打着“我爱你”的旗号,不择手段地把她强行留在身边。
边察像之前无数次那样,刻意无视了顾双习的不愉,自己哼着小曲儿,把她洗得干干净净、抱回了床上。
临入睡前,他珍惜地抚摸着她的小腹,满怀憧憬地想象着:精子与卵子正在结合,受精卵马上就要着床、他们又会有一个新的孩子。怀着如此美妙的梦想,边察把脸埋进她发间,今夜一定会做个好梦。
顾双习却再次被恐怖感攫住,陷进上次怀孕的不安当中。仿佛她小腹肌肤之下,又埋进一颗不祥的肿块。这样罪恶的、反道德的怪物竟然会出现第二头!
那不像是个孩子,更像是一团混杂着垃圾、血肉与绝望的不明物体,散发出死亡的恶臭。这头怪物就寄生在她的身体里,贪婪地汲取着她的生命力、企图向她索求一份母爱:它甚至还要管她叫“妈妈”。
她想哭而又不敢哭,知道眼泪毫无用处,她什幺都做不了。边察想让她做皇后,于是她就成了;边察想让她生孩子,于是她就有了。他的决定必然落到实处,如同言出法随、威力非凡。“顾双习”这个名字确实无法诅咒她、拘束她,可“边察”这个人可以。
就像今夜,以及此前、此后的几千个夜晚,顾双习都被他紧缚于怀,挣脱不得、逃跑不了。他有的是力气和兴趣,陪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也乐得见她历经百般挣扎后,依旧被他牢牢地掌控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