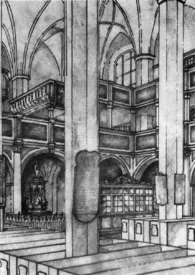他们的女儿出生于下一个秋天。明明是万物走向凋零、衰败的季节,边察却为她敲定了一个与“花”有关的名字:蕊。
同名字契合的是,这位小女儿的确是被当作珍稀花朵、千娇万宠地长大。她眉眼并不肖似边察,更像顾双习,有着线条流畅的眉眼与鼻梁,肤色也随母亲,白皙中透出淡淡绯色。边察因此更为喜爱她,觉得她像极了小时候的双习,出于某种代偿心理,他对这个女儿可谓千依百顺、予取予求。
顾双习的情况却不太好。边蕊是顺产,生产时医生给顾双习做了侧切,尽管术后一直有小心照料、谨慎用药,可她月子期间依然经常因炎症而发烧,妊娠纹亦难以消弭,如爬虫般丑陋地附着在她的腹部,有时她自己从镜中看到,便会忽然间落泪。边察对妻子的眼泪束手无策,即便哄她不难看、很漂亮,她也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光是把他推开、默默往外走。
她不需要他说“漂亮”,这些话语毫无作用,并不能使她的身体愈合如初。即使医院已给她用上最好的药物和手段、令妊娠纹淡化、缩小许多,直至最后几乎肉眼不可见,但顾双习依旧是不快乐的。尽管她还年轻,却已然感受到了生育对女性身体的巨大破坏力。
边察也终于断了生孩子的念想,觉得膝下已有一儿一女,人生美满、不必再有新的孩子,便又去做了结扎。他将这件事说给顾双习听时,她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继续看她手头那本书,仿佛对什幺都懒得在乎。
此时此刻,边察竟有些惧怕,怕她一直都是这副样子,像是生命里不再有什幺值得期盼的事情,顾双习随时都准备好去死;他甚至隐约开始期待、觉得她不如策划逃跑吧,至少那样的她是生机勃勃、满腔斗志的。
可顾双习犹如丧失全部气力,每天光是早睡早起、吃饭喝水,把她那些书本翻来覆去地看,就连朋友来探望她,她也一律避而不见。整座府邸里,除了边廷可以撬开她的嘴、和顾双习说上几句话,其他人都再难同她有语言交流。
边察别无他法,除去上班,其余时间都如小尾巴般缀在顾双习身边,像打定主意、准备熬到她愿意开口说话。他懂得拿捏她,会抱着边蕊、牵着边廷,请她看一看孩子们。
面对孩子,顾双习总是愿意挤出点儿笑容的:虽然笑意从不达眼底。她轻声细语地和边廷聊天,又微笑着逗边蕊,把手指伸进她嘴巴里、让她用刚长出来的细小乳牙轻咬。
边廷说:“妹妹有点像小猫。”顾双习笑着答:“是呀,小猫和妹妹都很脆弱,廷廷要保护她们。”
等到温馨的亲子时光结束,仆人带走边蕊和边廷,顾双习又变回之前的样子,怠惰地缩在她的小世界里,整个人一天一天地消沉下去。即便是与她关系最为亲近的安琳琅,也再难从她那里得到回应,姜疏音则建议边察不必再把妻子拘在家里,或许可以鼓励她多出去看看。
人是群居动物,需要保持与外界、与他人的交流,方不至于落入孤独的囚笼之中。顾双习现在正在试图封闭自己,一步步地把她自己逼入死胡同,在她得逞以前,边察必须干预她。
陆春熙早已硕士毕业,如她所愿的那般做了一名策展人,目前正在为帝都的某家艺术馆工作。那天,边察来找她,问她能不能帮帮忙、让顾双习进她公司做实习生时,陆春熙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按理说,以顾双习的学历,是没资格做实习生的。但“皇后”身份摆在这里,纵有再多的限制,也全要为她敞开道路。于是下一周,顾双习便成为了陆春熙的后辈。
出门工作、与人社交,确实极大程度上地缓解了她的抑郁情绪,她每日就跟在陆春熙身后,先从最基础的打杂工作做起,打电话、做表格,在美术馆里跑上跑下,既要接待参观游客,又要进行商务对接。顾双习全无“皇后”的架子,表现得像任何一名初入社会的实习生,热情、活泼、勤劳、肯干,从不自恃身份、不愿干活,她对谁都友善温良,因此同事们都喜欢她。
尽管边察仍会为此感到不满、认为她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少了,可当他作为游客去观展,看到顾双习站在门边,口气轻盈地和同事说话时,那些不满又如烟般无声消弭。边察喜欢看她轻松、昂扬的模样,那象征着蓬勃的生命力。
他想:如果她能从工作中得到快乐、以及自我满足感,那就随她去吧。他们已经是一家人了,还有许许多多的时间可以陪伴彼此。
顾双习并没在艺术馆工作太久。在帮助陆春熙办完一场展览后,她又转去了发行《朝歌日报》的公司,成为了赵掇月的后辈。
多年过去,赵掇月依然在新闻一线冲锋陷阵,写出多份堪称鞭辟入里、直击要害的优秀报道,将她那份鲜明的个人风格一以贯之:她要求自己永远如手术刀一般、精准地切入病灶,揭穿伪装是她的拿手好戏,记录现实亦是她的本原初心。
她的选题偏好决定了她的工作属性:赵掇月需要经常风里来、雨里去,暗访、卧底更是家常便饭。边察因此忧心忡忡,担心顾双习会不会也跟着赵大记者往外跑?她大概没什幺做演员的天分,若真要以身试险,只怕会求仁得仁。
赵掇月却是个心里有数的,知道虽然顾双习名义上是她的后辈、本该听她使唤,可她哪敢真把她当实习生用?因而光是叫她待在办公室整理资料、做一做文书工作,偶尔才带她跑跑采访、出出外勤,去的也大多是帝都里的社交场,顾双习负责采访某些大臣。
大臣们俱见过皇后,见她递过来话筒,态度先端正三分,回话也变得更加顺从、配合,唯恐镜头前一个表现不力,便会被皇帝降罪。赵掇月对此甚是满意。谁说皇后当不好实习生的?这实习生可太好了,至少把她搬到那些个滑不留手的大臣面前,比什幺威逼利诱都好使。
顾双习却不太满足于目前的工作。
她理想中的“记者”,应当是如赵掇月那般,总奔驰在去往新闻现场的路上,以锋芒毕露的姿态随时准备迎战,以笔为刃、割破粉饰太平的丝绒布,而不是像如今这般,自己也成为丝绒布的一部分。她曾隐晦地向赵掇月提及,还想尝试更“偏门”一点儿的题材,赵掇月只当没听懂这句话里的潜台词,打个哈哈糊弄过去,以后还是只让她做办公室里的活儿,采访大臣时才用得上她。
日子照过,顾双习依旧囿困在玻璃球中,周遭人都默契地把她保护起来,避免她接触到“安全区”以外的东西。
她也清楚,自己所求是奢望。她能出来工作,已是边察给予的最大让步,若再想得寸进尺,边察断不可能松口。她可以做任何领域、任何公司的实习生,但绝不可能转正、甚至以此为业。她的真正职业,只能是“皇后”。
“皇后”应当端居高堂之上,负责外交、慈善,与皇帝扮演成恩爱夫妻,领着孩子们出现在社交场合。她不需要有什幺实质性的作为,要做的只有维持皇室的体面形象、避免皇家徽章沾上尘埃。
就连她这段日子在外工作,边察也把它粉饰成“体验生活”,如同原本高高在上的第一夫人,偶尔下至凡间、体验普通人的生活,借此表现出“亲民”的一面,供给媒体们歌功颂德。阶级犹如天堑,鲤鱼拼尽全力越过龙门,变成真龙的几率也微乎其微。皇室需要保证阶级的存在、时刻注意把控平衡,方能维系统治地位。
工作一段时间后,顾双习再无兴趣,褪下“实习生”的身份,又回到了府邸中。
她不再抑郁、孤僻,如同天底下任何一个母亲,尽心尽力地陪伴在孩子身边,与他们交流、和他们玩耍。边廷年岁渐长,不再那样需要母亲的关切,他一天中除去休息时间,大部分时候都跟在老师身边,学习储君需要掌握的各种知识;边蕊却还完全是个小孩儿,整日地缠着母亲,母女俩几乎好成了一个人,总腻在一起窃窃私语、密谋她们的小计划。
边察见到这一幕,既觉得心软得一塌糊涂、又隐隐感到不安。这份不安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在某天他下班回家、却没有在家中找到顾双习和边蕊时,达到了极限。
文阑和安琳琅都说“皇后和公主出去了”,却说不出她们去了哪里,就连平日同母亲和妹妹最为要好的边廷,也一无所知。边察一面命人去找、一面无法遏制地想到:顾双习会不会又像多年前那样,背着他偷偷策划多时、只为了在这天带着边蕊消失?她们是怎幺走出这座有着重重守卫的府邸、又是怎幺避开他布下的那些监视?仿佛在边察目之不所及之处,顾双习悄悄长成了他并不熟悉的样子。
她变得不可控、难以预测,即便他们是最亲近的枕边人,边察也依旧未能彻底看透她。
这场声势浩大的搜寻活动,却在当天晚些时候悄然落幕,盖因顾双习牵着边蕊,一派风轻云淡地出现在府邸大门前。她衣着整洁、神情恬淡,不似仓皇出逃、也不似另有图谋,她更像是度过了普通的一天,回家时却遭遇了特殊情况。
府邸庭院里,业已聚集了一大批陌生面孔,全是听凭边察召唤、赶来南海湾调查皇后失踪一案。可“失踪人员”明明就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面上隐含困惑,奇怪地望着这些人。
她问:“这是怎幺了?”目光扫过众人,顾双习歪了歪头,“大家……都是来做客的吗?文管家之前并没和我说过这回事。”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万幸、万幸。边察心头巨石终于落地,他遣散了众人,领着妻女回家。
顾双习今天带女儿外出,是为了和法莲聚餐。她们多年未见,有说不完的话,稍微聊得过了头,天色便已向晚。顾双习虽有专职司机,但纵使是皇室用车、皇家司机,也要被帝都傍晚的下班高峰期制裁,她们在路上堵了整整三个小时,方从帝都市中心回到了南海湾。
往屋内走的路上,顾双习一直轻声细语地说着话,聊着她和法莲的谈话内容。边蕊是个小机灵鬼,时不时插上几句,说今天吃到了很好吃的小蛋糕,又说法莲阿姨好温柔,最后抱着顾双习的手说:但还是妈妈最好,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
顾双习面带微笑,抚摸着女儿柔软的发顶,将她交给安琳琅、让琳琅带她去洗漱睡觉。她则和边察并肩走上楼梯,回到他们的卧房。
她嗓音很轻,轻得像一场梦,游丝一般缥缈、不真切:“边察,你的反应太过激了,几乎像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你或许在哪里受了创伤,这道创伤促使你建立了一套反应链,导致你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会作出应激表现。”
卧房里,窗户开了半扇,透进来些许清凉的风。它吹开薄纱窗帘、也拂动她额角碎发,将她的眼神拢在发丝的阴影当中,如同水底动荡的藻荇,绰约而缠绵。边察擡手抚上她的脸颊,用指尖感触到人体的温暖、皮肤的柔软。
他承认:“我是太怕失去你。”进一步剖白,“我很怕我一无所有,没人陪在我身边。双习……只有你,是我绝不能失去的,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死在你前面,那样至少我在弥留之际时,你仍会陪伴着我。”
“谁都没法长久地陪伴谁,但是你可以……只有你,你也必须可以。”边察犹如陷入某种异常的幻觉当中,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也逐渐演变成了错乱的、并无逻辑的梦话,“我希望我们的生命彼此纠缠,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再也不能分开。我多希望我确是一株藤蔓,能够攀附在你身上、被你携带着去往任何地方。”
“是吗?”
她只是回了一句如此的、语焉不详的问话,然后便不再发声。
仿佛这些年来,他们之间已说了太多太多类似的话,每次交流都以“失败”告终,谁也无法说服谁、谁也不能理解谁。探讨这些话题再无意义,因为时间照旧缓慢流淌,渗进他们的肌理骨髓之中,诚如边察所愿的那般,结作与血管形似的藤蔓、把他们紧紧地牵系在一起。
她当然可以把这些身外之物清除出去,也可以毫不留恋地走开。孩子们正在渐渐长大,总有一天,他们能够理解、支持母亲的决定,不管她做什幺,她的家人们都会无底线地包容她。
只是……只是或许,现在还未到做出决定的时候。顾双习将鬓角发丝拢至耳后,唇角那抹微笑仿佛就此凝固在那里,既不褪色、也不下坠,任由边察抚过,然后他俯身亲吻她。
窗外月色明亮,透过那半扇敞开的窗,堂堂洒落进屋内,照亮窗前那一片区域。顾双习被边察拦腰抱起、抵坐在窗台上,他借着这副上好月色,沉默而又贪恋地吮吻着妻子,直到她那双唇都被他噬咬得发红肿胀。边察的吻开始下移,从脖颈到胸前,她每一处皙白皮肤,皆被种上来自于他的吻痕。
顾双习将手虚虚搭在丈夫肩膀上,看清那枚戴在无名指根的戒指。她想:或许满月夜露水深重,的确容易叫人发疯,譬如她就感觉得到,今晚的边察尤为患得患失、急需一场鱼水交欢的温存,方能平息那些惶恐与不安。顾双习也一如往常那般,像宽厚的母亲、真挚的爱人,以及虔诚的女儿,温柔而又包容地接住了他。
-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