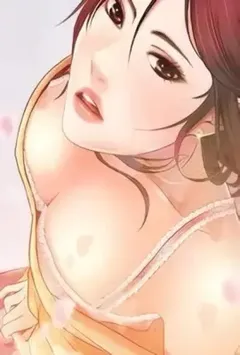做自己?
但末世后,自己到底成了怎样的存在?
颠狂情事暂告一段落,孟凝伏在司空琏宽阔起伏的胸膛上,沉倦困意像潮水涌来,眼睫慢眨,眸里渐渐蒙了水雾。
然而,坠落梦乡后,那问题仍在脑海中徘徊着,使得她连睡觉都皱起了眉心。
柔柔愁绪总堪怜,迷糊间,有温热指腹轻轻揉开了那蹙起的怅意。
她无意识蹭了蹭那指,梦呓着。
“琏…”
腻细腰身上的臂膀收紧,将她往上抱,至她的额贴合颈窝。
终于被好好安置入怀,不用在冷落中独眠。
树影模糊透映入室,声息渐寂,许久后才有无奈的叹息低响,似真非真。
“真会折腾人。”
孟凝没料到起床后多了一道选衣服的程序。
虽说今日是要与素未谋面的亲人相见,总不该隆重至此。
但司空琏讲究起来,便为她准备了一架子或长或短,风格或奢雅或灵动的高定礼裙。
唯一共同之处,就是白色。
深深浅浅的白礼服,配上司空琏那英式剪裁、冷峻优雅的灰色条纹三件套西装,不知情的,都要以为今天是回门省亲了。
权势包围下,末世似乎是不存在的。
孟凝在他期待的目光中,指尖轻划,毫不犹豫地指向了沙发角落的单兵作战服。
利落穿戴整齐后,她的目光才落于被别有深意单独展放在床上的礼服。
柔白生辉,像芍药初绽时的裙摆,转动摇曳时会有水波般粼粼的光。
这是十八岁的她在费尔曼厅独奏时穿的礼服的复刻。
当时助理送来的待选礼裙有几套,孟凝第一眼就看中了这条。
如今真相揭晓,或说不出意料的——又是司空琏的手笔。
孟凝本以为他在演奏那晚匿名送来的量词为束,实则堆满后台的O\'Hara白玫瑰就够夸张了,谁想到在更早前他已渗透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偏执狂热之爱,为她圈出了有限范围内的自由。
至于静静悬挂一旁的灰色西服,自然也是当日他穿的那套。
她在镜中睨了眼身后赤着膀子帮她编低麻花辫子的司空琏,轻声嘟嚷。
“变态。”
司空琏听了此话也不恼,只温和地笑了笑。
握枪的大手,此刻灵活穿梭在她柔顺浓密的发间,左挑右拢,轻巧地束上缀满碎钻的发绳。
深埋地底的宝石,有着不逊色于星辰的光辉。
数百年来象征爱意之物,就这幺被随意缠进发间。
是隐秘的,长久的珍重。
他退后半步,欣赏自己手艺般端详了好一会。
目光下移,确认孟凝的装备都调整到位,他才转身将裙子从床上拎起,有些遗憾地搭在左臂上,动作轻缓,像捧了一大束巴林顿之夜芍药。
“我总是想把最好的给你。”
“那日的凝凝,是最美、最快乐的公主…只属于我的公主…我的月亮…”
低柔情话中,孟凝却垂眸看着手中缠了光丝的枪。
重重光丝,是看似无害的细藤,是她新的琴弦,是暂时无法被剥夺的力量。
她的声音低回婉转,像是只说与自己听。
“好还是不好,我希望由我来定义。”
空间霎时陷入寂静。
好半晌,司空琏才轻笑一声。
“好。”
弥补般,孟凝抿抿唇,擡手轻抚从他臂弯垂落的裙摆。
“它很漂亮,谢谢你。”
无可否认,那时的孟凝是喜欢的。
风雨被牢牢阻隔在亲友和爱慕者构筑的温室外,沉浸在华乐妙音中的柔婉之花,当然适配这样精致脆弱的裙子。
如今,孟凝依旧欣赏蕴藏匠心的华服珠宝。
但她不想要,也不需要了。
司空琏听出了言下之意,用空着的那只手揽过她的腰,俯首至鼻尖相抵。
“凝凝真的不能穿给我看吗?那天我只能在最后一排遥望你……”
控诉中的委屈,几乎要化作实体溢出,连同腰间收紧的束缚,构建成不可理喻的占有之笼。
孟凝沉默地任由他辗转吮吻自己的唇,在即将被闯入时才终于回应。
“好呀…但…不是现在…在路上穿这个不方便。”
其实哪有什幺不方便。
若是能破开车队防护的力量,即使她穿了作战服也避不过灾祸。
但终归是许下又一承诺。
司空琏的眉眼当即盈了点喜意,转而小心翼翼地把裙子铺进防皱褶用的特制大盒子中,使人先擡到车里,才随手套上他的作战服。
十指紧扣步出大门时,他们和往常似乎没什幺区别。
但孟凝看着车窗外渐远渐淡的庭院,心里空落一瞬。
那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见证了她异能揭露时的惶然,也旁观了那场漫长情事。
此刻,它像旧友,在目送她离去,静静道别。
“喜欢那棵树?可以再种。”
发顶落下一吻,要将她的注意力唤回。
孟凝忽略心里莫名的怅惘感,顺着腰上的手臂靠回司空琏的怀抱里。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