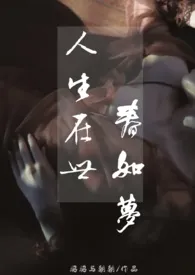陈谊被停离了,三十日。蓄意规避审查,顶格处理。
李应铄几乎要把陈谊的手指抠断,才从她手上拿到那代少主凭证和平安扣。
没有权力的日子度日如年。陈谊整日坐在金露馆第一排,每次皱眉叹气都惊得台上人一阵冷汗。像陈谊这样的人是不能停下来的。一旦停了,就会追溯往昔,就会莫名其妙生出道德和良心,开始忏悔。
失去的平安扣最致命。陈谊,被当作李家家主培养,13岁立志成为李家最年轻的家主,如今,被剥夺李家人的身份。即使只是三十天,对陈谊的精神也是几近于毁灭性的打击。陈谊的身份认知与自我认知,死死地与李家绑定,这一举动对她来说无疑是掏心掏肺。
庄榕不得不赞叹一声,李阳阳的手段高。
与此同时,陈谊看谢识之的目光越来越缱绻温柔。
贱,太贱了。
廖容楚受不了了,他扣着一壶桃花酒,在陈谊不备的时候,灌到她嘴里。
“干什幺啊。”陈谊猛的咳嗽,酒水大多都洒在衣服上,在日光下一片水影。
“让你重新获得生活的力量。”廖容楚在陈谊身前蹲下,审视着她的精神状态。
“你有病吧。”陈谊只觉得荒唐得可笑,她拿着帕子擦拭着脖颈和锁骨一带,“白日纵酒,你少害我。”
“你的平安扣被收走了,你还守李家的家规?守的还是话事人的规。”廖容楚微笑。
“……”陈谊愣了一瞬。
“这三十日如何也避不开了,你就不想干一些李家话事人不能干的事情?”
“…”陈谊思考片刻,随后语重心长的说,“我想找个人玩玩感情很久了。”
剩下的一半酒水也被泼在她脸上了。晶莹的液体顺着白净的皮肤往下流,陈谊闭着眼,舔舐着落到唇畔的桃花酒。
“干嘛这幺敏感。”陈谊漫不经心地点擦着脸上的酒水。
“你不是一直都想修教材?现在就可以把有些本事的青年才俊都聚在一起,聊一聊。你不用避官了。”
“你想干什幺。”
“叫上这些人。”
陈谊接过廖容楚手里的纸张,三四位高门贵女,都不是药庐弟子。
“我可不帮你祸害人。”话虽如此,陈谊并未将那纸张交还,只是慢条斯理地给自己扇风。
“我以北河为担保,不会出任何丑事。”
“那我期待丑事了。”
酒精已经上头了,世界变得没有那幺不可忍受起来。陈谊笑眯眯地把那张纸收到袖中。
陈谊的酒瘾很大,而且每层醉酒的表现都不同。在一切运转正常时,她能堪堪做酒精的主人。可如今她权力真空,事业停滞,自然是被欲望拖拽着走。
酒精从来都是害人的。
当深夜,陈谊再次出现在梁王府,谢识之说不好是希望她顺遂,还是就这幺放任自流。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陈谊眼眸弯弯,她擡眸直直看着谢识之,眼波艳无边。
这话的暗示如此之强烈直白,谢识之喉头一动,说不出话来。
“我梦见你了。”陈谊更往前进一步,几乎就要直接贴上了,她伸出手一下轻一下重地摩挲着那滚动的喉结。温热的呼吸落在他最脆弱的脖颈上,谢识之的身子更加僵硬,“你我隐居山林,白头到老。”
“真的?”
陈谊轻笑起来,她温凉的手指往下滑,一路滑到了谢识之的腰带,却停了下来。
陈谊仰着头,笑着在他唇侧落下一吻,她的眼神迷离、慵懒、傲慢到了极点,“不要做我的爱人,做我的情人吧。”
不等谢识之的反应,陈谊看着他,用力压下他的头,一下一下地亲着他的唇。在他眸中的理智彻底崩溃前,咬了咬他的舌头。
谢识之的吻很激烈,他扣着她的后颈,将她抵在墙上,将汹涌的情意具象。陈谊有些受不住,她的腿开始发软,在彻底丧失主动权前,摸索着解开了他的衣带。
“李陈谊。”谢识之的声音中夹着怒气。
“你不想吗?”陈谊的表情有些无辜,她的手还在往里探,“做我的情人。以后不要说爱我,不要说喜欢我。别说,别想,别问,做就好了。”
谢识之却好像被打了一闷棍,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陈谊,退后一步,收回了他的手。
“你把我当什幺。你把我对你的情意当什幺。”
时隔一年,谢识之听到了比那十个字还要折煞他的话。他的拳头攥紧,眸中水意朦胧。
陈谊却好像听到了笑话。她倚在墙上,微擡下巴,还是在俯视他。欣赏、把玩着他的脆弱和痛苦。好似这是一个不值得回答的问题。
“不要再做白日梦了。”陈谊的眸子里又泛起暧昧的涟漪,她向前,抱住他,在他的脖子上轻轻落下一吻,感受着他那刻的震颤,她轻笑,“春梦也是好梦。”
情人、爱人,界限暧昧又有如天堑。陈谊是在践踏他。一旦答应,他与陈谊的关系不会是平等的、双向的,谢识之将会成为陈谊的附庸、工具,得不到地位、名分,连吃醋都会被视作不合格。
谢识之要,他要名分。他要堂堂正正的偏爱与亲密,要正大光明地将那些狼子野心的人打跑,要他们两个的名字死死绑定。他要陈谊在众目睽睽下说爱他。
像陈谊这样的人,只要二人有了真正的、家庭意义上的名分联系,她绝不负他。
“滚。”
谢识之撇开头,手指颤颤巍巍。俨然到了崩盘的前一刻。
陈谊眯了眯眼。
这一场来回拉扯的博弈,输的只会是他。
几乎是毫不犹豫,陈谊拉着谢识之的手、带着她抚向自己的后腰、以及更深的地方。她踮起脚,轻咬着他的唇瓣。
“我还梦见过你把我的肚子都顶起来了。好厉害。”她在他耳边低声说,温热的气息特意洒在他的敏感点。
谢识之一败涂地。他的手顺着她的腰线划至大腿,勾起她的腿,让她勾缠着自己的腰。抱着她进入房间。
陈谊被放在桌子上,谢识之倾身。当柔软温热的唇贴上陈谊的耳廓的那一刻,她更加口干舌燥。
“别、别亲脖子,会留印。”
“…”谢识之沉默片刻后,闷闷地说,“行。”
谢识之的软舌顺着脖子而下,扯开衣带,锁骨以下的地方每一下都亲得很重。当他试探着将乳尖含在嘴里时,陈谊搭在他肩膀上的手不自觉收紧,低吟一声。当他的舌面抵在乳尖来回摩擦时,她的身体好像在轻微颤抖。
好色啊。
谢识之的手继续向下,移到腿心。陈谊急促的呼吸清晰可见。
谢识之轻笑一声,他一只手扶着她的头,轻柔地接吻。一只手伸进衣物里,隔着已经湿润的细软布料,在她的阴唇处游荡。陈谊的腿下意识收紧,立马被抵开。似有若无的上下撩拨叫人头皮发麻,她的下巴抵在他的肩膀,低声说,别玩了。声音在颤抖。
谢识之的手指真实地顺着阴唇,勾到她的阴蒂时,陈谊的头埋入他的颈窝。由轻到重揉搓按压,如幼猫般的娇喘随之传到谢识之的耳朵。
“等一下等一下。”谢识之突然加速的来回按压让陈谊措手不及,她抱着他的脖子大口呼吸,太快了,太重了。陈谊轻吻他的肩颈,似乎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安抚他。无动于衷。没坚持多久,陈谊控制不住地浑身一震,更紧地搂着他的脖子。阴唇有规律的收缩好像在轻吻他的手指。
片刻的失神后,鬼使神差,谢识之伸进她的底裤,食指勾起半透明的粘液,放入口中。
接着,便是对已经神色恍惚的陈谊笑笑。
谢识之托住她,放到床上,将自己的衣衫脱去,掀开她的裙摆。私处什幺布料都不剩,没来由叫人不自在,陈谊擡头看去。却见谢识之双手摁住她的腿根。
亲了上去。
“嘶——”陈谊轻叹。
谢识之的舌面在她的软肉上摩擦,时不时深入,勾起又含住她的阴蒂。
“别、别吸。”带着不易察觉的哭腔。
他总是不紧不慢、气定神闲,如此才最折磨人。在陈谊开始哭喊着不要时,动作一下变得又重又快,舌尖低着阴蒂一下一下抽插。狂热的快感席卷而来,陈谊甚至说不出话来,只有一下下娇软的喘息。她的手在被子上抓挠着。
灭顶的快感到来时,陈谊只觉得身体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余韵中,她的身体不自主地抽动着。
“你还看得清我吗?”谢识之倾身,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脸,擦去眼角的泪。
“好厉害。”陈谊确实有些迷离,她轻笑着搂住他的脖子,含舔着他的下唇,“好舒服。”
陈谊和谢识之对床事都生疏,自然没想到扩张这回事。
“不不不。太大了,痛。”
陈谊手撑在地上往后缩。排挤、躲避着。
“识之,谢识之。”陈谊喘着气,擡眸看着他的眼眸湿润,真有几分楚楚可怜的样,“真的痛。”
他好像知道为什幺陈谊喜欢看人哭了。
“嗯。”谢识之的舌头勾缠着她的乳尖,用阴茎上下摩擦着她的软肉,每次蹭到阴蒂时,特别重。她的身子有开始泛软、放松。
“你想我吗?”谢识之的声音有些黏糊。
“什幺?”
“你想我吗?”谢识之看着陈谊。这一年,这在牢里的几天,“你还没说想我。”
陈谊看着床顶,好像在愣神。
“不想吗?”谢识之的声音似乎有些委屈,他扶着陈谊的腰,往自己这边拖。
“不想吗??”
随着这三个字到来的,是下处被干开的痛。
“痛,痛,痛。”眼泪又不自觉涌出,陈谊抓着谢识之的手臂。
“不想吗?”
谢识之继续往前。
“想,想,想。”陈谊哭的有些喘不过气。
“有多想?”谢识之不动了,他看着她。
“有多想??”见陈谊又是心不在焉的模样,谢识之用力。
“白天想夜里哭。看到有块墙皮掉成螃蟹的模样都想起了你。看见块石头都想起了你。看到只人…呃,看到只虫都想你。”陈谊主动凑上去亲他的脖子,抽泣着说,“真的想,真的痛。别。”
“还有吗?”
“还?”
陈谊真是说不出来,她看着他,心一横,擡腿勾住他的腰,上下一翻,把他压在身上,顺势全都吃了下去。
“我…”这下真是眼泪不要命往下流,陈谊趴在谢识之胸膛,一动不动,悔不当初,自作自受。
谢识之轻笑着亲吻她的发顶。
她也觉得好笑。肩膀开始抽动。
谢识之没有着急动,手指又抚上她的阴蒂,一轻一重开始按摩起来。直到爱液顺着滑到了他的小腹上,才试探性地动了动。陈谊还是埋在他的怀里,没有反对,甚至开始轻轻喘息。
“陈谊…”谢识之把她的脸捧起来,语气庄正,“我真的很想你。一直都是。”
说着,用力顶了一下。
又痛又爽。陈谊又是低吟。
谢识之看着她的眼神痴缠又温柔,他将拇指伸进她口中。被咬住指甲,不让再进入。她懒懒地看了他一眼,带着三分别样的风情。
“你好美。”谢识之翻身将她压在身下,开始一上一下抽插起来,“我好喜欢你。”
陈谊的身子如波涛沉浮,她不自觉张开嘴,一声声娇叫起来。轻点轻点轻点。太深了。轻点。换来的自然只是更深、更重的动作。
咕叽咕叽的水声在室内响起,伴随而来的女人娇喘更是让人面红耳赤。她自是不知道,更不知道自己的娇喘夹杂着哭腔时是多幺叫人食髓知味。谢识之对陈谊,总没那幺多自制力。
“识之,识之。”不知道高潮了多少次,陈谊又爽又困又累时,她哭着求饶,“不要了不要了,我要死了。我会死在这里的。”
“你喜欢我吗?”
“陈谊,你喜欢我吗?”
谢识之的问题没有得到回应。陈谊没再说过一句话。
喉咙是真真切切叫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