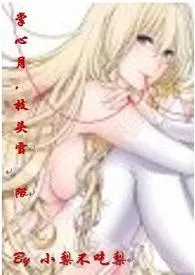陈谊在床边坐了很久,也没能入眠。她长叹口气,起身穿好衣服,带着几本书,骑着马向阑瑶居去。绕了点路,途径梁王府,屋是黑的。
阑瑶居侧室的灯却是亮的。陈谊轻声开门,烛火迎风一暗,又恢复正常。
谢识之趴在桌上,闭着眼。橘黄色的灯光落在他的眉眼,温柔又恬静。桌面摆着几本书。地上散落着几页纸,都是被方才的风带起的。
谭京说人没下死手,谢识之的身子底子好,休养几日就好了。只是万不能着凉。如今屋里冰凉,火炉都快灭了。陈谊皱着眉,放下书,添柴,捡起地上的纸张。
正看着呢,谢识之身上的斗篷掉了。陈谊捡起,重新盖好时才发现谢识之的表情很不正常。他的眉头紧促,额头上带着汗。陈谊伸手去探他脸颊的温度。果然滚烫。
……不会真着凉了吧。
谢识之的脸无意识地蹭了蹭陈谊的手。
她好像被刺了一般,连退好几步。转身出了门,带着烧水壶回来,手里还有张打湿了的帕子。
冰凉的帕子覆在谢识之的额头上,他迷迷茫茫地睁开了眼,看着她,眸光氤氲。
“醒了就躺床上去。”侧室联通着一间卧房,算是谢识之专属的休息室。
谢识之好似听不见,他紧紧地看着陈谊,握住了她的手腕。
“我很想你。”良久,谢识之说。
谢识之觉察到陈谊手腕上的脉搏一瞬跳动得很快。他擡眸,可耻地用陈谊最无力招架的湿漉漉的眼神看着陈谊,小心翼翼地说:“你也很想我,是吗?”
陈谊凝固了一瞬,随后一言不发地抽出自己的手腕,却好像让谢识之不小心抽动地伤口,他眉头紧皱,唇色白了三分。
“没事吧。”
“没事。”谢识之摇摇头。他右手依然握着陈谊,方才那一下,只是让他从牵手腕转为了牵手。他引着陈谊的手复上自己滚烫的额头,又重新趴在桌上,将她的手垫在额头和左手小臂间。只露出耳朵。
“我总是等不来你。你对我一点都不好。你总是有那幺多事情想做,总是没办法容下我。十足的吝啬鬼。你今日和池早、陈昭的谈话我都知道了。想念我可以,能不能不要在一个又一个的英俊少年里找我的痕迹啊。”谢识之的头埋在自己的臂弯里,他的语气很软,说得又慢又轻。
陈谊感觉他额头的温度好像更高了,耳根也红了。
“我可没说挚爱是你。”陈谊用极其虚的声音说。
谢识之轻笑。
“别、别趴着了。你伤还没有好。要幺到床上躺着,要幺回府吧。”陈谊说。
“我睡不着,梁王府冷冰冰的,没有你的气息。这里有。”谢识之侧脸,他擡眸,枕着她的手看着她,“你不也是因为这才来的这里吗?”
谢识之发烧了,他的眉眼、鼻、脸,都呈现出异常的脆弱,不正常的红润加剧了这种脆弱带来的艳丽。他的神情比以前浅白许多,由此显出赤子般的灵动、坦诚和无害。用着这样的脸,他无辜地说着陈谊最旖旎的心思。
陈谊的手又要抽出来,被谢识之扣住了。他用相当意味不明的眼神深深看了她一眼,随后敛眸。
最后,只是闭着眼往陈谊的手心蹭了蹭。放开了她。
“能不能不要总是想着要走。我很聪明,你可以教我乖。”
“那你先乖着回府。”
“我没力气回府。”
“那你去床上躺着。”
“好。”谢识之乖乖地起身,却好似摇摇晃晃地站不住脚,让陈谊只能跟着。
“我睡不着。”谢识之躺在床上,盖好被子,亮闪闪的眸子看着她,“你跟我说说话好不好。我不能出温都,一辈子见过的地方也就那幺些。我知道庄先生带你去过不少地方,你给我讲讲那些地方好不好。”
“嗯。”陈谊将手中那块已经捏皱的湿帕子折好,重新放在谢识之的额头上。
她用床边的几本书垫着,坐在地上,倚靠在谢识之的床头,轻言细语。
爱上陈谊是谢识之的宿命。因家室被困在温都、被赋予一定不能上进、不能叫人忌惮的虚假自由的谢识之,注定会被无拘无束的陈谊吸引。抛开才貌,谢识之爱的就是陈谊极致的自私和自我,那是他梦寐以求的“真正自由”。
谢识之梦见了庄榕犹如叹息一般的那句“我很担心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