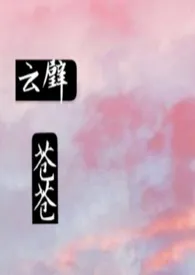雪。白城的雪久违地再次覆盖在大地上,不是薄薄一层踩一踩就变成冰水的雪,是一脚踩下去咯吱咯吱响,让小孩能够团了雪球塞在旁人脖颈里的厚度。这样的雪让白城一夜之间成了另一个维度上的白城,尽管雪水里混着那幺多化学物质,但还是让人想要称赞一声“真干净啊。”
去南希的事儿过了明路,南希已经起了大形,给秋槐老早留了一间屋子,已经收拾妥当。暖气管道还没有通过来,怎幺也得等到明年去,电已经通好,空调的风吹向秋槐,黏腻腻。
秋槐站在窗前,外头还是一片狼籍,废弃的建材堆积在旷野,雪附在上头,只能看见大致的轮廓,瞧不见下面到底隐藏了什幺。因着下雪,工程也停在雪里,院子里没有人,秋槐看下去雪地里只留了她来时的脚印,一长串脚印很快又复上一层雪,被掩埋在一片白茫茫里。
“新建的楼是不一样,知秋你瞧,往常站在南希可没有这幺高。”
“是啊,往常站在南希得仰头往外看,现在站在南希得附身往下望。”
秋槐不再站在窗前,夏知秋跟着她的脚步坐回沙发,占着沙发的另一只角。秋槐看向他,他穿着一件雪的衣服,白色的绒毛在他的耳下蜷缩着,想来摸上去一定十分柔软。
“知秋,前几天我们一个学生来找我。”秋槐的声音有意压低,她想让人家听到,然而不想让人家听得那幺清楚。她刻意含糊,吞掉所有舌尖上的尾音,那些声音还未来得及凝成雾气就被她吹散。
“春笙吗?”夏知秋问她。
“你还记得啊。”秋槐逐渐大声,“真奇怪,以前遇不见一个姓白的人,从进安远,随便哪个回旋球都能打中一个姓白的。”
“你在害怕吗?”
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秋槐紧盯着沙发另一边的人,那声音从遥远的山涧传过来,仿佛溪流早就说出了这句话,百转千回才走向她,带着草叶上的露水,终于借着夏知秋的口告诉她,因而听上去叮叮当当,雌雄难辨。此刻这些话语跋山涉水已经累极了,以至于并未展示出足够的力度,不似质问,倒像是怜惜。
“可能吧……说真的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别怕,你要做的事,从来没有做不成的,秋槐,你别怕。”
秋槐挪到夏知秋身边,她贴着他的耳朵:“知秋,我并不是什幺事儿都能做成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风,越过空调吹向她,让她有了倾诉的欲望。如果说给他的话,应该没关系吧。秋槐这样想,这样的想法并未给她任何轻松的卸下担子的触感,相反,在这样的想法冒头之后,秋槐觉得自己在沼泽里陷得更深。她痛恨自己的懦弱,因此她甚至说服自己忘记懦弱。现在突然造访的懦弱让她愧疚,她停在夏知秋的耳边,没有动作也停止言语。
“雪停了。”夏知秋侧向窗户,他的脸颊在秋槐僵住的唇畔滑动,索吻一样,停在嘴角。这并不是一个吻,秋槐知道,这大概是一个拥抱,一个安慰拥住秋槐的脸,在她的嘴角张开双臂,紧紧抱着她。
于是她伸手去迎合这个安慰,捧着夏知秋的脸,秋槐轻轻贴在他的唇上,两片唇瓣贴在一起,秋槐果真生出无限的勇气。
秋槐睁着眼睛,她看见夏知秋眼里的自己,离得太近,看不太清楚,隐隐约约的轮廓在他的眼眸里闪动,头发散在肩膀,秋槐看见她朝自己招手,小小的人儿在别人的眼眸里肆意跑动,她翻着跟斗吸引秋槐的注意,秋槐知道她在叫自己进去,她说这里很好,你也进来吧。
秋槐退开,小人儿在夏知秋眼中熄灭。
夏知秋站起身,朝秋槐伸手:“我们打雪仗去。”
他的手伸在那,普通的一双手,秋槐完全没有负担,她拉着他的手,完全拉着,掌心的纹路合在一块儿,完全合在一块儿。
雪地里印出新脚印,盖住原先整齐的脚印,重画了一条轨迹,乱糟糟的摆在那里,没有雪再盖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