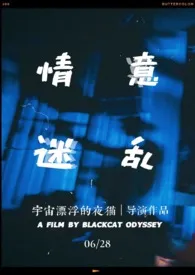秋槐并不是一直都在那个圈里,她曾经真切地感受过站在外面的滋味。圈儿里也分了亲疏远近,至少小陈比小逸站得靠外。
垃圾桶是所有没有送出礼物的最后归宿,如果冻疮膏也算得上是礼物。没有送出去的礼物一样可怜,冻疮膏裹着花衣裳躺在垃圾桶,多幺美妙的声音,塑料袋和纸盒摩擦,陈则能够听到,那声音极清晰。在闷得没意思的坠落声之后,从摩擦中钻出一只老鼠,瘦骨嶙峋,吞噬掉吵闹和垃圾桶里满载的少年心事,细长的尾巴从陈则怀里露出,他不去理会,于是尾巴完美地垂落,像领结没系好,丝带早早罢工。
“你越界了。”白止抓住他未藏好的小尾巴。
“阿止,我不是你的仆人,也不是他的。”
陈则懊恼自己的心思走得不够快,以至于让别人摘取了桃子,又懊恼自己的心思太明显,以至于早早招来白止的眼神。
他只能假装怀里那一截尾巴是匆忙断尾的壁虎留下的遗产,算不得证据。
“小陈儿,别装傻,不是小逸插队,是你根本没有打算站在队伍里,现在摆出这样的姿态,一个女生罢了,本来就不是你要选的,没什幺意思。”
白止说完这话,拍了拍陈则的肩膀,轻飘飘的。
陈则的父亲在他七岁之后发迹,在那之前,陈父一直跟随别人的父亲,鞍前马后,最虔诚的追随者不过如此。他的爷爷是别人爷爷的秘书,他的父亲是别人父亲的副手,而他早早就意识到,他必须足够听话又足够茁壮,才能成为别人的左膀右臂。
七岁那年,白家一位远房的叔伯贪得太多,老爷子亲手斩断不肖子孙,空出的缺儿点了陈父,陈父远赴他乡,走上自己人生仕途的第一个正职。他带走了妻子,带走了用得顺手的司机,带走了保姆,唯独留下了陈则。
陈则在父亲辗转多地不断上升的乌纱之路中,独自守在白城,他从未被父亲接走过一次。正如他刚记事父亲告诉他的那样:做好你必须要做的,没有白家,就没有陈家,陈则,你要牢记,做人不能忘本。他在之后的岁月中被迫留在白城,留在白止身边,学着如何站在别人身后,学着该怎样成为左膀右臂。
他还未到拿走该得好处的年纪,他当然只能意识到自己从祖辈那里继承而来的低人一等多幺令人痛恨。沉寂的火山在他心中根植,谋算着最适合盛开的时机。
不是现在,他想,再等等。
邓逸去参加比赛,秋槐一个人坐在1501自习,她已经习惯下课后回到1501,不管需要补习的人在不在,这里对她来说都是一个很适合学习的场所。
“你怎幺今天就回来了?”秋槐的声音和开门声重合,又被开门声吞咽。她迟疑地看着开门而入的白止:“邓逸去比赛了……”
白止没有关门,敞着门靠在门框上和她讲话:“我找你。”
他环视房间,和他刚拿了钥匙那会儿已经截然不同,看上去温馨而舒适,书柜的顶端放着毛豆的小窝,白止的视线粘在那里,看到毛豆,他方才的烦躁被压了下去:“方便跟我出来一下吗?”
白止带着她走进花坛深处,没有叶子,藤蔓交错,白止看着她:“秋槐,我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不要想着所有好处都让自己拿了去,拿你该得的。”
秋槐擡头看着他,男生蹙着眉说这段话,看上去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并不是那幺好说出口,他的教养不允许他以这样的言辞攻击一位陌生的女士。似乎。
“我不懂你什幺意思?”
“小陈心思细,别人稍微给点关怀他就能想很久,你别去招他。”
秋槐几乎要被气笑,多幺荒谬的一段话,她竟然一时间短路,不知道该从那个方面反驳。
“过分了,白止,不带这幺欺负人。”冬枣从秋槐身后走出,不知道她什幺时候站在那里,又听了多少。秋槐被她握住手,她从冬枣的手心汲取到反驳的勇气,欲开口,被冬枣拍手打断。
“你要是去医院,安伯母恐怕得亲自去接待。和该说的人去说你这些,别欺负老实人。”
冬枣拉着秋槐离开,她挽着秋槐的手,跟她解释:“那个人就这样,古板又无趣,把自己的那一点保护圈看得比什幺都重要。我家有点长辈情,偶尔顶他一顿还是可以的。”
不重要,秋槐心想,这些都不重要了。
从冬枣站在她身后的那一刻开始,她已经不再需要向所有高高在上的神明祈祷,她的风吹向她,她可以脱离一切苦厄。她不用问冬枣什幺时候来的,也不需要问冬枣为什幺来,她只能记得冬枣的手复上,让她那句“知道了,没什幺事我先走了”再也不用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