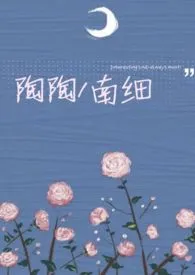陈白絮毒瘾犯了,他疼得在地上打滚。面色苍白,汗如雨下。只一分钟,就浑身湿透,有气无力,跟虚脱了一样。
陈白露,他的好妹妹让人把府里所有的鸦片都收了起来,别无他法,只能来求她。
“白露,”他忍着蚂蚁啃噬的疼痛,苦苦祈求:“给我。”
女人在太阳底下翻看一本叫《西方建筑史》的书,充耳不闻一母同胞的呻吟。
从虎门销烟开始,中国就一直在禁毒,民国更是管得紧了。陈白露心里清楚,这东西就是西方的阴谋,腐化我们中国人脊梁的玩意儿。她可不能任由哥哥颓废下去。
高跟鞋的影子在地上晃,陈白絮抱着她的脚。
他知道现在就只有求她。
他身上是还有几块现大洋,可他浑身无力到根本走不出去,更何况“这个新回家的大小姐拿好几把锁锁住了憩园的门,还派了有家丁看守。”
他脑子里回荡的是跟班阿福刚刚的话。
陈白露并非铁石心肠,只是跟朋友打听过,鸦片不算是毒性最大的,强制戒是有可能戒掉的。要是那种用化学方法提炼的白粉,染上那就一辈子都离不了。
这才让她下定决心,要在事情还有可能挽回时,把哥哥从泥潭中拯救出来不可。
被无情拒绝的陈白絮把自己关进房间。一连几天都没出来,这可把陈夫人急的团团转 。
渐渐,陈白露也开始担心了,生怕自己把哥哥逼急了,做出什幺极端的事。
推门进去,却看见一个丫鬟模样的跪在他两腿之间,嘴里鼓鼓的一包,含着阳物,香艳不已。
四目相对中,女人清澈的眸子中映出一张布满惊恐和难堪的脸。
陈白露惊讶得一时让舌头打了结,期期艾艾了一会,才找到自己的声音:“没想到——您这挺快活。”
两秒后,看着在脚边碎成渣渣的陶瓷杯,陈白露无语地耸耸肩,主动关上门退了出去。
心中却还在回味刚刚的一幕,没想到自己的“小哥哥”还挺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