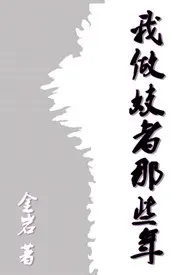萧琢臣一听到他的话,先是一惊,为他的决定与想法担忧着并也震撼着,虽皇帝是他的兄弟,但在法治前,即使是兄弟,还是无法容存着例外与宽容,但他却为了她,竟想以命护之。
虽莽撞,但却也成功的烫热了她的眼眶与心,为他的承诺感动着。
「你不用这样的。」萧琢臣还是担心他会因此而遭受惩戒。
毕竟那晚的一切,本就是她开的头,她打一开始就没打算要他负责,甚至希望他能当作是场春梦转身便忘。
墨逵朗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反而问道:「后悔吗?把身子给了我?并且将自己是女儿身的秘密让我知道?」
萧琢臣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后无悔的摇了摇头。
若说后悔,便是她起得太晚了,若那一夜她没在激情中昏厥,始终保持清醒,或许便可避免掉许多不愿面对的麻烦。
看出她眼底盘算的墨逵朗。
「妳以为自己始终保持清醒,便可趁我睡梦中离去,制造出一场春梦的假象来粉饰太平吗?」
萧琢臣没料到他竟准确的猜出她的想法,吃惊地看了他一眼后,便心虚的别过眼去,默认了他的说词。
墨逵朗对于萧琢臣毫不掩饰的真切反应,露出无奈却饱含无尽宠溺的笑。
「妳以为初尝禁果的妳,能支撑住我的索取吗?」说到此,他突然停住,随之身子一探,贴在她耳边轻声道:「那夜我的猛烈,别说妳忘了。」
听墨逵朗这么一说,萧琢臣立马想起那夜的缠绵火辣,与眼前男子那孜孜不倦的疯狂,脸瞬间一红,拉起被子就想将自己羞涩的模样掩盖住,可惜她的动作还是慢了墨逵朗一步。
墨逵朗按住就要被往上提的被子,凑近她羞红的脸又道:「妳知道自己的左乳下方,与腿间秘林内各有一颗芝麻大小的小红痣吗?每每一碰,妳便会化身成蛇,敏感且诱人,尤其是随之发出的吟叫声,格外的甜美。」
萧琢臣一听,简直快疯了,他怎么可以将这么私密且……且……羞人的事直接讲出来,这跟登徒子有何异!
想瞪他,却没勇气面对他那仿佛要将她吞食殆尽的炙热眼神。
又一次使劲拉扯过被子,想掩盖住自己此刻所有的反应,眼前这男人却无耻地直接用自身的体重,将其压制,让她想躲却没地方躲,甚至让这登徒子贴得更近了。
气愤的她,只能伸手摀住他的嘴,让他别再说出那些让人心头搔热、羞涩难当的话语。
可她却没料到,眼前这男人却以一招化解了她的封印。
这时她突感手心一阵湿热,墨逵朗竟伸舌舔刮了下她的掌心,让她不禁惊叫出声,忙松开对他的封制。
为他的不正经,皱眉微蹙,发怒着,双眼却依然不敢与之相迎,就怕看到他眼底的戏谑。
却忽略了只是套上并未系上的长衫,在两人的拉扯间逐渐敞开,春光外泄中,让墨逵朗大饱眼福。
坏心的墨逵朗没有出声提醒,而是双眼更是肆无忌惮地又一次细细欣赏那遍布她全身,由他一手促成的红紫印痕,每枚印子都意味着他那夜的侵占与疯狂。
一想到手心滑过萧琢臣皮肤的触感,与硬铁深埋于她紧致甬道内被挤压的快感,好不容易平息下的燥热,又自他的胯下蔓延开来。
暗暗地将身子又朝她靠了几分,甚至恶意地压住长衫,让长衫随着她的动作一点一点的失守。
萧琢臣懊恼地想推开过于靠近自己的他,可眼前的男人,却如座无法撼动的大山般,无论她如何推就是推不开。
开口才想喝斥他别太得寸进尺时,一步步靠近她的男人却抢先开口道:「酒不会喝,就不要再喝了,我怕妳到时会吃了不该吃的人。」
「才……才不会咧!那是因为是你才……」
萧琢臣急忙想解释,可解释到一半,发现自己若将心底话全说出,恐会让两人间的关系更加的难以厘清。
加上……她若说出,不等于是赤裸裸的告白吗?
她还没有心理准备做到那一步啊!
当她吞吞吐吐时,眼角却不经意地对上他狡诈的眼。
这男人显然已然猜到一二了,却还用话来套她,就是希望她能吐露出内心对他的真实情感。
「因为是我才什么?」墨逵朗笑颜逐开地追问道。
萧琢臣别过头去,不想回答,更不敢看他,就怕他看出自己真实的心事。
可即使萧琢臣不明说,光是看她的反应与发红的耳尖,便知道了一切。
墨逵朗将她整个人紧抱入怀,唇贴在她耳廓边,边着摩娑着边轻声问道:「所以……那夜的一切,是一时的冲动?还是……」
他不愿自己独下注解,他希望由她亲自告诉他。
虽他大致已明白萧琢臣的心意,因她不是那样随便的人,她洁身自爱、严以律己,若不是她心甘情愿,他这辈子恐难知晓这秘密,毕竟这秘密一但揭露,欺君罔上株连九族是迟早之事。
她妹妹是比她命还重要的存在,她竟愿意冒着她妹妹可能受其牵连的危险,将自己的秘密曝露让他知晓,甚至将自己最珍贵的身子给了他。
便知晓,若不是她对自己有意,这辈子他恐怕怎么样也无法近他半分。
低垂着首的萧琢臣,自然明白他问的是什么,身子一动就想逃。
可近乎半裸的身子却被身旁的男人给紧紧箍住,怎么样也动不了。
「八年我都等了,妳逃了今日,明日后日我一样会逼妳说的。」
墨逵朗的警告让萧琢臣无奈一叹。
因她自然明白这男人的执着是有多么持久,就如他痴缠自己身子时那般的无赖,怎么样也甩不掉。
她犹豫地揪了揪身下的被褥挣扎了下,才喃喃道:「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十年前,你拿了一碇银子跟一张宫卫的引荐书给一对在街角卖艺,却无人理会的兄妹,你对那个哥哥说,你的能力不该埋没于此,用来报效国家才是正途,况且唯有这样,才能有更稳定的薪饷照顾你的妹妹。」
随着萧琢臣的解说,那段已然模糊的记忆在此刻慢慢的具体起来。
当时的他,为了帮助他二哥夺权,佯装纨裤子弟,游手好闲地四处晃,实则是四处招兵买马,当时的他,应是见她是可造之材,所以便给了那张引荐书吧!
他还记得当时一个王爷仅有十张引荐书,所以他二哥一见到他要将那张引荐书给萧琢臣时,还一脸玩味地对他说:『你确定要给?给了就要负责人家一辈子喔!』
当时有些喝大的他,还一脸潇洒的回说:『负责一辈子就一辈子,我又不是养不起。』
万万没想到,当时的玩笑话,如今却成真了。
现在想来当时他二哥的表情,恐早就一眼瞧出萧琢臣是个女子,不说破,就是为了看他的笑话罢了。
想到这个可能,他便一阵的气恼。
但他的气恼,很快便被萧琢臣那软软糯糯的女子声线给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