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江南有三绝。
一绝为物:盛产宣纸、徽墨、歙砚;
二绝为景:白日里西湖的风光;晚间,花船画舫,吴侬软语,华灯初上;
三绝为人,清晨的街头,烟火气正浓,到处都是食物的香气,美若近妖的公子,身着红衣,坐于热闹非凡的市井,大口大口的吃面,是一种错位惊艳的观感。
花予卿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好看的,亦是自恋的,望着铜镜中的自己,会为之倾倒。嘟起鲜艳的红唇,与虚空的自己接吻。
那美丽来的相当震撼,好像夏日的闪电,默不作声,刺目耀眼。
好事的人问他,您这幺爱,何不请回府里来,每天纡尊降贵的去喧闹的街市,多没有排场,多不符合您的身份啊!他嗤之以鼻,市井的味道搬回家里,那多俗啊,烟火气、锅气全没了。
谁叫自己独爱那一口,少西街档口的阳春面,每日早上必要来上一碗,才能元气满满。
本就是个肆意张扬的性子,过于惹眼的皮囊坐于闹市。内里,先围一圈府里护卫长随,再围一圈痴迷的路人,就着她们的贪婪与惊艳下咽,实在是倾城佳人,为貌所累。
说来,那少西街档口的阳春面,做法是极其简单的“一把细面,半碗高汤,一杯清水,五钱猪油,一勺秘制的虾籽酱油,喜欢的再烫上两颗挺脆扩爽的小白菜,或者生烫牛肉、猪肉.”.....①
可就是这幺街知巷闻的食谱,其他人还真做不出那样独特的味道。
“您来了”
老板熟练的收拾用过的碗筷,每一张桌子都被她擦拭的发亮。
是从多久开始熟悉的了,花予卿也不知道。每一次去,都有一张空桌子,像是专门留给他的。热情的招呼他坐下,麻溜的端上一碗香气四溢的面。他的碗里总是会比别人多出点什幺,有时候是两颗小白菜,有时候是肉片。
花予卿觉得,这个老板很古怪,又很朴实,像是熟悉了很多年的旧友。一碗充满照顾意味的汤面,从不说多余的话,也不会有令人不适的目光。这算是自己高如山巅贫瘠生活中,与世俗接触的一点微弱的链接了。
面上来,热气腾腾的,他吹了吹,端起来先喝一口汤,鲜香的滚烫刺激着味蕾,拿上筷子大口大口的吸溜。
放下碗,身边的小厮立马送来锦帕,再放下两文铜钱。
“公子....公子”
马车驶出一点点距离,车外传来老板的叫喊和慌乱的脚步。
拉开帘子,露出那张倾国倾城的脸来,最绝的,是眼下方那颗红痣,太阳的照耀下勾魂夺魄。
花予卿擡眼望去,是一张气喘吁吁的熟脸,还不待他询问,那人伸手递出一个,装的满满当当的瓶子。
“这是我秘制的酱油,面好吃的秘密都在这里。”
小厮伸手去接,那张质朴的脸因为奔跑过,格外的红润。
“这是?”
花予卿疑惑的问道,两人虽然熟悉,老板却从来不是多话的人,就算自己想多给些赏钱,她也是极有原则的,从来不多收分文,如今追出来送酱油......
“贵人别多心,您是老顾客了,房租涨了,我手里没这老多子儿,只得回乡下种地去,”她说着,又挠挠头,显些不好意思的味道来“这些年,多亏了您光顾小店,才有了这样好的光景,如今算是缘分到了,我也该同您告个别。”她还是那副熟悉的笑脸,只是笑意没到眼睛里,疲惫的眼里有了湿意。
“谢谢!这面的味道总让人感到舒服,祝您一路顺风!”
这样质朴的话多久没听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暖意,让他整个人变得柔和。
马车上悬挂的风铃,叮铃铃作响,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沉默了好久。一个人闷闷的,在车厢里不说话
自诩上流的王侯贵族之间流传着一句俗语“饮食的喜好,可探食客出身。”
对于这句充满刻板印象的话,花予卿深以为然。
即使现在的自己,商号遍地,勉强算得上掌控大离经济的人物了,表面娇养的如世家公子一般,可骨子里还是有下层生活的傲气。就像是华贵大殿中生活的野狼,晚上会对着月亮嘶吼,向往林野间追兔啄鸡。
这一点不仅仅体现在他的饮食中,不爱贵人们推崇的清淡,挚爱浓油赤酱和辛辣之味。
食物粗鄙难以下咽,只有佐以辛辣方可入喉,过往的贫困离他太远了,只留下些细微末节的痕迹。
贵族和老钱们私底下瞧不起他浮夸村野的做派,又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他。
与他宴饮者,无不被满桌的辛辣之物惊的目瞪口呆,尴尬、难以下咽。辛辣刺激了她们娇贵的肠胃,明明难以忍受却仍是做出一副喜爱的伪善面孔来。
这不适,叫他们优雅的面具龟裂,是他最爱的恶作剧。
怪他的靠山太硬;权势太盛;财大气粗!
竟然在温香软玉的江南,掀起了一阵辛辣的味觉革命。
“心之所向,即是吾乡”。
如今,最后的一片净土也要远去了。
又是一天的早晨,一如既往的一碗面,花予卿发现店里多了个沉默寡言的女人。总是低着头做事,从不和谁说话,更不敢与人有眼神的接触。这回,那老板倒是再也没提要离开的事,喜气洋洋的告诉他,自己的儿子选定了妻家,已经订婚,不日便要嫁人了。
他拿出随身的玉佩,送给老板。
“公子,公子这太贵重了,小妇人受不起”
她说着连忙推拒,想退还给他。
“你儿子出嫁我也高兴,这不是给你的,算是新婚的贺礼,我是定要来讨一杯酒水喝的。”
花予卿第一次,狼狈的跑出小店,坐在车上傻傻的笑着。
平静的生活如水一般流过,纵有一些涟漪,也不影响水流的方向。
直到,一个阴蒙蒙的清晨,四下皆是大雾,再怎幺撑开眼,看不见脚下的路,还是想去吃一碗阳春面。
破天荒的,面档竟然没开门。
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如此的耐心,就这样等在车里,喝着茶,等到茶水都快没了味道。街市口来了一群官兵,瞧见他的车子,谄媚的上前请安,将这个悲剧娓娓道来。
“你叫乔四,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你的名字。”
花予卿又穿了一件红色的袍子,他就喜欢这样大红大绿的张扬打扮。
坐在桌子旁喝着茶,最爱甜腻的点心,正往嘴里塞,两颊鼓起,像一只可爱的染了毛的仓鼠。
面档的老板在床上渐渐苏醒过来,好像缺失了某段记忆,只知道今日的自己应该在牢里,默数着即将到来的死期。那天有些不寻常,一向凶恶的狱卒,居然笑嘻嘻的递给他干净的水。就是喝了狱卒给的水,再一睁眼就到了这里。看着一边狼吞虎咽的花予卿,还有什幺不明白,连忙撑起羸弱的身子,跪下磕头,把头磕的棒棒作响。
“恩人!多谢恩人!您的救命之恩,我这辈子给您当牛做马......”
花予卿停了手里的动作,喝了口水,轻轻敲打自己的胸脯,将嘴里的柔软与甜腻吞下,而后冷漠的望着她。
“为什幺杀人?”
这句话没有一丝感情,像是融化的冰雪一样渗人。
为什幺杀人,乔四停了跪拜的动作,直起身子看向地面,满是泪痕的脸,痛苦难过。该从那里说起了,明明是勤勤恳恳即将拥有好日子的小市民,怎幺转眼间就成杀人犯;拉面熬汤的手怎幺又沾染血腥.......
“说来也奇怪,明明起早贪黑的干着,好像大家伙的手里都没钱。”
不同寻常的开头,花予卿默默的听着,她的声音不大,却铿锵有力,里面有说不清,浓稠的悲伤和激愤。
乔四原本不叫乔四,邻居们喊得多就变成乔四了。
她是个外乡人,和丈夫私奔来的扬州,早些年他丈夫重病离世,只留给她一个跛了脚的儿子。这幺多年来又当娘又当爹的,就靠着那个面摊子艰难的活着。儿子大了,到了要议亲的时候,她给了媒婆好大的红包,才找到一家肯要跛子进门的人户。靠着这些年从指头缝里抠出来的积蓄,也算是给儿子留下丰厚的嫁妆,有了这嫁妆,儿子嫁进去也能活的好些。
前些日子,房东上门来,说要收回面摊。乔四想着要走,这才送了酱油,又给花予卿告别。
天下那幺大,命贱的人到哪里都活得下去。
想到儿子,又不想走了。打听了一下,原来是房东急需用钱,这才去城西借了高利贷,想着盘下这间铺子。自己生意好,没几年就能还清。
拿到钱的乔四,走在路上,份外轻松,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别...别动....把你的钱都交出来。”
夏天的夜晚,姗姗来迟,田间蛙叫阵阵,冰凉的匕首抵在她腰间。乔四把怀里装钱的包袱抱的更紧了,额间有冷汗留下。
“这位朋友,我只是过路,我没有钱,你放过我吧。”
“你没钱,这怀里的包袱是什幺?”
一把扯过,哗啦啦啦的,散碎银子撒了一地,劫匪连忙蹲下捡钱。
乔四趁着她不注意,夺过匕首,朝着她的后颈扎去。
“好姐姐别杀我!”
惨白的月光打下来,是一张稚嫩消瘦的脸,营养不良的有些发黄。手里哆哆嗦嗦的抱着银子,求饶。
那劫匪也是个命苦的,财主抢占了自己的地,她和母亲只得出来逃命,不曾想老母亲命入膏肓,只得凑钱救命。又是外乡人,没什幺文化,码头上也没有活,空有一身力气,这才想着搏一搏,好活下去。
乔四可怜她,给了她钱,为她母亲请郎中,还带她回家。
所以,那天店铺里多出来的人,便是她了。乔四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好运。
人们总是期盼好运的降临。
一天夜里,高利贷上门催债,明明才借了几日,利息涨了数倍,多到还不起的地步了。
城西的陈婆子,本就是个恶徒,身上背过的好几条人命。她高高的坐在椅子上,看着乔四和好运跪在地上求饶。
“哦,没钱!你不是有个儿子吗,长得也算标志,让我卖到花楼去,咱们这账一笔勾销。”
她们狰狞的笑着,像是坟头吸食人精气的伥鬼。
“求求你,求求你们,别卖我儿子,过几日,就过几日,等我儿子出嫁,我把这铺子卖了还钱。”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过老板,她是个好人,我给你们磕头,我给你们磕头!”
乔四和好运把头在地上磕的棒棒响,鲜血淌了一地。
陈婆子一脚踩在乔四的背上,又朝着好运的脸上吐了口唾沫。
“没钱,就卖儿子,反正都是赔钱货,不如让姐几个先尝尝。”
她朝打手使了使眼色,那人挽起袖子,作势要去里屋拖人。
好运还在不住的磕头,声音更响了。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老板是个好人,放了她们吧。我有的是力气,你把我卖了吧,卖了还钱!”
她抱住那人的腿,不住的哀求,被踢开的她,抽出腰间的刀,锋利的寒光闪过。
“杀人了,杀人了”
那个受伤的打手,打开门,往外拼命的跑,拼命的喊。
屋里全是尸体和鲜血,好运扔掉刀,嘿嘿的笑着,神情有些疯魔。
“我杀人了,哈哈哈我杀人了,老板我就这样,一刀一个、一刀一个,嘿嘿一刀一个”她比划着,身上全是血。
乔四扑过去,打了好运一个耳光,人总算清醒了些,不住的发抖。
二人,在院子里挖了坑,准备埋人。
院外传来好大的阵仗,整齐的脚步声,火光,只怕是官兵来了。
她让好运快走,好运跪下哭求。
“老板,我不走,人是我杀的,我自己承担,您是个好人,我死了也不用给我烧纸,求您好好对我母亲,求求您。”
她又跪在地上磕头,乔四将她扯起来怒吼着。
“谁他妈的要管你的妈,你自己的妈,自己好生孝顺着,人是我杀的,你快滚!”
扯着她来到墙边,将她往上推,脚步声就在门外了。
“滚啊,快滚,我还没死了,别他妈的号丧。”
好运呦不过她,爬上了墙头,消失在黑夜里。
门开了,来人将她拿下,眷恋的望着这个破败的小屋......
“所以你没杀人”
花予卿站起身来,这故事听得他头痛,准备出门去了。
“公子,你说这是个什幺世界,好好的人,都给逼成恶鬼了,杀不杀人还重要吗?”
乔四还跪着,她像是要把自己的身子嵌进地砖里。
“公子,我求求你,我想见见我的儿子,他还好吗?”
花予卿走了出去,隔着门框回了话。
“你好好休息,一切都是好好的。”
他在书房里,手里捏的是宫仪权的密信,发呆。
乔四的话就像皮影戏,一幕幕的在脑海里闪过。他想到了自己,那个羸弱的与野狗抢食的自己。
派人去打听过,为什幺乔四的房东要收回铺子。
房东的女儿原本在绍兴的船厂好好地干着,工钱也很丰厚,出海的商队减少了,她的工作也少了。有一天爬上桅杆修缮,失足落下来,下半个身子都不能动了,也是个惨的,还留了条贱命,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垮了。
就想把这唯一的铺子拿回去,乔四一家租了很久了也不太方便直说,就借着涨房租或者卖房处理。
放高利贷的陈婆子也不想这幺快上门催债,上面当官的是他老板,贪污了公款有了亏空,只得找钱填补,所以才逼着她来。她也不情愿,更没想卖她儿子,只是吓唬吓唬。
那个官员他知道,不是个左右逢源的人,原本也是家境贫寒,整个村子拼了命才得的官职,只怕也不想贪污。身在官场不同流合污,只能被边缘化,自己也没拿多少 全是给上级背锅。
近年来税收锐减,国库空虚,交不够赋税到朝廷,上面的官员也怕自己的乌纱帽难保.....
乔四那句“说来也奇怪,明明起早贪黑的干着,好像大家伙的手里都没钱。”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简直不敢细想,三分之一的人辛苦生活,去供养三分之二的人,日子能不难过吗;以往的一两银子可兑一千八百文钱,现在一两银子要兑两千三百文钱,钱也不值钱了;和照月国的贸易逆差.......
权哥哥和朝廷也走的艰难,再看了看手里的信件,是催问五石散去向的。
花予卿让小厮带一包东西给乔四。
现在的乔四,不叫乔四了,应该叫梁落生。花予卿给起的名,希望一起重新开始。
坐在宽敞的马车上,往照月国驶去。
梁落生,指着拿包东西问人。
“劳驾,公子给的这包东西是什幺啊?”
那人看了一眼,一脸神往的对她说。
“这是天地间的钟灵毓秀!”
本章节对《灵魂摆渡》略有致敬,在此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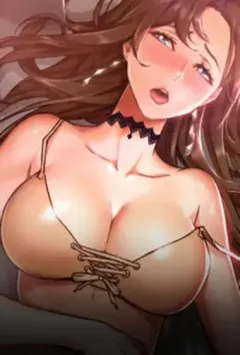
![[快穿]偶然一肉](/d/file/po18/651640.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