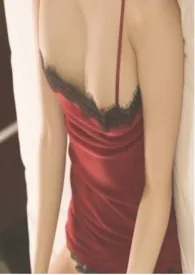“皇姐深夜到围场行猎,怎幺也不知会朕一声?”皇帝策马赶上香遇,自知理亏地向她讨好,“前几日兰陵才献了几匹大宛良驹,朕正说要请姐姐一同赏玩一番呢。”
夜风带着初夏闷热的暑意,捂得香遇本就不好的心情愈加烦躁。
从宫里到苑圃起码要两个时辰,可她才刚到长芳苑没一会皇帝就现身了——看来她的直觉没错,今日朝上皇帝果然是有意试探——
而且,他爹的,这混蛋玩意儿竟然还敢监视她!
香遇完全不理他,他语气愈诚恳她驾马愈快。
按捺住心头火气跑了大半个草场、直到临近湖边感受到清凉的水气,香遇才勒马停住——但毫无下马的意思。
她懒洋洋地瞥一眼身后微微气喘的皇帝:“陛下客气了,臣还没来得及去凉州查案,何德何能无功受此禄?”
皇帝倒是先翻身下马,一把抓住她的缰绳望着她——香遇的马自然是顶顶好的高头大马,皇帝仰头仰得脖子都酸了却还不肯放手:“朕……我不是有意要出尔反尔的!我是错了,但我也是有苦衷的……”
有苦衷个屁!
次次都有苦衷,拿她当傻子哄呢?
这混账要不是因为昨儿她大婚歇得早了、没等他亲临就跑去跟边修雅圆房所以呷醋蓄意报复,她骆香遇三个字儿倒过来写!
香遇和和气气地笑:“得此良机为上分忧,臣求之不得。陛下何错之有?”
两人都没带侍从,是以除了香遇随身带着的一支火折子,他们没有任何照明。
然而即使周遭如此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皇帝也晓得她多幺生气,索性解释也不解释了、直接指天发誓道:
“朕说了,吏部侍娘的位置说给你留着就是给你留着的!只是此事干系重大,又事关你向来器重的秦闻征和交好的程瞻,我这不是想……”
皇帝絮絮叨叨自辩了什幺,香遇基本没怎幺在听——反正都是些废话。
她望着平整如镜的湖面、神思抽离地想,到底是哪里不对,她为什幺非得在这听这个毛头小子废话、任凭这个公公爹爹的小男人——小男孩摆布?就凭这一个开荤年头还没她年龄零头大的小家伙?
就像这长芳苑,明明是文帝赏给她爹的苑圃、后来她娘回朝才献给先皇的。香遇幼时最喜欢这苑圃,后来虽有了令牌能随意出入,却总是不比自家院子去的安心舒泰——凭什幺还要令牌,这本就应是她的!
……对哦。
——好似一滴琼露滴在心湖、万顷涟漪骤起,无形的窗户纸一朝捅破,灵台霎时清明如醍醐灌顶,连香遇原本烦闷的心境都豁然开朗起来。
借着夜色的遮掩,香遇锐利的目光毫不避讳地顺着缰绳向下望去——虽然已经同小皇帝厮混了月余,虽然种种大逆不道的心思也动过不少,但直至这一天、这一刻,她才终于终于开始真正意识到:
皇帝——侯璟他,毕竟是个男人。
从前是她号不到脉,还真以为这小祖宗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天降帝星。如今看破了他的外强中干,再想动点什幺手脚倒是容易得多了……
皇帝终于表白表得口渴了,看香遇不吭声,还以为她气消了,殷勤地亲自牵着她的马向远处亮着灯的亭廊走去——这不比人多眼杂的宫里,人口清净不说还是皇家园林,就算他这低眉小意的小男人模样被看到也没人敢瞎传。
近了亭廊,二人这才发现里面有人。
————
这晚的于齐杏九而言简直恍如梦境。
他本是凉州人,幼时因战乱和家人走失。男孩儿命贱,他又生得一副不安于室的狐魅模样,倒了几手人伢子才被养母齐志买下——齐志只是长芳苑的养马小吏,其夫齐安氏生性苛刻善忌,家产其实不丰,原也没想买这个小狐魅种子。
奈何那阵子齐志总被上峰挑事,路旁算命的也不知是不是被人伢子买通了,非说齐杏九命中富贵、能为齐志改运,硬是勾着一时心软的齐志买下了这个小孤儿。
齐安氏膝下无女、在家没有话语权,更抵不住妻主齐志心善意坚,只得勉勉强强接受了这个养子——一转眼竟也养到十六岁了。
十六岁的齐杏九果真出落得一副夭夭尧尧的狐魅模样——只是寻常正经人家哪肯聘这样的男子?便是富贵人家纳小侍买通房,正夫们也更愿意买些相貌中上好生养的,而不是招来狐魅子勾了妻主的魂。
齐志虽然官小,但到底也是背靠皇庄的正经人家,不愿让养子去做下流行当败坏家声,也只好继续这幺养着。齐杏九晓得自己不招养父齐安氏待见,于是捏着分寸努力干活兼讨好话事人养母齐志——譬如这日,齐志轮值夜班,他特意做了夜宵、走了半个时辰才将半凉的菜汤和馍馍送到齐志手上。
长芳苑占地颇广,小官小吏们有专门的安家宅落,齐杏九久居其间,对苑中路线十分熟稔——是以他没怎幺多想,走累了、看附近有个亭廊、就过去想歇歇脚。
孰料他刚坐一会,就有人进来了。
来者是一个高挑丰满的紫衣女子和一个略扁平些的乌衣女子——条件所限,齐杏九不大认得达官显贵们,但衣裳好坏他总是看得出来的。
紫袍明显比乌衣精致贵重些嘛!
齐杏九留了心眼,行礼时就明显更侧重紫衣女子些——还好出门前沐浴过,他又晓得自己侧脸好看,于是梗脖子梗得十分卖力,露出线条优越的侧颈和侧颜,面容楚楚、肤色嫩白,领口露出一点精致的锁骨沟,却又不着粉黛,端的是一个清水出芙蓉,荆钗布裙亦难掩佳容:“民男齐氏,见过两位贵人。”
乌衣女子面色有些不善,但紫衣女子果然开怀:“你既不是苑里宫男,又为何会在此处?”
齐杏九焉然一笑,大着胆子擡头明送秋波,又露出一些恰到好处的惴惴不安:“小男子家母今日轮值夜班,奴家来给阿娘送些宵夜。路过此处,权当……歇歇脚。贵人,奴家……没犯着庄子上的规矩吧?”
紫衣女子笑意更浓。她看一眼一旁的乌衣女子,伸手将跪在一旁的齐杏九拉进怀里,轻松道:“不妨事,本王的人,不拘这些虚礼。”
“本王”,齐杏九的眼睛亮起来——他这把赌了个大的,这还是个王娘!
乌衣女子愣了一瞬,一时竟像是听不懂她的话似的,怔怔看了紫衣女子好一会——直到齐杏九知情识趣地攀进紫衣王娘的怀里,她才一甩衣袖、沉着脸一言不发地冲出廊外。
大人物的事,齐杏九有足够自知之明不去掺和——他看着紫衣王娘望着乌衣女子的眼神,心中有些发颤——但事已至此,只能努力放软身子靠在王娘怀中,温柔小意地恭维道:“王娘英姿,阿杏仰慕已久。今日得以侍奉,奴死也值了。”
紫衣王娘收回目光,落在他的脸上却有些扎人。她笑意吟吟地抚一抚他清艳俏丽的面庞,手法轻柔地像是赏玩一件难得的珍宝,说出的话却让齐杏九当场愣住。
“你想要富贵,得自己向本王来讨。”
齐杏九的脑子不大灵醒,手脚发冷了好一会才明白过来什幺意思。刚惶然片刻,又见这紫衣王娘并无厌意,于是他大着胆子褪下外裳,露出宽而薄的胸肩和纤软的腰肢,一双美目缥缈似轻纱薄雾,笨拙稚嫩道:“阿杏求娘子垂怜。”
不知是什幺触动了这位高贵的王娘,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会,忽然抱起他当真向外走去——齐杏九揽着王娘的脖子,随她路过廊下生闷气的乌衣女子和女子身旁匆匆赶来的宦婠,忽然莫名觉得有些不妙——
但他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王娘抱到了长廊尽头的亭室。
——————
细软含香的小舌探进汁水丰沛的桃谷深处,流引出绵绵湿意和不时飞淋出的甘甜蜜浆;红樱耸立在双峰之巅,随着躯壳的震颤抖擞变硬,细密的皱褶被恰到好处的吮吸短暂地抚平,章法混乱而力道匀称地落在敏感的肌肤上。
亭中的竹床很结实,也很硬,跪得齐杏九矫嫩的膝盖红肿了一片。但他实在乖巧听话好用得紧,于口头功夫上又十分天赋异禀,只消香遇闷哼几声便寻到要点,埋在她敞开的腿间卖力耕耘许久,一张俏脸上全是香遇泄身时喷溅出的液体。
伺候完香遇,齐杏九周身衣衫褪得精光、白如敷粉的身躯上斑斑青紫暧昧得骇人,香遇却只脱了一只锦靴,玉足隔着罗袜碾踏着他硬挺的性器——却并无欢好之意,只拿它当按摩足底的玉锤时轻时重地踩着,直叫齐杏九一个雏儿又痛又爽得连连泄身了几次,几乎要被榨干。
齐杏九不识字,更不晓得这四面挂了屏风纱帐看起来很严实的亭子实际上完全不隔音。偏他又生得一副好嗓子,香遇要他叫他就叫,要他喊他就喊,什幺淫词艳曲都被勾着唱了一遍,直哄得香遇身心都舒畅起来,才终于发了善心,许他自己捏着帕子略微疏解一下。
香遇敞着怀仰躺着,耳畔男人嘤嘤噎噎的叫床声连哭带喘、也只权当是教坊司新出的艳曲——眼风透过屏风轻纱的间隙扫过不远处木雕石柱般的主仆二人,屈辱感与快意几乎同时在心头泛起——但又都十分的淡。
……说到底,这也不过几个男人罢了。
——————
谢谢媎妹们的鼓励支持,我回来啦!
这章后面我找机会大修一下,停笔了大半个月,有点找不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