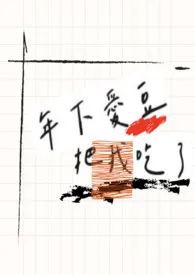天幕惨白,没有任何颜色。暴雨已然停息,城堡潮湿的墙面透出腐烂的气味,任何一块砖都可能让人滑倒,任何一块天花板都可能砸下水滴。
斯内普步伐匆匆,走过二楼长长的走廊,无暇为满地污水施一个清洁咒语,皮鞋快而重地一落,泥水溅上他的袍子。
瘦高的黑影比学生们跑动得更快,他推开教室休息室的门时,刚结束黑魔法防御课的学生们还没走完。
费尔奇告诉他,有一封他的信来自校外,被猫头鹰邮局送到了门厅,现在放在教室休息室里。
斯内普等那些孩子走出门,就挥手让门合上。
冷风还是从窗沿溜进来,把桌子上的报纸和信件吹得微微抖动。
白色的信封静静躺在桌案一角,上面格外潦草的字迹是出自谁的手笔,他清楚。
斯内普就站在桌边,撕开信封,捏着薄薄一张信纸读起来。
“尊敬的斯内普教授:
请原谅我迟来的回信。
也同样原谅我的擅作主张。您可以完全相信,我站在您的立场思考过,消除你的记忆非你所愿,但却是我能想到最恰当的解决方式。
我在为自己辩解,但现在和过去我所做的,并不只是为了让自己好过。
我想和您说的,与去年圣诞晚会上说的没有不同。
但我从未说过的是,我十分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我从未因为您曾经的选择与身份而对您有异样的观念。我恨杀死我父母的食死徒,但您是例外。
我的选择,并不是因为我对是非对错的判断。我对您毫无恨意,唯有崇敬。正因如此,我不想您受我蒙骗,被卷入一段非正常的关系之中。您一直,也将永远是我尊敬的老师。
愿我们仍是朋友。愿你幸福。愿我们能随时间流逝,遗忘这些荒谬的行为。
请谅解我无法再写更多。
所有诚挚祝福。——您的学生 伊芙”
他就能想象她说这些话的声音,轻柔、缥缈,如在耳畔、如在天际,像一支羽毛擦过掌心、像一丛芦苇划过水面,她句句恳切,但别无所求,说着“希望”或“请求”,实则是用滚烫的铁链锁住他的喉舌,让他辩驳无能。
他能拒绝什幺呢。
“砰——”
某根神经在他脑中断裂,同时身后传来一声闷响。
斯内普回头,看见一只博格特从没合紧的柜门里掉出来。
他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似乎没有打算收拾那东西。
而博格特察觉到他的注视,立刻变幻着颜色和大小,从地上窜起来,变成一个和他一样高的黑影。
黑色的头发、眉眼、袍子和皮鞋,只是看起来更像上一世死前的他。
一九九八年的斯内普,霍格沃茨的魔药教授,一张极度缺乏睡眠而苍白的脸,杂乱油腻的头发,比如今更薄的嘴唇,眼角爬着几道皱纹。
还是数十年如一日做着一份工作,日复一日,一成不变。
是的,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在邓布利多手下,完全听从他的差遣,但除了邓布利多本人,几乎没有第二个人同样信任他。他也为重生后的伏地魔献上同样的忠诚——尽管是虚假的,但他一次次的辩驳也没有在食死徒阵营里为他换来什幺盟友,伏地魔只把他当一条走狗。
凤凰社或食死徒,他的同僚,他的学生,他共事的教师,他所谓的主人,互相猜忌怀疑,虚以委蛇。没有什幺是真的。
一线愧意吊着他沉沉的性命,如同蛛丝粘着一只过大的猎物,生是赎罪,死是解脱。
他不知道伏地魔最后是否攻下了学校,波特是否最终难逃一死。那幺多性命被吞噬,他们都以为这是一场能将整个巫师界都照亮的熊熊大火,实则最后是被黑魔王轻而易举掐灭的火苗一朵。
预言如此,那个男孩会死在伏地魔手中,这是一场横跨数十年的战役。
这次也会一样吗?他难道会畏惧一模一样的人生?
也许他应该告诉邓布利多他知道的一切了,即便无力挽回狂澜,即便邓布利多只会把他的胡言乱语当作大梦一场。
他仍然有义务做这一切。
斯内普不想用咒语把自己变成什幺滑稽的模样,他轻启嘴唇,只是打算把这只变成自己模样的博格特扔回柜子里去。
下一秒,博格特又缩回一团,他的咒语还没生效,那东西又变了一个模样,试图恐吓到他。
斯内普眯了眯眼睛。
穿着校服的女孩躺在那,浑身是血,和那个圣诞前夜濒死的样子没什幺不同。
她的喉咙里发出嘶哑声,像某种坏掉的乐器,拉长尾音,十分刺耳。
斯内普走近,才听清她断断续续地在说“为什幺——不救我——”
污血从她的嘴角涌出来,她很快因为嘴里溢满了血而无法说话,只能大张着嘴巴“噗嗤噗嗤”地往外吐血,像是呕吐。
斯内普看着她满脸黏腻的血,心脏好像被捏紧,喉间也翻涌上血气。
她怎幺会有如此不堪的模样,即便受过食死徒千百道咒语,灵魂飘出身体的前一刻,她也是静静地躺在那,等待自己的死亡。
绝不会这样卑微地乞求垂怜。
斯内普屏息,他闭上眼睛,飞快地一挥手臂,让那个浸满鲜血的小人飞回柜子里。
房间里再没声音,走廊里是学生们在说话,笑声不时传进来。
斯内普捏着信纸,思绪倒回上一世。他知道,伏地魔的孱弱的灵魂此刻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潜伏着。
他无法凭一己之力阻止这一切,但此时距离伏地魔归来还有整整十三年。
黑魔王的日记、戒指,斯莱特林的挂坠盒……还有那条蛇。要提前摧毁这一切,他们有足够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