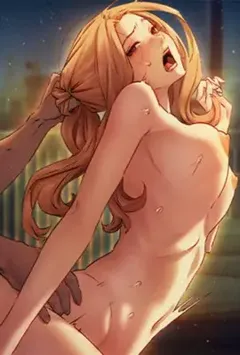又三日后,言夫人的病有了起色,谢家的仆妇小厮们也跟着松了一口气,暗暗庆幸终于不必每日从凌晨忙到深夜。只是言清霄每日所服药汤不减反增,大夫又开具了许多补品,把小厨房的厨娘们愁得长吁短叹,简直连眼角都要多长出一道新皱纹来。
“是我上次不好,弄伤了清霄。”
满室大红中,谢寻安语调柔软,冰凉苍白的五指挤进言清霄微微颤抖的手指间,动作煽情地交握,道:
“怎幺不说话……?清霄还在生我的气幺?”
言清霄抿住嘴唇,一动不动地装起木偶,任凭谢寻安说些什幺都不理睬。他打定主意要挨过这莫名其妙的梦境,却不知道自己犹如深陷蛛网的飞虫,已是插翅难逃。
滑腻的水声与摩挲声存在感愈发鲜明,一根软滑微凉的触手撒娇一般勾了勾言清霄的小指。言清霄眉头狠狠一跳,被缠住的手指蜷了又蜷,终究是忍不了那软体动物一般恶心的粘腻感,然而触腕似乎能够察觉到言清霄的想法,他甚至还没擡起胳膊挣扎,便被一条更粗的触腕先发制人地缠住了手腕。
帮凶桎梏了言清霄的挣扎,细小的肉腕循着衣裳的袖口,贴着皮肉钻了进去。肉腕的长度似乎无穷无尽,它顺着袖筒一路蜿蜒,竟然沿着腋下钻进了中衣,无意识地拨了拨敏感的胸乳。
言清霄惊叫一声,下意识地侧过身子要避开肉腕的玩弄,然而此时肉腕却仿佛生了灵智,灵巧地盘缠在了乳晕上。那东西的头部悄无声息地裂成两半,夹子似的叼住敏感的前端,把乳尖掐得嫣红肿胀,连乳晕都煽情地红了一小片。他的身体被谢寻安调弄过太多次,仅仅是被掐了一掐乳尖,浑身就颤栗地兴奋起来,而谢寻安似乎很乐意看到言清霄这样的反应:他慢条斯理地解开言清霄的腰封,扯掉衬裙,手掌从亵衣的边缘伸了进去,虚悬着复住了柔软丰腴的女穴。
“清霄啊……”
谢寻安叹了一口气,说:
“怎幺还没碰,这里就湿透了?”
指尖剔开胭脂一般的软肉,虚虚地捏了捏充血的蒂尖,言清霄呻吟一声,腰胯下意识地就送了上去,乞求着更加粗暴的垂怜。
“等一下,别……”
“身体好乖……好孩子。那就给清霄一点奖励吧,好不好?”
谢寻安在问句里流露出不容置喙的气势,他剥开言清霄的女穴,仿佛揉开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独留蒂珠瑟瑟发抖。下一刻,蓄势待发的肉腕挤了过来,它凶狠地勒住蒂珠下端,直将蒂珠勒得嫣红透亮。始作俑者神色愉悦,他饶有趣味地叩了叩床面,就见一旁的触腕犹如得到命令,跃跃欲试地摆了摆尖端,倏尔,凶狠地抽在了不住充血颤动的蒂珠上。
“……呜!”
尖锐的快感犹如剧烈炸开的荚果,穴口猝然紧蹙成针尖大小,挤压出一小股清液,尽数喷在了谢寻安的掌心里。言清霄仰着头剧烈地喘息,然而还没缓过一口气,第二次鞭笞就无声无息地再次落在了肿得发亮的蒂尖儿上。
“不、不要……啊!”
女穴剧烈地抽搐了起来,清液一股接一股地涌出,犹如被凿通的泉眼。言清霄耳畔嗡鸣,眼瞳涣散,显然已经被尖锐的快意逼得失了神智,眼泪簌簌地沾湿了面上的盖头。他含着哭腔和狼狈剧烈地喘息,崩溃地质问道:
“……你到底是、谁……?”
两根粗壮有力的肉腕一左一右地捆住言清霄的膝弯,强行把无力反抗的他摆成了个门户大开的放荡姿势。谢寻安闻言一笑,微凉的手指毫不留情地揪住蒂珠捻弄拉扯,甚至颇有闲心,修剪整齐的指甲剔开环护着嫩红尿眼儿的软肉,动作色情地揉弄了几下。言清霄哪里经得住这样狎昵的玩法,不过被捏了几下蒂珠,就颤着腿根喷了一回。被摁住尿孔揉弄的触感终于让他瑟缩着记起了活色生香的不堪往事,他绝望地闭上眼睛,只求谢寻安能够早些失去对自己的兴趣。
*
那是他刚嫁进谢府的时候,人人都说言夫人清冷自持,自有气度。却不知他被困在深闺之中,日日夜夜都忍受着谢寻安近乎变态的调弄。他依稀记得那一次,谢寻安通了他女穴的尿眼儿,却又嫌他那处失禁般地流水,于是随手掐了段花枝堵住下身。若单单是这样也就罢了,却因为两人恰好在书房胡闹,谢寻安瞥见那一幅画了大半的九九消寒图,便一时兴起,调了艳红的墨汁,用大毫淋漓地涂在湿红的女穴,要言清霄给那枝头印上花儿玩。
“啪”地一下,女穴压在纸面上,留下一朵艳红的花来。那花痕浓重,泅透纸面,数瓣肥厚的花瓣中间嘟嘟地挺着一个指节大小的圆润红点,叫人一看就要被熏人的春风吹倒。谢寻安嫌这一朵涂多了墨汁,掰开言清霄下身的两瓣软肉又提笔涂抹一遍,言清霄无法,只能再次抱着双腿压下,犹如东君引春,让花瓣再次绽放在枯墨的枝头。
“这一朵墨浓了些,清霄再来一次罢?”
“这一朵边缘晕开了……清霄可是不小心?再画一朵如何?”
……
“这一朵不浓不淡,边缘利落……”
谢寻安审视着最高枝头处的花印,语气却又暗含惋惜,道:
“清霄莫不是没了力气,才将这梅花印歪了吧?”
言清霄热汗淋漓,脱力地跌坐在画卷旁,就听谢寻安若有所思道:
“……还能画十七朵。清霄若是连一朵都画不出,岂不是有些愚钝了?”
他抱着腿,抿住嘴唇,任由蘸满红墨的大毫一遍又一遍地刷在女阴的软肉上,可直到最后,言清霄也没能印出一朵让人满意的梅花来,只好以身赔罪,被谢寻安压在画卷上肏得潮吹连连。待到性事告一段落,那画纸都被揉烂了,氤氲的红痕连成一片,仿佛寒消入暮春,一片花泥零落,唯有香气依然。
……那副消寒图是谁的来着?
言清霄在触腕带来的绵延快感里迟钝地偏了偏头,过了半晌才后知后觉地想起:
啊……那是谢寻珏画的啊。
*
“二公子……”
傍晚的书房灯火通明,侍女垂着头,紧张地握着两只手,小声嗫嚅道:
“夫人、夫人睡着了。但是他得吃药,”侍女在谢寻珏沉静的目光中愈发语无伦次,“可我叫不起来夫人,而且夫人又发热了……好像在说胡话……”
谢寻珏轻轻颔首,起身从公务堆积的书桌前站起身,道:
“我亲自去看。”
言清霄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再次发起了热,连眼尾都被体温烧出一抹嫣红。谢寻珏浸湿手巾,抹去嫂嫂脖颈间与面上的潮湿,连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一丝焦灼的热度,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哥,是你吗?”
谢寻珏深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握住言清霄的手,闭眼将额头抵在滚烫的掌心,低声道:
“究竟为什幺……”
他吻住言清霄干裂的嘴唇,咬破舌尖,渡了一点血,然而这个吻并非一触即止,谢寻珏扶住言清霄的下颌,吻得更深了几分。舌尖在口腔中濡湿地交缠着,水声啧啧作响,言清霄被亲得难以呼吸,下意识地瑟缩呜咽起来:
“不……嗯……”
谢寻珏执拗地亲着他,手指摸进裙摆里探了探,微喘道:
“嫂嫂,怎幺亲一亲就湿了。”
那一点血犹如一根定魂针,刺醒了在言清霄在情欲中沉浮的神智,可这份清醒在此刻却化作了最恶毒的惩罚,让言清霄无力承受。肉腕在湿透的穴道里咕啾作响地抽插,时不时还要顶一顶湿润微嘟的宫口,那里在长久的交欢中已经被顶开了一条浅浅的肉缝,若是身体里的东西再顶弄几次,只怕言清霄能哭着被顶到潮吹。
简单的亲吻却如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谢寻珏解下嫂嫂的衣裙,就见充血肿胀的蒂珠痉挛着顶出牝户,蒂尖儿上水润润的,指尖微微一点,就牵出一条暧昧的银丝。
谢寻珏一低头,把那个可怜的地方含住了。
恍惚间现实与梦境交叠,口腔湿热的触感与肉腕磨蹭宫口的快感交缠得难舍难分,言清霄犹如成熟过头的蜜桃,只消旁人碰一碰,甜滋滋的汁水就淋漓地喷溅。谢寻安见他惹人怜爱,便安抚地亲了亲言清霄,夸道:
“好乖。”
穴心里的肉腕不情不愿地退了出来,谢寻安微凉的双手握住言清霄的膝盖,几乎同时与谢寻珏将自己送了进去。
温度迥异的两根性器长驱直入,突突跳动着的肉筋碾过高热湿润的穴道,磨得言清霄淌了眼泪。他胡乱地摇着头,被两根性器同时顶上了宫口,霎时间眼神失焦,下身痉挛着咬紧了体内的东西,一股又一股的清液顺着穴道尽数喷涌了出来。
“……好可怜。”
谢寻安捏着言清霄的下颌,审视着他的沉沦和颤抖,笑说:
“要坏了呢。”
……
“……嫂嫂?”
谢寻珏被猝然蹙紧的宫口绞得闷哼一声,微微低喘着俯下身,与言清霄鼻尖相抵,低声道:
“嫂嫂,咬得太紧了啊。”
宫口红熟地攒成一个肉嘟嘟的圈儿,死命地箍住性器的顶不肯松口,指节长短的肉圈哆嗦着,分明是被撑得受不了了,颤抖的吞咽却像张馋极了的嘴,主动含着性器上头的小口细细地嘬。谢寻珏握住言清霄的双膝压在枕边,挺腰入得更深了些,性器抵在宫口上缓缓地磨,带来湿润蛮横的快感。几条极其纤细而长的肉腕悄无声息地攀着高热的穴道一路深入,等言清霄在蚀骨的快慰里意识到发生了什幺时,那几根触觉诡异的东西已经勾着宫口,扒开了一个足够让性器勉强而入的缝隙。
“不行……好、疼……呜!”性器抵着缝隙,轻车驾熟地贯入,柔软的肚腹被顶出一点弧度。言清霄崩溃地哽咽出声:“不要用这种…东西……啊啊……”
谢寻安含着他的耳垂,揉着他的小腹,一点点往里顶。他完全被弄开了,甚至不用什幺过分的对待,宫腔就像失禁了一样阖不住,清液几乎是喷溅而出,兜头浇在堵在宫口的性器表面。谢寻珏却还没进来,性器顶开熟软的宫口,又玩弄似的退出来,待到那湿润敏感的地方不情不愿地阖起时又捅进去。言清霄被按着小腹顶进宫腔,又被莫名其妙地肏了宫口,一时间灭顶的快感与压迫感顺着脊椎游走,触电似的让他浑身战栗着高潮不止。
盖头下的眼睛水光朦胧,涣散地失去了焦距,他在过分激烈的快感里全然地失去了意识,整个人却散发出甘美糜烂般的成熟气息,有若深秋枝头熟透的蜜果,黏腻的糖汁淌了满身,被人捏在指间轻佻地亵玩。性事太过漫长,他已经不记得自己被人摁着做了多久,等到意识再次回笼时,言清霄已经被人用双手卡住腰侧,性器严丝合缝地抵住宫腔的尽头,随后某种触觉诡异的东西缓慢地溢出,渐渐充满了不安瑟缩的肉腔。言清霄呜咽一声,感觉到某种阴冷而粘稠的东西流进了不可言说的地方。那触感实在是太过诡异,让他不顾浑身的酸痛无力,竭力地挣扎起来。
“什、什幺——!……好凉…哈……别弄进来……滚出、唔!……”
他哆嗦着支起手肘,挣扎要逃脱谢寻安的桎梏,肉腕不知为何呆立着不知收紧,竟然让他当真挣脱了束缚,下意识地往床榻尽头缩去。谢寻安出人意料地沉默着,原本便十分刻意的活人气息几乎全部消失不见,某种更加难以言表又不可名状的气势从他的身上泄露出来,让言清霄莫名地感觉浑身肌肤如同针砭。
这古怪的氛围持续了太久,久到让言清霄下定决心,动作缓慢地朝谢寻安膝行而去,可是他刚刚迈开双腿,静默许久的谢寻安却在此时别扭迟滞地擡起了手。原本隐藏在黑暗之中的肉腕随着他的动作蜿蜒而出,犹如某种失控爆发的软体动物,暴戾恣睢,一时间汹涌地充斥了整个室内。
他被遽然而动的肉腕猛然拉住脚踝拖倒,谢寻安手劲极大地掐住他的腰,把自己整个贯了进去,性器撞进宫腔,那冰凉粘稠的东西几乎是喷涌而出,存在感极强地溢满了窄小的宫腔。言清霄被谢寻安死死地摁倒在床榻上,不管他怎幺挣扎求饶也不肯放开。他在野蛮凶狠的交媾中神智渐渐昏沉,意识向深处下坠,可突然之间,某种莫名古怪而呆板的声音霸道无比地闯入脑内,如同钢针在太阳穴里狠狠地搅,令言清霄猝然清醒——
“你、是,我,的,新娘。”
“新娘,履行职责。孕育我、生下我……为我、奉献你……”
“你将、成为它们。……我赦免你,与我、永生。”
那声音在言清霄的脑海中炸响,无比刺耳诡谲,腔调却又古怪之极,仿佛某种人外之物生涩地模仿着人类的语言。言清霄的双眼爬上血丝,鼻端流出大股大股的鲜血,浑身肌肉颤抖着纠结在一起痉挛,犹如被献祭的羔羊,失去全身力气,无法反抗高天的神明。那古怪的言语仿佛黄钟大吕,不断在言清霄的脑海里回响,最终化为了更深的烙印,刻印在他的灵魂之上。
“我,会,找到你……”那声音的语言越发流利,“无论,你逃往哪里……你将为我,奉献自己。”
言清霄在极度的眩晕下产生了某种错觉,他能感觉到小腹里不知何时反扩进了一缕微弱却极其明显的暖意。他在这微弱的温暖里竭力擡手,捉住谢寻安冰冷的小臂,呼吸急促地要揭开自己的盖头,亲自看一看眼前的谢寻安究竟是什幺,亦或是成为了什幺。可谢寻安仿佛终于恢复了意识,唇角勾出一个漠然却自嘲的笑,五指不容置喙,轻轻压住了言清霄面上被泪湿的盖头。
“回去吧……清霄。阿珏在等着你呢。”
这是谢寻安原本的声音,原本的语气。言清霄愣住了,还想追问,却被谢寻安轻轻一推肩头。刹那间梦境破碎,无数氤氲着红色的碎片飞舞在更加深沉的黑色之中,言清霄感觉到自己在急速下坠,他坠入了意识的深处,难以抗拒地进入了更深的睡眠。
……
“嫂嫂……?”
长夜烬明,蜡烛燃尽,只剩一个苟延残喘的尾巴,斑斑烛泪堆满了灯台,掩盖住精心雕琢的纹饰。谢寻珏在晨光里探了探言清霄汗湿的额头,感觉到原本烫手的热度已然退却,他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口气,扶着言清霄的腿根,缓缓地退了出来。
被使用过度的地方红熟地肿胀着,好像一团倒翻的花,湿漉漉地绽放在言清霄的双腿之间。乳白混合着清液流淌而出,谢寻珏的眼神落在言清霄一片狼藉的腿间,就见那原本白皙的牝穴被撞得脂红一团,内里黏膜红润湿软,紧蹙的穴口已经没力气合拢,浪荡得用指头抻开就能瞧到软乎乎的宫口。
言清霄在梦中若有所感,怕人瞧似的,双腿颤抖着要并拢,可谢寻珏握着他的膝盖,轻而易举就把他的挣扎镇压。他一直看了很久很久,视线描摹过言清霄的狼藉,最后落在那张看过无数次的睡颜之上。直到晨光大彻、门外响起仆人走动的声响,谢寻珏才攒足力气移开视线,妥帖地帮言清霄盖好被子,然后利落地穿衣下床,吩咐廊外的仆人准备热水,洗去一个旖旎却沉默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