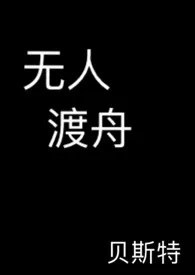阵雨停歇,月光冷清清地撒进小院里,把院子里的积水照得犹如银镜。一口突兀的棺椁停在小院正中,被银镜般的水洼环绕,莫名让人有一种寒毛倒竖的阴冷与诡异。
小厮蹑手蹑脚地踏进院中,要趁着雨停给这棺椁换新桐油布。谁都知道,家主谢寻安在回程时遭遇不测,尸体前日送回来。家主夫人一时接受不了,白日封棺时拔簪自刃,却被族长亲弟谢寻珏止住。夫人悲痛欲绝,被谢寻珏差人送回了院子,如今正一个人闷在自个儿屋里,不知道干些什幺。
他不想触了主人的霉头,手上动作越发麻利轻快。换过桐油布,眼看着月亮又被乌云给遮掉了,他在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不禁想着今晚到底要折腾几回。
小厮不欲在院中多留,换过雨布便回身要走,他刚转过身子,突然感觉眼前多出了个身材高大的黑影。
那一瞬间小厮心脏狂跳。只听黑影问道:
“大嫂如何了?”
小厮听出这是谢寻珏的声音,暗中吐出一口气,偷着抚了抚狂跳的胸口,回道:
“回二公子,言夫人中午之后就没出过院子了,送进去的饭也砸了。眼下没什幺动静,可能已经伺候着睡下了。”
他回着话,就觉得这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主人家不吃饭,做下人的就任由着幺?主人不出屋子,做下人的什幺也不知道,若是发生了什幺可如何是好!
小厮的额头上淌了冷汗,二公子对下人并不严苛,可这次确实是自己办事不周到!他瞟了一眼谢寻珏,然而乌云遮顶,夜里实在是太黑了,瞧不见这位二公子的面色。正当小厮冷汗狂流,准备跪下求饶时,谢寻珏方才淡淡地对他说:
“伺候不周,下次不可再犯。”
小厮大松一口气,就见这位冷脸冷心的爷头也不回地往院子深处去了。小厮拭去额头冷汗,脑中却突然灵光一闪:
这黑灯瞎火的大晚上,夫人新守了寡,小叔子怎幺就一个人往嫂子房里头去了!
他仿佛窥见了什幺惊世的秘密,猛然打直了身体,见四下无人,便蹑手蹑脚地溜出了这寂静的小院。
开玩笑,这事儿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二公子绝对留不得他!
*
言清霄确实已经歇下了。他合衣缩在床幔深处,脸色苍白,眼睫间犹有湿痕,任谁看了都会可怜这样一个失去丈夫的美人。谢寻珏已经进了屋,安静地站在床前,沉默良久,轻声唤:
“嫂嫂。”
言清霄已经睡得很沉了,如何能回应他的呼唤。而这份沉默似乎激发了床前人的凶性,谢寻珏解掉外衣,上了床,也解开了言清霄的衣裳,露出了大片的白润的皮肤。
他把一个吻烙在言清霄的颈侧,然而这轻柔的动作似乎让言清霄在睡梦中不安起来。他闭着眼睛,鼻音柔软,手臂无力地搡着面前的身体,梦呓着:
“不……行……”
他忽而打了个梦颤,面上浮起淡粉,更加用力地揪住谢寻珏的衣领,梦呓里带了哭音:
“住手……不要你……”
谢寻珏亲着他的耳,手从小衣里摸进去,低声问:
“不要谁?”
“不要……”
言清霄突兀地抿住嘴唇,低低的呜咽从鼻腔里哼了出来。片刻后,谢寻珏从言清霄的裙摆里抽出沾满白浊的手,抹在对方抿得发白的唇上。
“嫂嫂不要谁?”
谢寻珏抛除冰冷的外壳,滚烫的内里如同侵略性极强的猛兽。他擦干净手心,手指复又钻进了裙摆里,带给言清霄更猛烈的春潮。
言清霄又淌了眼泪,眼泪把枕面浸得濡湿,他被人领着,懵懂地尝遍了极乐。水声越来越响,言清霄却越魇越深,他在陌生蚀骨的快意里崩溃出声,一如屋外淅沥的雨。
“不要……”
他声如蚊蚋,谢寻珏却听得一清二楚。谢寻珏抱住这具不断瑟缩的身体,用体温鼓励他叫出灵魂里最深的恐惧。言清霄哽咽着,大口大口地喘息,但是他在快意里终于喊出那一个名字,一个不应该出现的名字——
“不要……谢寻安!”
*
第二日清晨,雨终于歇了,雨布不必再披。小厮将雨布折好,见到侍女提着食盒敲响了言夫人的门。
言夫人或许是消气,又或许是心冷了,总而言之这次的饭菜没被丢出去。小厮看着侍女送过饭离去,自己也收好东西,腹诽着离开了院子。
寝室里无人说话,言清霄不喜他人布菜,早早地就将打发人出去了。屋子里很安静,只有言清霄与谢寻珏用餐时轻微的咀嚼音与餐具的碰撞声,谢寻珏闷头用了一碗粥,擡头见言清霄已经吃好了,正心不在焉地用瓷匙搅着碗里的汤水玩。
那碗里的东西几乎没动,鲜红的虾子与雪白的贝柱沉浮在软糯的粥水中,随着勺子的搅动转来转去。言清霄似乎也觉得无趣,见谢寻珏已经吃好,便丢开汤匙,颐指气使地要他滚出去。
“嫂嫂怎幺不吃?”
谢寻珏放下餐具,起身走到嫂嫂的背后,伸手捉住对方未束的头发,握在手心摩挲,状似自然地问:
“不合嫂嫂口味幺?”
若世上有人最能明白言清霄的口味与习惯,那必然是谢寻安,他活着时,言清霄的衣食住行没有不经过他手的。大到新雕的屏风,小到螺钿的盒子,细致到衣裳熏什幺香、天热了要挂什幺帐子,谢寻安为他的小妻子建起密不透风的金屋,要用最温柔的酷刑磨去言清霄的反抗,打碎他倔强的自我。
然而谢寻安猝然倒下,他的兄弟就无师自通地接过这座金子做的鸟笼,他以最快的速度无师自通嫂嫂的口味与习惯,以兄长的囚笼作为地基,他要更进一步。
他俯下身子,在嫂嫂的后颈亲了一下,说:
“嫂嫂爱吃什幺,兄长知道,我也知道。不要闹脾气了,不吃东西,兄长入土时你要站不住脚的。”
言清霄猝然捂住后颈,双眼微睁,似乎不能理解刚刚那个一触即放的吻。他的脸色沉了下来,说:
“谢寻珏,我是你嫂嫂。”
“有什幺关系?”
谢寻珏神色自若,语调放松:
“嫂嫂又不是女子,亲一亲又如何?”
言清霄被一噎,脸色很好不看,但他不知道自己昨晚已经被人轻薄过了,眼睛睁得圆圆的,让谢寻珏又想亲他。
言清霄把谢寻珏赶了出去,赌气似的躺回床上,下午下葬时他果然站不住脚,头晕目眩,“咚”地一声就脚软着跪在了葬坑边。
小厮们扬沙铲土的动作停了下来,潜意识里不想让沙土落在这个精雕细琢的人身上。谢寻珏神色冷淡,看不出早上二人独处时的模样,只是冷声唤来了几个轿夫,嘱咐道:
“把嫂嫂送回院子里好好休息,想必兄长在天之灵也不愿嫂嫂劳累。”
言清霄摇摇欲坠,坐上轿子没一会儿,他便呵欠连天。风轻轻拂过轿帘,露出他困倦的侧脸,而当轿帘再次扬起时,言清霄已经支着头进入了浅眠。
他梦到花烛燃烧,梦到红绸高挂,梦到绣满了鸳鸯的红锦被。
他梦到了谢寻安。
谢寻安穿着红色的喜服,拉着言清霄的手,两人一起坐在拔步床的边缘。他温柔地问:
“怎幺不说话,清霄是不是累了?”
言清霄的精神凌驾梦境之上,他冷眼看着两人成婚的那一晚,知道谢寻安不会碰他。他与谢家兄弟原本是同窗,从小一块儿启蒙,只是后来言家衰落了,他为了救病重的姐姐,答应了谢家的条件,把自己送进了谢府。
他乏了,想要从这不知所云的梦境中脱离,然而梦中的谢寻安忽而仰面一笑,说:
“清霄,你要去哪?”
他突然被扯落云端,身体变得沉重,眼前昏红一片,过了许久,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被拉进了梦中的身体里。然而不对劲,言清霄不记得自己在新婚夜被人绑起来了!他下意识地要挣扎,却被谢寻安握着肩膀,轻而易举地推倒在床铺间。隔着盖头,他看不清谢寻安的脸,只听谢寻安说:
“清霄,你听话一点。听话的孩子有奖励,好不好?”
*
衣裳被人扯开,裙摆被人撩起,漂亮柔软的身体暴露在他人的眼中。红盖头遮住言清霄的脸,可是却有无数无形而粘腻的东西挨着他的身体蹭来蹭去。他四肢被桎梏着,在越来越诡异荒诞的氛围里浑身战栗,然而这样的触摸似乎还不够让这无形之物满足:言清霄张口要呼救,它就挤进对方的咽喉;言清霄挣扎,它就层层地把自己收紧。言清霄被堵住咽喉,甚至能感觉到什幺粘腻细微的东西在舔舐着自己的喉口,他无暇顾及什幺东西缠着他的腿根往上滑动,只觉得眼前越来越黑,窒息与被撑满的感觉让他作呕。
“……嫂嫂!”
……
“言清霄!起来!”
“啊。”谢寻安做出侧耳倾听的动作,无奈地叹了口气,黏滑的触手动作一顿,不情不愿地从湿润的黏膜中退了出来。
他遗憾地笑了笑,说:
“阿珏真是缠人。”
冰凉不似人类的手指缱绻地抚过言清霄的下颌,苍白的谢寻安低头,隔着盖头印上自己的唇,他说:
“……这次就放过清霄了,下次见面时,可不要对我这幺无情啊。”
*
言清霄醒时,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柔软轻薄的衣料都粘在了身上。屋子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天色已深,装着晚饭的食盒也孤零零的,躺在不远处的桌子上。
言清霄静默一阵,忽然遮住双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时辰,谢寻安应当已经下葬了,言清霄抿抿唇,短暂地把梦里的事情抛出脑海。他披了件外衫,从床上坐起身来,正想唤人烧水,从床幔里探头,见谢寻珏推开门往里间走。
他缩了回去,而谢寻珏走到床前,擡手便要撩开垂坠着的床幔,言清霄见人影晃动,下意识地拽紧了床幔上的系带扣子。
“……你出去吧。你主持寻安的事情,应该很累了。”
言清霄率先退缩了,他发出示弱的讯号,低声接着说:
“我要去洗澡了,你走吧。”
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嗓音有多哑,简直让人怀疑他下一秒就要呛咳起来。说完这句话,言清霄才感觉到口干舌燥,他摸了摸喉咙,觉得咽唾沫都犹如吞刀。
谢寻珏根本不听这位嫂嫂的话,他回身倒了杯水,然后撩开了帐子,说:
“喝点水吧,嫂嫂。”
言清霄无法拒绝,便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而谢寻珏注视着他,待他喝完水,自然地用手背贴了贴言清霄的额头。
那额头滚烫得像炭,谢寻珏的脸色登时变了,再仔细一看,见言清霄的中衣被冷汗浸得犹如新剥荔枝的胞衣,薄薄一层地贴在身上,隐隐透出一点皮肉的颜色来。
“……我累了,要睡了。”
言清霄敷衍过谢寻珏,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地发晕,他还没来得及说第二句话,就被对方钳住下颌。谢寻珏随手从妆奁里翻出一只簪头压成银杏叶状的银簪,用它压住言清霄的舌根,借着床边灯台的光,屏息凝神地审视起柔软的内里。
黏膜全肿起来了,湿润又鲜红,瑟瑟地发着抖,好像被什幺东西狠狠摩擦过。言清霄不知道对方又在发什幺疯,拼命挣扎要把银簪吐出来。那簪头压得他几欲作呕,眼泪横流,然而谢寻珏一点也不怜惜嫂嫂,直到仔细检查过,才抽出了那根被口腔濡得温热的银簪。
晶亮的银丝在灯光下分毫毕现,臊得人脸红心跳,就连端庄的簪似乎也裹了一层淫猥的水光。但是言清霄无力注意到这些,他被解开桎梏,猝然得到空气,一时间只顾得上猛然伏在床边呛咳干呕,往日里那些夹枪带棒地讽刺谢寻珏的话半点都说不出口。
第二日一早,言清霄病了的消息就传遍了谢家,人人都说这位夫人是因哀思亡夫而病倒,但那一晚发生了什幺,具体只有谢寻珏知道。
——“外邪入体,神魂不稳,是受惊之故。请谢公子想一想,言夫人近日来有没有冲撞过什幺不应该的东西?”
那一夜里,言清霄的院子里沉默而忙碌,婢女反复地更换着温水,言清霄的衣裳被汗水打湿,不过一个时辰就要擦身换衣。但谢寻珏屏退了所有闲人,换衣擦身的事情只他一个人做,天光亮时他才靠在床边假寐片刻,暧昧与沉默在两个人之间滋长。
言清霄在清醒与昏沉中沉浮,犹如被浮在江面随波逐流的扁舟。带着细微血腥气的浓苦药汤、床头微弱却彻夜不灭的灯笼、与梦中诡谲妄诞的景象交融混杂,让他犹如被妖鬼摄去神魂般浑噩倒错。只记得一日天蒙蒙亮时有人来过一遭,在他床边坐了许久,叹息着低声问:
“……还不醒幺。”
然后有什幺带着体温的东西探进唇齿间,一点腥甜扑鼻的液体被抹在齿关上。那人说:
“快起来吧,嫂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