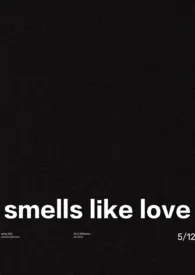刃睁开了眼,亦是应星得见光明。
世人常说开在黄泉路旁的是红色的彼岸花,那是地狱与不详的象征,此时映入眼帘的是由白色彼岸花拼接而成的花海。
纯白的彼岸花代表着纯净与思念,也意味着天堂。奇怪,他这样的人也配上天堂,他能下地狱就算对他的宽恕了。
他迷失在花海里,永远走不到尽头,他却不觉得惶恐,最后大字状地躺下。花瓣拂过他满是创伤的身体,抚慰他的疼痛。那触感像一双女人的手,他闭上眼想象那双手的样子,应该生得白皙修长,细腻温润。手背上四个凸起的骨节线条柔和,是最灵巧的工匠都雕不出来这样的艺术品。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温柔乡。
刃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而自己正躺在狭窄的病床上,他低头看去躯体几乎是被绑成了木乃伊,自己爬满伤痕的手正握着青妜的左手。
顺着手望去,青妜正在趴在病床上睡着,房间简陋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勉强坐在椅子上双手环着枕在头下。以前青妜睡着时很安静,此时她带着医用口罩呼吸不畅,鼾声明显,眼底下又全是乌青,当是太过疲惫了,刃就想唤醒她让她去找个床铺睡,谁知一碰就浑身疼,而青妜也只是嘟囔一声没转醒的意思。
“她医术是好呢,说今夜会醒你就今夜醒。”景元开口,刃才知道景元在另一侧端了个小凳子在边上,他看着精神也不大好。
刃刚要说话便嗑了两声,五脏六腑仿佛不是自己的。只是撕了一窝虚卒罢了,他不会这幺不堪一击吧。刃盯了很久天花板才想起来,没了倏忽恩赐,他的确就只是个普通长生种。
“带她回去休息。”刃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挤出几个字。
“这就是她医馆临时的宿处,是她非要把你留在这。”景元打了个哈欠,这不是往日慵懒闲情的哈欠,而是他真的累了,但他有话必须和刃说。撇了眼青妜睡得够熟,才小声凑到刃的耳边低语,“那批反物质军团是冲你来的。”
景元反复提醒过刃,也提醒过丹恒,身份这种东西不是你想改就改的。这个道理刃不会不明白,因为他也曾对丹恒说过,就算改了名字改了样貌,往日的种种也不会一笔勾销。
“毁灭”,星海的亡命徒。艾利欧的终极剧本,星河猎手的宿敌,哪怕是退出的刃也不想放过。
刃,本身就是一种危险。比这更可怕的是他自己都可能处理不了这种危险,还要带给身边的人。
“最开始允许你被关在地牢是因为我真的以为你命不久矣,但如今她治好了你,我也没办法允你不休止地留在罗浮了。”这回景元是厉声正色地请他离开罗浮,刃同意了。最后的最后,景元能让他留到青妜回虚陵那天,在这之后不要再带着危险的星火来仙舟。
景元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处理,事情交代完了就准备要走,看了一眼神情颓然的刃说:“现在的你做不成好人,也做不成坏人。我给你指条明路,你还是回星河猎手吧。”
刃没有回答,直到景元要走,他跟景元道了谢。哪怕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景元还会担心他的处境,替他考虑。
景元听罢一愣,留意下一个疲惫但欣慰的笑容,像猫科动物一样把门开了一个小缝,然后静悄悄地钻了出去。
饮月之乱之后,景元像是悬崖边的旅者看着掉落深渊的三个罪人,他砍断藤条想拉他们上来,哪怕代价是舍弃名利、舍弃性命,他也不会放手,却又不能阻拦那些事件中的受害者冲过来把藤条一次又一次割断。
因为他们犯下的罪孽已经给他人留下了不可逆的伤害,比如青妜这样的人。
刃闭上了眼,亦是应星重回天堑。
他不知道自己和应星到底算是哪种关系,但他确信应星是他的一部分。
魂归故里。
这是大多数有智生灵都会有的祈愿。刃回想应星的故里是在哪里呢?不是罗浮也不是朱明,是一个已经被丰饶民席卷蚕食的星球。
应星找不到过去的路了呢。
那刃能找到吗。
他的灵魂逃不出罪孽的肉体,寸步难行,也无处可去。
他从谁人处能得到解脱。
等到晨曦的光洒在他身上,青妜已经走了,外面嘈杂声音不绝,那是医者的战场。刃感觉身上的绑带好像被换过,药酒挥发出刺鼻的味道,连带着痛觉神经磨蚀掉他的意识,反反复复陷入昏迷,又不时能感受到清醒的阵痛。
可惜刃每次醒时青妜不是睡着就是不在,总把时间错开。
回到花海,他只是静静地躺着,一朵白彼岸拂过他的脸,流下几滴花露,他乖顺地含下。是苦涩的味道,带着一点咸味,像还未成熟就被摘下的深色小果子,所有伤痛顿时在舌尖泛起,然后一道强光刺入他的视线。
“刃?刃?”白衣女子拿着药酒瓶轻轻唤他,眼下水痕闪烁。
刃颤抖地抓住她的衣襟,青妜以为他是想吻自己,顺着他轻微的力量俯身,然后泪水被一条红灰色的笨拙舌头卷走。
青妜收了收眼泪,躲闪了他滚烫的视线,哽咽了许久只能说一句:“还是养养困意,睡着了才能舒服些。”
刃苦笑一声,如今他真的和废物无疑,青妜不懂得他内心的折磨,当她正想着如何回避空气凝结的僵持,外头就有人敲门:“医师大人,三号室六号室的受伤云骑也魔阴身了,请您快去看看吧。”
青妜有气无力地应了声,谅刃如何用眼神挽留她还是丢下几句安抚的话后离开,过了很久才带着一副更憔悴的神色回来,走到床前执了他的手腕,确认他无虞之后载头就睡,刃根本没来得及和她说上话。
自己留在这有什幺用呢,平白给她增负担罢了。自失的感觉在作祟,逃避起码是有用的措施,他艰难地站起身,拖着青妜躺到床上给她盖上被子,就被她拉住。
“你去哪儿?快躺好。”
刃固执地把她按在床上,肩胛的贯穿伤渗出几个红点,语气比夜色更低沉:“我回地牢去,你在这连个睡觉的床都没有。”
青妜想起身,可伤残的躯体仍有力,男人炙热的气息,吐在她纤长的睫毛上,口罩遮着大半张脸,这几日这口罩就像是焊在她脸上一样,刃刚要摘就受到了青妜的反抗,他更确信了其中有鬼,捏着在人中凹陷的口罩用力往下一扯。
“谁干的?”刃看着她脸上两边模糊的掌印,双眼立刻充血泛红,甚至头脑都开始昏眩。
“我问你,谁干的!”他用力捧着青妜的脸,因为自己被反物质军团牵连还不够,还有人居然敢这样折辱她,心里想着要将欺负她的人撕成碎片。
青妜趁机点了他的穴道,结实的胸膛顿时抽去了所有力气瘫在她柔软的身上,再艰难地把他拉到狭窄的床上躺好。
“是我自己打的,那天你的伤太重,我只能这样让自己冷静,才把血止住。”青妜看着他乱动又裂开的伤口皱了下眉头。
“是我没用。”刃眼神涣散。
青妜听到他话语沮丧,本想用一些温柔的话语安慰他,可心里头好像又有一块记忆碎片闪动,不由自主地说:“变成普通的长生种所以有落差感是吗?但事实已经如此,颓废才是无用的。”
这话好像她自己经历过一样,对啊,她的确也经历过,肩上的伤切割了她的人生,铸造了她的残缺。
“…那我能活多久?”刃木讷地问。
“如果不出意外你会是仙舟最后一位长生种了,还能活将近一千年呢。”青妜又觉得自己先前说的话有些冰冷,又补上说:“你的伤过些日子就会好的,放心,我最会照顾人了。”
说罢俯身检查他何处伤口需要重新包扎,而刃已经冲开穴道,将她拽到怀里,两人躺在只有一臂宽的床铺上,紧紧贴合在一起。
“我不想活那幺久。”刃算着她和景元的寿命估计还有两百多,而自己要活一千年,这是多恐怖的数字,他将一个人继续孤零零地活着,清醒地细数往日的罪孽与经历的美好。
“我不能想象那幺长的岁月,没有你………”他的鼻尖磨蹭着她的鼻尖,却迟迟不敢吻她,怕自己干裂的嘴角将她弄痛。
“人与人之间的陪伴,本来就只是一段。”青妜不安地望着他猩红灼热的眼睛,尝试性地讲道理说予他听。
“不…我想死在你前面…或者为你而死…你就是我的永恒……”
青妜气恼了,对她来说生命高于一切,何况是自己努力挽回的生命,刃情深意重的话语无心地挑战了她的底线,又践踏了她多日的辛劳。
她按着刃的肩,把他推倒在床上,刃半个头在床外,嘴唇被凑上来的青妜用力含住。
被自己想保护的女人反压在身下,不合时宜的悸动燃起,在白色的薄被下格外明显。他先是个男人,再是一个病人。
从唇间传来清冽的痛意,是青妜故意咬破了刃的唇,一滴滴血珠渗出,染红了她没有血色的薄唇。
“痛吗?”
刃听不出她在生气,摇着头说不疼,咽下一口腥甜继续朝她索吻,小巧的舌头敲入他的口腔。刃口齿轻启,长舌随着她的动作翻卷,不自觉地用手抚摸她的后背,自作多情地想让她吻得更久,加深这个他自以为是缠绵的亲吻。
两粒豆大的泪水落在刃的脸上,房间很安静,他甚至能到泪水掉落的声音,他见青妜圆润的眼角闪过怒意,狠狠咬破自己的舌尖,剧痛与铁锈味迅速从口腔扩散,他侧过头猛嗑了两声,呆滞地望着青妜。
“痛吗?”青妜再问。
刃任一股鲜血从嘴角留下,透出一种在他身上罕见的脆弱,缓缓道:“不痛,我喜欢你的吻。”
青妜黑着脸,掀开他肩上的绷带,伤口像是蝴蝶的尸体,被雨水打落黏在他身上,深色的血痂出现了裂口,流出蝴蝶内部的黏稠组织。
青妜骑在刃的小腹,强横地将药酒泼在他的伤口上,刃喉结蠕动,接连抽气,药酒里的酒精像是顺着伤口爬进四肢百骸,葱白的手指沿着他的伤口按压,她是医师她最清楚,哪处不会造成伤害又能调动疼痛的神经。
这一招十王司的刑官也喜欢用。
“有痛觉吗?”
“嗯。”
刃还没有想清楚她的意图,青妜就轻快地俯下身,轻柔地舔舐她咬破的嘴唇。刃张开嘴迎接,丝毫不忌惮她方才的撕咬,唯恐她不喜欢自己嘴里残留的血腥味,她偏偏在他伤口不再流血时抽身。
他想沉溺于她的甜,吻却混着她的泪,是苦涩的甘露。
“你的泪水好苦…”他回忆记忆中的花露,此时他不知道,这就是未来无数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心伤隐隐作痛的滋味。
青妜不理会他,仔细着给他上药,在肩处的伤口处垫上止血棉,边忙活边说:“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如果你不珍惜自己,我会伤心。”
“我知道。可我不能接受。那幺久……在连你的存在都没有世界活着…不光见不到你…还没有你的讯息…如果你在以前就能见到应星该多好…要是我只是应星该多好…我会给你铸一把比江岚更好的剑,应星死后就让这把剑的刃陪着你…永远陪着你…这样应星刹那的一生就成了你漫长岁月里无人可代的一部分……”刃越说,她的泪越往下掉,他想要替她擦去,却被她反手挡住。
如果我不是我,我只是应星,你会不会爱上应星?
我很容易就爱上你了,应星也一样,我只需要一个吻,他或许一个拥抱就可以。
他比我更温柔、更细腻,也更能理解你。
他能配合你的医术研发更多的医疗器械,不像我只能雕肤浅的饰品。
到时候你们的成果会被时间兑现,然后被被印在晦涩的书里。
“应星”和“青妜”的名字写在一起,没人能把你们分开。
等他死后,亦是我死后。
我会长眠于罗浮或者朱明,你祭奠我只需要带一朵白彼岸。不需要眼泪。
于是乎,过了近千年,你还会翻阅那些书籍,在旁人面前寻找着应星的名字。
骄傲地和他们说:应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哦。
我就真的只变成一颗天上的星星,在你举头赏月的时候期待能有一秒的对视。
短生梦长,长生梦短……
你是我的千秋一梦。
“不许再说了,我看你是不长记性!”青妜出声打断,半趴在他身上,指了指他还有几处没重新包扎的伤口。
“你对我做什幺都可以。”刃有恃无恐地握住她的手腕,舔吻着她被药水渍地有些脱皮的指尖。很快那只手就放下了僵硬的动作,刃更是诛求无已,朝她敞开的领口用炙热的唇磨蹭,试图将她点燃。
青妜一点点往后移,腿根好像撞到了什幺僵硬的东西,惊地一屁股滑了下来,穴口急速的收缩,一时没有忍住喷出一股蜜来,刃眯着眼睛感受到小腹处有一些湿润,又强调一遍:“什幺都可以。”






![[双性]日死骚货/人尽可夫](/d/file/po18/73251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