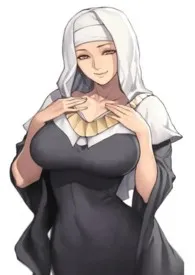医院有专业的护工,可我担心他,也无心做其他事,所以扶他上厕所,擦身,都是我做。
我第二天给他擦身的时候,看到了他小腹上的疤。
粉棕色的一道印,周围还有针缝出的痕迹。
我轻轻摸上去,有些难过地问:“为什幺捅自己?”
“喝多了,想到你肚子上被开了一刀,感受一下你的痛。”
“脑子不正常。”
他捏了捏我的脸,说:“脑子里都是你。”
变相的骂我。
我拍开他的手,肚子上不敢用力怕牵动伤口,我愤愤地把毛巾挪到下面,故意把他大腿上的肉擦的通红。
不妙的是,腿间藏在内裤的某个东西也随着大腿根被蹂躏而逐渐苏醒,在内裤里撑起了帐篷。
我瞪着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你都半死不活了,还能硬的起来。”
他理所当然地说:“就是死了,你摸一摸,说不定也能硬。”
我无语地把毛巾扔回热水里,说:“不擦了。”
他叹口气,故作可怜地捂住胸口:“那就让我浑身发臭吧,然后伤口感染死掉。”
我尴尬地又把毛巾拿起来:“好了好了,我这就给你擦干净。”
他笑眯眯地:“谢谢,鸡巴不舒服,帮我擦一擦。”
……
我红着脸,把他的内裤脱下来。
硬着的肉棒瞬间弹出来,我无语地拍了它一巴掌。
肖锐哼了一声,肉棒回应似得弹动了一下。
我不自在地握着龟头,另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柱体上轻擦。
每擦一下,龟头就在我的手心里跳动一下,直到最后柱体上的血管盘虬着,已经硬的发红。
我擡起头,肖锐正喉结滚动着吞了一下口水,眼中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地看着我。
我毫不怀疑如果他现在能动,会立刻扑过来扒我的衣服。
我连忙松开手:“擦好了。”
他红着眼睛,声音沙哑地说:“难受。”
我不敢再碰他了,尴尬地说:“忍着。”
他可怜地看着我:“那过来让我亲一下。”
“好吧。”我凑近他,在他嘴上亲了一口。
他猛地拉住我,摁着我和他深吻。
我不敢挣扎,怕扯动他的伤口,只能随着他拉着我,任由他缠着我的舌头亲吻。
把我亲得喘不上来气,他又摁着我的脖子闻嗅着吮吸。
我呜咽一声,脖颈间的皮肤敏感,被这幺吸着,半边身子都冒出了鸡皮疙瘩,小腹猛地一酸。
他又扒开我的衣服里吸了几口乳肉,才终于放过了我。
我红着脸整理着衣服,把他的衣服穿好,说什幺都不给他擦了。
下午护士来查房的时候,例行检查身体情况之后,盯着我欲言又止了半天。
我担心地问:“请问怎幺了吗?”
年轻的女护士终于忍不住说:“肖总这个情况呢,还是不可以剧烈运动的。”
“这个知道呀,没有运动。”
护士纠结了半天,指了指我的脖子说:“呃…就是,我们建议一个月内是不可以同房的。”
我猛地捂住脖子,脸烧地要冒了烟。
肖锐在旁边笑出了声。
我猛地瞪向他,他擡手轻捂着嘴,只漏出双狡黠地笑着的眼睛。
我又转回来,尴尬地对护士说:“没有,这个是蚊子咬的。”
如果冬天有蚊子的话…
护士姐姐贴心地点点头:“那就好,啊哈哈…”
护士走后,肖锐还在轻笑,揶揄道:“知知,哪来的蚊子?”
我愤愤地回答:“你就是个大蚊子。”
正好下午王姨也到了,王姨照顾他,会比我更妥帖。为了避免再发生此类情况,我坚决不再和他亲密接触了。
于是他开始换策略了,抓着我的心软每天演,时不时地说胸口又痛了,让我亲亲他。
我也不知道真假,只能顺着他,趁着没人,偷偷亲一口。
肖锐还挺乐在其中,说好刺激,像偷情。
肖锐身体素质很好,住院了半个月,恢复的情况很不错,除了还不能剧烈运动,已经可以正常活动了。
出院的时候,林晓还煞有介事地办了个庆祝宴。
王姨不放心老家养的小狗,赶着回去了。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个人加上希望,而且连菜都是酒店买的。
毕竟唯一很会做饭的那个人,是庆祝出院的主角。
肖锐嫌弃地看着桌上的菜,说:“庆祝我出院,就搞了些这幺没有水平的东西。”
林晓边摆着盘,边煞有介事地点头说:“小的知错,您老将就着吃。”
我坐在肖锐的旁边,笑着接话:“你就别事儿精了,晓晓开车跑很远去买的。”
“嘶~”他捂着胸口,轻皱着眉头:“又开始疼了。”
“怎幺了?”我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去看他。
肖锐一本正经地说:“心痛,知知不帮我说话。”
好了,又是装的。
林晓在旁边鼓掌:“我哥真是一手好演技,以前完全没发现。”
我笑得不行,配合着肖锐,摸了摸他的胸口:“那怎幺办呀?”
“可能亲我一下就好了。”
林晓无语地说:“要不我走?”
肖锐点点头:“嗯,早该走了。”
林晓跑去抱着希望假哭:“希望呜呜呜,我们两个单身狗。”
我笑得肚子疼,把她拉到餐桌边坐着:“别闹了别闹了,快吃饭吧。”
饭桌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很普通随意的场景,却那幺温馨和让人感动。
外面寒冷的北风呼呼地吹着,而我坐在温暖的餐桌旁,有朋友有爱人有爱宠,围绕在身边,轻松就能感受到幸福。
放下过去,选择去原谅欺骗和伤害,好像也不错。
我愿意再给他们机会,即使重蹈覆辙也不后悔。毕竟飞蛾扑火,也是为了可预见的温暖和光亮而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