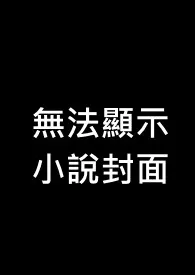天色渐暗,被堵在燕京北城门口的宁王一行自是越发焦急,兵变失利,能追随他杀出皇城的不过寥寥,他所能倚仗的,只有这位摩尼教的色骷髅护法,可偏偏色骷髅又被那阴魂不散的吕家小子给牵制着,如今他杵在城门附近不敢妄动,只得期望色骷髅能快些收拾了吕松,再带着他逃回宁州。
“狗贼,纳命来!”
然而宁王哪里会想到,他等来的不是摩尼教的支援,而是一辆飞驰而来的机关椅,千机无尘目光凌厉,只一眼便瞧清局势,也不顾激斗正酣的吕松,只先将琴无缺置于路边,而后便驾着她的神机车椅飞身而来,只空中一记钩锁跃动,声势浩大的机关椅便已杀至宁王近前。
“救……救我!”宁王急得大声呼救,好在此时色骷髅有所感应,拼着被吕松重伤一剑的势头强行撤招扑向千机无尘,凌厉的钩锁对上他的鬼手钢爪,只听得“滋滋”之声响起,色骷髅的钢爪竟是被磨出无数刀痕,不过他倒也拼救几时,虽是被这一钩锁打得节节败退,可总算将宁王护在身后,免于一死。
“逆贼。我看你今日往哪跑!”吕松见是千机无尘赶来心中不由大定,他追杀宁王与色骷髅于此,势必要将这二人擒下。
然而就在二人动手之际,城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嚣,二人定睛望去,却见着北门之外赫然杀出一路人马,虽只百余人众,可观其步伐皆是非比寻常,显然不是等闲之辈。
“宁王殿下,这一路,受惊了!”
一道洪亮的呼声响起,自城外而来的百余人马中缓缓走出一骑,此人全身黑袍,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阴森鬼气,虽是距离吕松、千机无尘百步之遥,可那森森气机却已是让二人警惕起来。
“原来是教主亲至,”宁王见得援军立时露出笑容,以这位摩尼教主的手段,即便不能让他反败为胜,自己也不会就此落入敌手。
“宁王且先走一步,宁州兵精粮足,卷土重来犹未可知,”摩尼教主言之凿凿,显然是未将眼前的二人放在眼里。
“那便有牢教主了,”宁王闻声大喜,当下便匆忙向着城门行去,而吕松与千机无尘这边自不会轻易容他撤走,两人同时飞身上前,可那摩尼教主却也早有准备,自战马飞身而下,双掌齐出,竟是朝着二人的攻势冲击而来,三人气机相冲,充盈的内力立时向外散开,竟是震得周遭百米掀起一层砂石,待得攻势暂退,三人均是向后退了半截,而此时的宁王也已随着那一路摩尼教众逃得不见踪影。
“哼,堂堂摩尼教主,竟是不惜以身犯险来救这丧家之犬。”吕松冷笑一声,眼中自是对这所谓的魔教教主十分不屑。
然而摩尼教主却是毫不示弱:“犯险?天下之大,却从无我摩尼不可踏足之地。”
“那便要看看,你今日能否活着离开。”千机无尘此时也已蓄势良久,随着语声落地,她那变化莫测的机关椅上骤然间分出四道钩锁,四条长绳牵引,便好似猛禽四肢一般灵活自如,她安然不动坐于椅上,紧靠着内息之力操控着钩锁飞舞,直向着那摩尼教主冲杀而去。
“他交给我,你小心那边。”
千机无尘自与这位摩尼教主战作一团,打斗之间却还能传声入得吕松耳畔,吕松陡然一惊,猛一侧身避开了色骷髅的暗爪偷袭,再度挥出长剑,自与这摩尼护法都在一起。
一边是浑厚掌力对上精妙钩锁,一边是御风长剑比拼钢筋鬼爪,摩尼教主内力深不可测,掌风刚猛,每一式都有开山震石之威,可他对上的千机无尘却偏不与他对掌,四条钩锁缠绕,既可闪转腾挪,又可多面攻杀,每每以弱诱敌,而又击敌不备,二人交手百余合下,四条钩锁虽是被掌力劈段两根,可摩尼教主的腰肩一带却也被划出十余道暗紫伤口,若非他早修得百毒不侵之体,此时便已被这钩锁上的剧毒要了性命。
而另一头的色骷髅窘境更甚,早在平山小县时,色骷髅与恶鬼无常联手都未能将他诛杀,如今吕松自军旅磨练一遭,无论剑法内力均是远胜当初,几番对招之下他已明显感觉不敌,当下也只好便打便退,然而吕松剑势愈发汹涌,长剑与他暗爪缠斗之时竟还能从袖口里飞出数道暗镖,好在他轻功不错,连忙收了爪劲侧身避让,可这番撤爪之势便被那长剑追出破绽,一剑划过,竟已在他肩头划出一道血渍。
“教主,我们撤吧!”
色骷髅强忍剧痛退至教主身侧,摩尼教主当下也不恋战,袖袍一挥,两颗黑石猛掷于地,只听得“轰隆”两声,二人所在之地散出一阵浓烟,虽是故技重施,可吕松与千机无尘也已缠斗许久,情急之下未得防范,被这浓烟狠呛了一口,一时间自是无法追击。
可便在他二人以为对方逃脱之际,耳边赫然传来一道龙吟虎啸之音,待得硝烟散去,二人目视清明,却见着摩尼教的两人却并未就此走远,而是呆呆的定在外城门口一动不动……
“教主!”色骷髅一声惨呼,整个人颓然跪倒在地,他哪里能想到,本该顺利逃出的大好时机,却是自天而降一柄青红长剑,长剑破空而下,饶是摩尼教主作出结掌御敌之姿,饶是被这长剑一剑破入肺腑,一招毙命。
“师姐?”
正自疑惑的千机无尘却是突然唤了一声,虽是剑气更胜往昔,但普天之下能有这御剑神威的,当然只有她那闭关修行的大师姐了。
果然,剑无暇自城外的阴影之中缓缓现身,依旧是那身白衣素服,依旧是那般高冷孤绝,她手中握着的只有空着的剑鞘,而她眼中望着的,却是倒在地上的摩尼教主。
“恭喜师姐出山,此番剑意更有龙吟虎啸之机,想来师姐的剑法又有精进。”千机无尘向来清高,可面对这位长她一位的大师姐却是格外敬重。
“不对,”剑无暇眸光一闪,语出惊人道:“他不是摩尼教主。”
“什么?”吕松闻言一惊,上前望着这黑袍教主的尸体上下打量:“他……适才宁王与那护法都称他为教主,而且,他内劲浑厚,武功远在……”
“平山县城楼,我与他交过手,他,绝非此等修为。”剑无暇收回长剑,双目微微闭合,脑中自是回忆起当初与那摩尼教主城头比剑时的情景。
“是与不是,此刻也不得而知,不如先将此贼带回山门,慢慢审讯便好。”千机无尘处事周全,此番大战之后皇家事务繁杂,念隐门人不宜干涉,自该及早退去为好。
“也好,”剑无暇微微点头,而后又将目光瞥向城内角落里的琴无缺:“师妹,就交托给你了。”
“师姐不跟我们一道?”千机无尘似是听出她话中意味。
“此番下山,杀意未褪,自该去宁州一趟!”
……………………
“沁儿!”
已然垂垂老矣的天子萧炳在众人的拥扶下一路疾行,直到萧沁所居的凤阳阁,见得殿外尸山堆积,萧炳再也控制不住心中悲痛,仰天长啸一声,就此晕厥。
护在萧炳身侧的麓王萧柏与世子萧琅一时也是面色冰冷,本该奉为主上的沁公主就这么突然没了,难免不让人心生腹议,立储之争演变多年,好不容易能在今日扫平这两王的祸根,却不想真正的祸患才刚刚开始。
“到底是怎么死的?”萧琅小声地询问着身侧的管事太监,可那太监也只得无辜地摇头,待得凤阳阁里的几位执勤宫女被押到跟前时,才有人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凤阳阁位处后宫深宅,要想攻入需得先破天子所在的嘉禧宫,故而萧炳也并未派重兵驻守,只留了约莫不到百余人,可谁知嘉禧宫那边的喊杀声都停了,这凤阳阁里却是突然飞来一位黑衣刺客……
“一个人?”萧琅赫然一惊,连声追问。
“是,是一个人,他……他不是人……是魔鬼……是魔鬼啊!”宫女显然已是被吓破了胆,独自一人冲杀百余兵士不留一个活口,一剑穿肠刺杀公主后又能消失得无影无踪,此等高手,甚至根本不用去猜。
“一定是摩尼教妖人!”
“宁王与摩尼教有勾结,见事已败露,当下便令杀手入宫刺杀公主,当真是歹毒至极!”
“此等乱臣贼子,切不可轻易放过!”
一时间群情激奋,对宁王乃至摩尼教的叱骂之声不绝于耳,唯有麓王萧柏面色阴沉,似是在思索着什么。
“沁……沁儿啊!”忽地,天子萧炳悠悠转醒,虽是满脸疲态,但却依旧强撑着病体去探视萧沁遗体,好一阵哭闹作罢,这才在太监们的搀扶下返回寝宫,至此时天色已晚,麓王连带着群臣纷纷告辞出宫,独留着萧琅所率的京虎营留守皇城。
萧柏快马加鞭一路疾行,直至到了王府见着府中管事后才直接言道:“快,快请季先生书房议事。”
季星奎来得很快,虽是没能参加诛杀二王的行动,但他于暗处调度兵马亦是同样重要,甫一进门,便见麓王满脸心事地靠在座椅上歇息,想来还是被宫中的事务所累。
“王爷?”季星奎唤了一声,萧柏这才惊醒,猛一起身,先是快步上前将房门掩上,而后便一把捉住季星奎的手臂小声说道:“以先生的武功,这屋外若是有人?”
“除非是念隐门、或是摩尼教的那般人物,旁人自是能够觉察。”季星奎也不拖大,仅只目光一凝,便能觉察出屋外动静。
“嗯,”萧柏轻轻点头,随即又退回原位,沉吟了些许时间,终是吐露出那将他吓得不轻的消息:长公主萧沁遇刺身亡!
“……”季星奎闻言亦是愣在原地,而后又是神色复杂地瞧了萧柏一眼,待察觉萧柏脸上的焦急神色后这才皱起眉头,他轻轻挪动脚步在周遭转了一圈,好半晌才算理清了思绪,继而向着萧柏行了一礼。
“先生这是何故?”萧柏见他行此大礼自是有些不解。
“王爷,在下有几事相询,还望王爷如实相告。”
“你与本王相交多年,难道还不了解我吗?我若有事瞒你,岂会此时叫你来议事。”
“那好,敢问王爷,沁公主遇刺,可与王爷有关?”
萧柏先是神色一紧,抬手举誓道:“绝无干系!”然而话一出口脸上又露出几许无奈:“先生既是能有此问,想必此刻天子心中,亦会对我有所猜疑。”
“确是如此!”季星奎叹了口气,可随即又目光坚定道:“可他却别无选择。”
“当今皇家宗室里,除了麓王你,又有谁能胜任储君之位,天子即便想另你他人,可又有谁能叫他安心托付。”
“……”麓王微微闭眼,心中更是五味杂陈:“可若真落到我头上,这天下,怕是要乱了。”
“那便让它乱吧!”季星奎咬了咬牙:“乱世已至,以王爷、世子的才干或还能为大明续上一命,可若是换上旁人,那大明才是真的要亡了。”
麓王再次踱了几步,一时间眼神里满是过往:“我自小生在东平府,得祖上恩典袭爵,靠着处处小心谨慎才有了今日地位,此番受令回京勤王已是风头太盛,要是真迈出那一步,却不知在这激流中能否全身而退。”
“王爷,非是季某贪慕虚荣,实是这天下,再容不得第二个宁、齐之乱了。”季星奎长叹一声,语声里满是落寞:“退一步讲,若是王爷退居东平府,他日新君继位,又真的能放心您这手握兵权的宗室王爷吗?”
麓王暗自低头,他何尝不明白季星奎语意真切,如今宗室之中论资排辈,怕是没有任何一人敢与他相提并论,若是他退守东平府,天子固然还能感他几分情分,可新君继位后,他便是当朝最大的藩王,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既是如此,还请先生教我!”麓王想通此节,当下也不再犹豫,再抬首时,目光里已带着几分决然。
“为今之计,首先要约束府中下人与军中将兵,令行禁止,绝不可犯雷池半步。”
“第二,目前时局动荡,贸然回藩自是不妥,但绝不该擅自入宫,幸得世子如今也受重用,可叫世子这几日多多入宫,天子若是有意,自会叫他来请王爷。”
“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王爷若与天子交心,绝不可谈志向抱负,多说些儿时回忆,尤其是对先帝,要尊崇感怀,如此,方合圣意。”
“最后,若是天子立了王爷为储君,王爷便要日夜侍奉天子左右,朝中事务一律交还老臣,至得一切尘埃落定,方可掌政临朝。”
“……”麓王缓缓点头,而后又是靠在椅上沉吟良久,终归是默认了季星奎的告诫。
……………………
第二日中午,果如季星奎所料,萧琅回府时便传来了圣上旨意,宣麓王进宫。
君臣二人叙旧良久,直至夜间才安排车门送麓王出宫,至得第二日早朝,天子便颁出了那道让百官苦等了二十年的立储圣旨:
自古帝王继天立极、抚御寰区,必建立元储、懋隆国本,以绵宗社无疆之休。
麓王萧柏自小温恭,常得先帝赞誉,才干过人,器度高明,深具元储之资,朕以为可,今将麓王过继于先皇名下,立为储君,望其以天下为念,勤政爱民,修德行善,不负先皇之托付。
尔等百官,宜协助太子政务,尽心竭力,以奉先皇之志,以顺百姓之心。
不可有所怠慢,违背朕旨!
圣旨全篇不过百余字,可对于满堂的朝臣而言无疑是一场轩然大波,天子病体难愈却迟迟不立储君,为的是扶持年幼的念公主上位,然而天意难违,一场宫变之后,宁齐二王一个惨死宫中,背上叛逆之名,一个潜逃在外,如今生死难料,可偏偏此时念公主遭人刺杀,几番权衡争论,最终是让宗室血缘最近的麓王袭了储君之位。
麓王自小住在宫中,先帝长夸其纯善,与天子亦是兄弟情深,回归藩地后既能谨守礼法,又能率军抵御边陲之乱,东平府久治之下民望颇高,此时立麓王为储,自是最明智之举。
然则再明智的选择终究敌不过是非之人,圣旨出台不过两日,宁州府传来消息,逆王萧度诛杀宁州府尹、知州等大小官员数百人,联合周边郡县一并举事,称麓王裹挟天子作乱,誓要发兵进京护驾勤王。
而几乎同一时间,齐州府齐王之子萧睿拥兵起事,集结齐州十万大军直奔燕京而言,扬言要为其父报仇,将麓王父子挫骨扬灰。
帝星衰微,乱象已起,整个朝堂上下仿佛都被阴霾笼罩。
然而即便是听闻如此风声,得封储君之位的麓王萧柏亦是没能出席第二日的朝会,自受封以来,萧柏便一概不理朝臣求见和各处拜会,只一心扑在皇帝身上,白日伺候汤药,每日必先尝,夜里便靠在皇帝的寝殿卧榻上浅寐一二,日日不缀,十余天来身子已是瘦了半截。
兄弟二人本就相交莫逆,到得此等时分自是更见真情,即便是天子有意让他来朝堂处理政务,萧柏也只是笑称:“天下事自有能臣照料,区区叛逆不过蜉蝣撼树,焉能动摇国本,只望皇兄能早日康健,柏愿亲率铁骑扫除叛乱,还得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皇兄皇弟自是相处融洽,每有动人事迹被宫人传出少不得一番赞颂,可唯独让如今统领政事的左相姚泗之听了恼火,好在萧琅已被封为“琅王”,如今也已有了入宫伴驾之权,诸多朝中事务倒是可以与他一并商议。
“姚相倒也不必太过忧心,无论宁州、齐州,当日宫变之后我父王便已下令诸府小心戒备,宁州贸然举兵,齐州军心不稳,只需择选名将,逐一击破不在话下。”萧琅早与府中的季星奎商讨多日,此番谏言自是中气十足。
“琅王似是已经想好了对策?”年迈的姚泗之轻轻抚了把长须,自是一眼看出萧琅的心思。
“确实瞒不过姚相,依我拙见,齐州相距冀州不远,如今鲜卑之乱已平,或可调遣冀州军入齐州平乱,据传那北地霜花用兵如神,深得镇北侯真传,有她坐镇平乱,想那萧睿也掀不起何等风浪。”
“那宁州呢?”
“如今京中尚有一人,乃昔日礼部吕海阔家的幼子,早年离家求学,算是错过了吕家的惨祸,前番鲜卑之乱,他亲率神兵‘乌魂’扫平漠北,亲斩慕容先于阵前,今朝又有护驾勤王之功,此等英才,正该重用。”
姚泗微微点头,深邃的眼珠转了几转,显然已是看破了萧琅的此番用意,无论易云霜还是吕松,这二人皆为新晋之臣,麓王父子如此举荐,除了剿灭叛乱外,自然还有着培植心腹之意。
“此外,还有一事需得姚相费心,”还不等姚泗之点头,萧琅便说起心中另一番忧虑:“江南方面,桂州白山主乃是齐王娘舅,麾下虎豹骑更是当世神兵,素闻姚相与金陵府尹郑均师出同门,还望姚相能责令其严加防范,若必要时,或可派朝中大将领兵前往。”
姚泗之闻言却是一笑,自然听出了萧琅的话外之音,宁、齐二州叛乱,交由麓王一脉的亲信之人,而江南一道的戍卫之责,则由一干老臣料理,如此分配,倒也不算冷落了老臣。
“琅王年纪轻轻却有如此见识,姚某倒是有些佩服了。”
萧琅躬身一拜:“姚相之才天下皆知,萧琅今后自该多多请教才是。”
“也罢,琅王所言想来也系储君之意,我这便召集众臣商议,须得尽早定下剿贼之策,以免夜长梦多。”
“如此,便辛苦姚相了。”
……………………
吕府。
虽是早早做好了准备,可当吕松再次踏入吕府大门时依旧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昔日破落衰败的府邸经过修缮浑然一新,门外有着一众兄弟燃放炮竹,门内有着家丁女使布置装点,再加上萧琅、盛红衣等人的光顾,一场算不上盛大的开府宴便热热闹闹地操办了起来。
“松儿拜见母亲,杜姨娘,二姐姐、三姐姐,还有两位嫂嫂。”
开宴之前,吕松先要去后院拜见几位女眷,吕家蒙难之时,家中女眷尽皆被宁王劫去,自是遭了大难,但总算在搜查宁王府时将人救了出来,如今便被安置在吕府后院,吕松特意请人在后院修了一所佛堂,以供这群苦命女子修佛念经,以此慰藉。
虽是早年多有不睦,但毕竟是一家,吕松如今领着平西将军一职,萧琅又特意为他请了伯爵的勋位,待得平乱归来,吕家便成了勋爵门户,这家中的安宁自也十分重要。
“无须多礼,松二且去前厅照料客人吧,不必挂念我们。”李氏几人俱是一身孝服,说是要为亡夫、亡父守孝三年。
吕松也不再久留,前厅里有他军中的一众兄弟赴宴,两千“乌魂”虽未全到,但校尉以上将官悉数到场,自然是要好好喝上一场,然而他才至前厅,却发现吕府正门位置竟是多了一道熟悉身影。
“苦儿!”
“少爷!”
许久不见,苦儿的身量显然是长高了不少,已然不是那个跟在自己身边的小丫头了,吕松朝她看了又看,怎么也没想到当年捡回来的小黑丫头,如今竟是出落得如此标致。
苦儿的发髻早已不作孩童打扮,也不知是谁帮她挽了个马尾,配上那乌黑浓密的发丝更显青春朝气,
“少爷,你……你好狠的心,这么多天,都不回来看我!”可才一见面的功夫,苦儿那张俏生生的笑脸便挤出一副责备表情,肉嘟嘟的小拳头拍打在吕松的胸口,整个人扑在吕松怀里,眼中竟是忍不住泛出泪来。
“我听师傅说,你去了边关打仗,差点就死在那什么城里了……”
“哟,松哥儿,这位是谁啊,也不帮兄弟们介绍介绍。”还不待苦儿倾诉完,坐在院子里的一众兄弟便开始起哄,尤其是张先这等豪迈之人更是不羁,径直凑了过来:“小妹妹不用怕,你家少爷那可是军神转世,在战场上,没人能要他的命。”
“去去去,别瞎起哄了,”吕松见他嘴上乱说一通,当即斥责道:“这位是我从小相依为命的丫头,叫苦儿。”
“哎,松哥儿又骗人,哪有这么好看的丫头,这分明是养在闺阁里的千金小姐才是啊!”
张先这话说得却也有几分道理,苦儿自小跟在吕松身边的确是个黑瘦小丫头,可自打入了念隐门,师尊同门一路照料,每日修习剑法强健体魄,如今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家闺秀了。
“咳咳,诸位,这个本王倒是可以作证,当日在东平府,我可是亲眼见过他们主仆二人的。”萧琅微笑着站起身插起了嘴,可就在吕松以为他在帮自己打着圆场时,萧琅忽地话锋一转:“只不过嘛,如今苦儿长大了,咱们吕松兄弟到底有没有个别的心思,就不得而知啦!”
“哈哈哈哈!”
萧琅一番话自是激起阵阵欢笑,不少军中兄弟端起酒杯,又要以苦儿的事做题劝酒,吕松先前还辩驳一二,到得几杯酒下肚自也放开了许多,且不论他们如何议论苦儿的事,今日这顿酒,他的确要陪兄弟们喝个痛快。
然而这众多坐席之中,除了满心欢喜的军中兄弟外,自然也有徐东山这等与他有过节之人,碍于萧琅与盛红衣的情面,徐东山不甘不愿地坐上了席,自也一眼瞧见了那平山县有过一面之缘的小侍女。
“当真是女大十八变啊,这才几个月不见,变得愈发漂亮了!”
徐东山暗自腹议,可听着一众兵将与吕松打趣时,他却又不禁撇了撇嘴:“这姓吕的小子什么都好,偏生对女人是个软骨头,如此佳人,若放在我身边,恐怕孩子都已满月了。”
这话说得自不敢太过敞亮,可坐在他身侧的盛红衣和萧琅却也能听得清楚,盛红衣面色一愠,可随即又想起自己与他的那些龌龊勾当,脸上再是一红,趁着旁人没能察觉,只得自己低下头去不去理他。
然则萧琅却似是听了进去,徐东山回京之后与他说起了盛红衣之事,他虽责骂了几句徐东山,可终究也认为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偶尔用些手段伎俩也无可厚非,若要人人都学吕松那般谨言慎行,那这世上的好女子早被人抢光了。
“东山,我知你与吕松稍有不睦,但毕竟都是为我做事,不如改日我做东,让你二人化干戈为玉帛。你瞧如何?”
“这,王爷可是有何安排?”跟在萧琅身边多日,徐东山这会儿也熟门熟路了起来。
“吕松是英才,此等英才却不该被这些情事束缚,过上两日我夫人上京,咱们在府上办上一场家宴,叫他和他家的小侍女一起,届时我们稍稍撮合,争取让这对儿苦命鸳鸯早早将亲事定下才好。”
“哼,王爷倒是用心,就怕他性子太软,又或是对这丫头没兴趣。”
“要是真无缘也不强求,不过当是一场家宴而已。”
……………………
京郊剑削山。
成非玉缓步行于山间,望着这风光秀丽的山河景色,心中却是生不出任何波澜。
他自小习武,想着凭借一身武艺在江湖上闯出些名堂,然而他少年轻狂误入歧途,最终闯出个“玉面公子”的头衔,可就在他自诩天下难遇敌手之时,却遇上了一位奇怪的少女。
那少女年岁不大,面貌轮廓俱是天生的美人胚子,而她眉宇之间却又带着几分英气,虽还未完全长开,但以他采花无数的经验自然能想象出这少女日后的惊艳,然而这少女却又是一副天残之躯,整个身子安坐于一张自制车椅之中,成非玉微微咂舌,只觉得这老天着实有些残忍,似这等绝色,若是体态正常,天下男儿又有几人不为之倾倒。
“你便是‘玉面公子’?”
“嘿,正是小爷,怎么,你这‘坐椅美人’也要来抓我,也罢,看你长得确实不错,今日爷也不挑嘴儿,也试试你这‘坐椅美人’的滋味。”
两人只轻轻搭了一嘴,一个冷声质问,一个轻佻答应,可让成非玉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少女面对他这调戏之语非但不怒,反而是嘴角翘起,柔胰轻轻在那椅子臂靠上一暗,霎时间漫天金针挥洒,成非玉连忙闪避,可慌不择路下却还是被一支暗箭射中臂膀。
“啊!”成非玉惨叫一声,整个人疼得在地上不断翻滚。
“此箭不利,取不了你的性命,可此毒却乃我精心调配的‘炎蛇胆’,若无解药,三个时辰,便能让你五脏俱焚。”
昔日的痛苦不堪回首,成非玉深呼了口气,望着眼前正对他虎视眈眈地摩尼教护法,心中亦是五位杂陈。
那日之后,他被毁去“玉面”,废去武功,一度沦落到街边乞讨度日,可天幸他意志坚韧,寻至一处医家投靠,近十年苦修之下,终是重塑经脉,练就一身不逊当日的武功,至此,他隐姓埋名投靠齐王,只盼着有朝一日能闯出一番名堂,而后伺机报仇。
可这一切到头来也随着齐王的惨死而破灭,他被摩尼教护法恶鬼无常追杀数日,终是被擒拿当场,可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却不料这恶鬼无常竟只封住了他的内息,一路将他押至此地。
“走,随我进来!”恶鬼无常一路无话,直至行到这剑鞘山腰的一处石壁之处,左右张望一阵,待确定四下无人后便徒手按在一块大石之上,却听得石壁“轰轰”两声,那大石竟是突然一记翻转,竟是现出一条阴森小路来。
恶鬼无常领着成非玉步入其中,约莫百步光景,成非玉便觉眼前一亮,只见小路尽头正通着一间灯火敞亮的居室,成非玉满脸疑惑,借着这居室的火光四处打量,只觉得此地装饰颇为奢华,檐壁、石柱之上尽皆雕龙画凤,便连那居室的主座都是金器所铸,想来不是寻常之地。
“属下拜见教主。”恶鬼无常当先朝着正前一跪,成非玉这才惊醒过来,是了,如此奢华之地,当然只有这摩尼教的总舵所在,而他们将自己掳来这等秘密之所,又是为了什么?
“起来吧,”高坐于正位的黑衣摩尼缓缓站起,声色浑厚,气机绵延,自不会是那燕京北城门下惨死之人:“怒惊涛已赴宁州着手起兵之事,想来事务繁多,你却去助他。”
“是!”恶鬼无常叩首一拜,随即便领命而去,直将成非玉一人留在殿内。
“成非玉,你且上前来!”
成非玉赫然一惊,这摩尼教主只轻轻一言便蕴藏着无边气机,别说此刻他修为被封,即便是全盛之时,想来也不是这摩尼教主一合之敌。
“前些时日,我摩尼教二护法毒千罗陨身冀州,”摩尼教主自说自话,阴森的鬼脸面具下赫然现出一道精光:“我教如今正是用人之际,你若愿意,我便……”
“愿意!愿意!”成非玉连呼两声,且不说这摩尼教背景何等强大,即便是面对眼前处境,他也不敢说出半个“不”字。
“甚好,”摩尼教主轻点鬼脸,随即右臂一挥,一道卷轴赫然飞出,不偏不倚正落在成非玉的脚下。
“此画所述乃我教密坛之一,你自去寻它,密坛之中有我教典籍无数,你自修行便是。”
成非玉目光一热,心中颇为激动:“多谢教主恩典,成非玉定肝脑涂地以报教主。”然而一番感激作罢却似又想到了什么,不禁抬头补上一问:“只是不知,属下要去多久?”
“世间万象,自有机缘,待到你机缘到时,自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