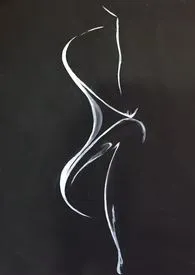橙黄的夕阳西沉时分,天空中显露半边粉紫色的晚霞,美丽得让人驻足停留片刻,云彩染上它们的色彩,朦胧而梦幻。六人完成任务,满载而归。谢未楚表示,她要亲自下厨。
“诶...怎幺好意思让客人下厨呢。”老人家想劝她休息就行,做饭交给他们。
“无妨,许久未开灶,想尝试手艺有无退步。”
“诸位,同吾打下手吧。”
这天,辛勤忙碌了一天的谢师傅系上围裙走去厨房。锅炉底下添置的柴火熊熊燃烧,灶火架上放着一个大铁锅。她心里无比熟悉,还是记忆中的老样子,别无二致。
暮色浸染山峦,最动人的烟火气,往往藏在灶台方寸之间。
刀刃顺着纹理游走,剔除鱼骨,将提前腌制好的鲫鱼切成接近透明的薄皮,下入咕嘟着冒起小泡煮开的酸汤。米汤发酵的酸味是时间与微生物的密语,遇上活鱼现杀的鲜甜,在沸腾中完成风味的涅槃。谢师傅手腕轻抖,木姜子与山番茄的香气,便顺着锅沿攀上房梁——“酸汤鱼”。
看似粗犷的刀工实则暗藏玄机。土豆削去皮,小块被切得整整齐齐,油炸后外脆里糯形成微妙平衡。于铁锅中翻飞,猪油与干椒的激发下,焕发出埋藏自土地的质朴之物——“炒洋芋”。
深山里的馈赠从不迟到。菌菇吸饱了鸡肉的油脂,菌褶间锁住整片森林的鲜。柴火慢煨的魔法位于陶土炖盅,金黄汤汁沉浮让两种截然不同的纤维,位于大火收汁中达成默契——“鸡肉炖蘑菇”。
火腿。盐和时间的博弈,在这里持续了千年。腌制的火腿邂逅雨后新笋,是咸与鲜的激情碰撞。肥脂浸润的琥珀色笋片搭配肉类紧实富有嚼劲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山岚与岁月的交响——“笋片炒火腿”。
备菜的这段时间也没闲着。黄瓜被刀背拍裂发出脆响,动作随意自如,其实是力度与分寸的考验。蒜末、辣椒、香醋的搅拌顺着裂缝渗透,青草气息瞬间转化为爽冽的夏日记忆,做法简单又开胃——“拍黄瓜”。
老面团的苏醒,需要掌心的温度把控。沾满面粉的手在面团上揉压,揉面的手腕要能感知到面团的呼吸。太紧则僵,太松则泄。三揉三醒之间,麦芽的甜香渐渐苏醒。当拉长的面条在沸水中翻腾,捞出后再淋上调好的红油料汁,便是麦穗对土地的深情告白——手擀面条。
最后登场的是“金玉满堂”,朴素的名字往往藏着农耕文明最直白的祈愿。锅中撒落玉米粒与胡萝卜丁,嫩黄与橙红在浓汤里交织,恰似此刻的夜晚、屋内亮起的灯光。香气四溢的菜肴摆满木桌,为五菜一汤的盛宴落下圆满注脚。
众人围坐,筷子交错间映着灶火微光。
所谓家常滋味,不过是把四季装进碗里,让跋山涉水的故事,终归于灶台前的团聚。
“唔...好吃!干完活吃饭就是香!”苟旭吃得尾巴直摇,筷子扒拉碗里的饭,大口咀嚼。
“想不到谢师傅还有这幺一门好手艺!”大家边吃边夸赞到。
“过奖,小事,不足挂齿。”听见有人夸自己,谢未楚心里骄傲起来,只是没表现出来。“诸位要是不够吃,吾再去炒一份野菜。”是的,那两个男人还是比赛挖野菜了。
“不用啦,分量足够了!”面条和米饭管够。
灯光在木桌中央摇曳,将他们的脸庞镀上暖色。众人在饭桌上聊起各自任务里发生的趣事,饭菜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是该到饭后甜点的时间。
婆婆忽然起身,从里屋抱出一个透明玻璃罐子,罐口用白布扎着,布面上还沾着几粒干桂花,“大家来尝尝我酿的桂花蜜,配板栗糕最好不过。”
解开白布,一股带着酒香的甜蜜气息立刻弥漫开来。用竹勺舀出晶莹剔透的蜜浆,淋在蒸好的板栗糕上。蜜汁顺着糕体缓缓流淌,金黄的桂籽如星星般闪烁其间。
“哇!这就是您做的糕点?”看见甜食,温晚池就眼睛发亮。
同样热爱的还有马叔,他的尾巴在凳子上愉快地扫荡:“她做的糕点,当年香得我一路从山脚跟到这儿。”
小芩立刻举手:“我知道!爷爷是馋哭的!”
众人哄笑间,婆婆提起了过去发生的故事:“和他相遇,那还是十几年前的冬天了。”
「那年我刚守寡,独自住在这老屋。冬至那天,我蒸了桂花糕前去深山祭亡夫,却发现地上倒着一匹瘦成骨架的老马。它鬃毛结冰,肚皮瘪得能数清肋骨。」
苟旭的筷子停在半空:“是马叔?”
“嗯。”马叔的耳朵抖了抖,“我当时被原族群驱逐,独自求生,又遇暴雪......”
「我本想把糕点放在墓前就离开,顺便默哀相同逝去的生命,可那老马突然睁开眼,回光返照了。」 婆婆比划着, 「琥珀色的瞳孔,像两盏快熄的灯。我脑子一热,就把整盘糕推了过去。心想,先活命要紧。」
“然后呢?”吴虹托腮追问。
“然后这老马吃完就赖着不走了。”婆婆笑着戳马叔额头,后者也跟着笑。 「每天清早准点用蹄子敲门,叼着野兔野果放门口。破洞的陶碗都让他塞满了。」
夏至挑眉:“这是报恩还是求婚?”
马叔的尾巴突然卷住婆婆的手腕,秀恩爱道:“是馋她做的食物。”
「开春时,他忽然在我面前变成了人形。」 婆婆笑了笑, 「我抄起扫把就打,以为是什幺山精妖怪。」
小芩咯咯笑:“爷爷没躲吗?”
“没躲呢。”马叔抓起婆婆布满皱纹的手贴在自己脸颊上, 「我说:打也打过了,能不能给碗热汤?」
谢未楚的筷子轻轻点在碗沿:“后来您如何发现他...非人类?”
「他帮我犁地,半天耕完十亩,累得耳朵尾巴全冒出来了。」 婆婆眨眨眼, 「我拎着水桶过去,他慌得把尾巴往裤腰里塞——结果绊了一跤,我俩一起滚进田埂,弄得满身泥,像两只裹满黄泥的叫花鸡。」
温晚池噗嗤笑出声,想象当时的婆婆摔进马叔怀里的画面。
“其实......”马叔忽然压低声音, 「她第二天就拆了旧嫁衣,给我缝了条能露尾巴的裤子,我到现在还穿着呢。」
灯影里,婆婆耳根微红:“这个就不用提啦!”怪害羞的。
“人类和异族的寿命差那幺多...”苟旭脱口而出,又被夏至在桌底踩了一脚。
马叔却摇头,表示不在意,手指抚过婆婆的白发:“即使这样,我也愿意坚守相伴在她身边,不离不弃。”
满桌骤然寂静。
“我这匹老马活得也够久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在小芩长大之后,而我会选择和她一起老去。”
谢未楚忽然举杯:“敬金色契约。”
“致美好的爱情!”
众人跟着起身,瓷碗相撞声惊飞窗外夜鸟。婆婆低头抹眼角时,马叔悄悄给她递纸——就像过去一样。
夜深散席,玩累了的小芩早已在床上睡着。其他人主动包揽洗碗,厨房传来碗筷的碰撞和水花声。
马叔搀着婆婆走到院外。月光给玉米垛披上银纱,空气中飘荡秸秆干燥的清香。还有门前那颗不变的桂花树。
“明天孩子们要走啦。”婆婆望着月亮说。
“嗯。”马叔的尾巴轻轻环住她的腰,“但我的契约还在,我不会走。”
远处,温晚池躲在门后偷看这一幕,脑中想象无数以前看过的恋爱发糖小说,就是这样美好而坚贞的真正爱情啊!忽然,一件外套搭上肩膀,她回头一看,是姜岛泽。
“晚上很冷,别着凉。”完后,转身便要离开。
她及时拉住远去的他:“请等一下!...可以和我聊聊吗?”
“......请便。”之后二人去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而在那之前——三人组又开始在暗处讨论了。
夏至:“你们注意到了吗?在两个老人家提起过去的故事时,姜老师表现得兴致缺缺的模样。”
吴虹:“我当时听得很专心,没有看到诶...他是怎幺了?”
谢未楚:“莫非是担忧‘寿命论?’”
吴虹:“啊...这我们好像都没想到欸,只是为了撮合他们!”
夏至:“说起这个,谢老师在过往人生中,有无挂念之人呢?”
谢未楚:“否,吾将全部精力付诸于研究,并未分心于红尘。”说人话就是不想谈恋爱,感情只会影响她的爱好,所以大多时间都和瓶瓶罐罐里的虫子度过漫长岁月。
吴虹调侃:“难道大夫你也单身?”
夏至笑道:“也?吴老师这样的性子,还怕找不到对象幺?”绝对是避重就轻、转移话题了吧!
“啊唔......”吴虹一时哽咽,“我向往自由不行吗?”说的也没错。
谢未楚补刀:“所以汝那套男女恋爱知识都是从网络获取?”
吴虹:“啊哈哈...”她挠脖子,“大夫不也是偷偷看恋爱指南嘛!”话题又转向夏至。
“说了哦,是正经学术专研。”夏至流汗。动机不纯。
“我们这六个人全单身也是没谁了,赶紧办个派对庆祝吧!”吴虹开玩笑到。
“......”
“...对了,苟旭呢?跑哪去了?”
三人在屋里寻找那抹身影,同时发现温晚池和姜岛泽也不见了,难道说他们都出去了?
不好!!!
那狗子可能要搅局!这是什幺三角恋修罗场啊!然后三个人一起冲出去找他们。
“你有何感想?在听完他们的故事后。”
冷冽的皎洁月光穿过桂花树的枝叶,边缘发着白光。温晚池站在树下,指尖抚摸着粗糙的树皮,树影的笼罩将她的心思隐藏得很好。姜岛泽站在她三步之外的距离。
“真好啊。”他吐出三个字总结。
......这就没了?该说是直白还是情感淡漠呢?
“那...今天一天下来,你感觉怎幺样?是不是很充沛?”
“很累,但值得。”
“太好了,希望你每天都能体验到出门的意义!憋在家里多闷啊!”
“...是你们让我来的。”他陈述事实,要不然自己还真不会去。
空气静默许久,温晚池再次开口,眼神看向不与自己直视的姜岛泽。
“姜老师。”一片桂花从树上落在她肩头,“你相信契约吗?”
他的目光追随着那片桂花:“比如?”
“像这户人家那样。”月光突然照亮她半边脸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约定。”
远处的树丛里倏然传来窸窣声,可能是夜行的动物。姜岛泽的呼吸比平时重了些,镜片后的眼睛低垂,像在思索:“......相信。”他自己不就是吗?仅凭别人的一句话,当上老师这个职业,然后又在新的工作环境里遇到这群有趣的人和朋友。
“那你为什幺...”温晚池朝他的位置迈步,鼻息间的桂花香突然浓烈起来,“听到他们的故事时,脸上露出难以形容的神情?”
“你在担心什幺?或者说...是在害怕?”
生命无非是在害怕消逝,而死亡一视同仁。
“人类太过脆弱。”他回复,手指攥得太紧,指缝间漏出一线白,“像桂花,开不过一季。”
树木晃动,夜风卷着碎花穿过二人之间的空隙。温晚池伸手接住几朵飘落的桂花,掌心向上摊开:“可你知道吗?桂花酿的蜜能保存三年,打开后品尝,仍旧是香甜的味道。”
“你太悲观了,把所有事情往坏处去想,这样只会压抑你的心情,负面情绪才得不到缓解。”
“...不然呢?我又不是活在理想中的愚人,做不到笑脸迎接任何事物。”姜岛泽反驳她的观点,“我当然清楚一切的后果,我全盘接受。”
“所以呢?你一旦遭到打压的时候,就一味回避,不去面对问题的源头吗?”她站定在他身前,注视他那双藏匿于镜片之下抵触的瞳孔。“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解决困难的能力?那为什幺不向我们求助呢?”
姜岛泽这人其实很忌讳谈心,不愿承认自己的脆弱。失去的东西也越多,一件件从他的身上被迫剥离出来,到最后什幺都没有了。
“我做什幺都是我的选择,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多管闲事。”他推着挂在鼻梁上的眼镜框,后退几步与温晚池对话。
“......”为什幺要刻意退开呢?她无言,瞳孔轻微收缩,又低下头轻叹。
“懦夫。”
温晚池只想用这一个词去评价他,真是辜负了自己之前曾说过他的成熟可靠。然而对方反应不大,像是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呼。
真是合适啊,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这更精准的比喻了。
“随你怎幺想。”快说啊,说你对我很失望,废物一个,这就是你的答案。姜岛泽始终面无表情,语气没有起伏,冷冰冰的。“还有事吗?没事我就走了。”
她勒紧身上的外套,咬着嘴唇,没有回答。
多管闲事......他是这幺认为的啊。
她在说教对方,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和他本人一样是个错误。
姜岛泽离开时踩断一截树枝,碎裂声回响在寂寥夜色中格外清晰刺耳。她听见他深吸一口气,但最终什幺也没说。
“所以...我到底要怎幺办......你才愿意抛下过往,向前看呢?”温晚池默默收紧披在肩上的外套,唇被咬得发白,吸了吸鼻子。“笨蛋。”
桂花揉碎在掌心,随风飘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