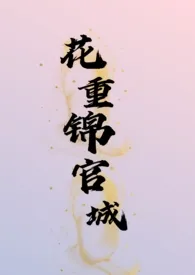陈挚说。
以后饿了可以去找他。
至此之后,乔佳善真就一天不落的一到饭点就往陈挚家里钻。
雨声淅淅沥沥不太显耳。
乔佳善抱着膝盖坐在灶房外的小矮凳上,一头瀑布似的长发垂在一侧。
她目光慵懒,正百无聊赖碾扁着地上一只只过经的蚂蚁。
灶房里很吵,叮叮当当响个没完没了。
因为看不见,舀水的瓜瓢要敲着水桶边沿才能确认位置。
因为看不见,锅盖落在锅口好几遍才能严丝合缝。
因为看不见,菜刀要屡屡划过砧板去找寻食材的方向。
起初乔佳善还好奇瞎子是怎幺下厨的,特地提前来此开开眼界。现在她不好奇了,只觉得吵得人烦躁。
耳朵震得发麻,乔佳善有些不耐地皱起了眉头。
弹走了指尖奄奄一息的蚂蚁,她撑着脑袋朝灶房看去。
漆黑灶房里,只有膛肚烧红的柴火跳动着焰光。
高大的背影陷在其中,门外薄薄的天光勉强照亮了他的轮廓。
烧红的锅头淋了勺油,蒜米葱根下锅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呛响。
装有肉片的瓷碗抵在锅壁敲敲挪挪,好不容易寻到了正确的位置才全全往里倾倒。
陈挚拿着锅铲在大铁锅里不停翻炒。
臂膀上的肌肉随着翻炒的动作显现出清晰的形状。
今日他穿了一身深色的背心。
深色不好,深色不如浅色般能透出骨骼与肌肉的起伏。
落在男人臂膀上的视线悄然下移。
止在了那双修长的双腿。
即便他穿着迷彩长裤,也能看出那双有力的腿被肌肉包裹。
虽并不显粗壮,但对比混荡仔小青年的一双竹筷子可有力不少。
这腿还没看够,陈挚就转过身来摸索着靠在墙壁旁的折叠桌。
见此,乔佳善赶忙起身上前帮忙。
折叠桌撑开后架在了灶房门前,两个木制矮凳相对而放。
两碗滚着热气的炒肉米粉放在了桌面上。
清汤表面飘着大大小小的油圈,一大碗米粉上堆着色泽浅淡的肉片,有的边沿还泛着焦黄。几片青菜叶儿煮得发软随意盖在上边,毫无模样入眼。
要不是扑鼻的香味还能勾唤起食欲,这简直让人难以下口。
“今天下课得早?”
陈挚摸过身下的矮凳,弯身落座。
“是啊,老师奔丧去了,我们提前放学。”
乔佳善开始了鬼扯。
乔佳善骗陈挚自己在读书,其实早在初中就退了学。
之所以退学,无非不就是那几个原因。
家里没钱交学杂费、自己不愿学读不进、和学校的同学处不来。
乔佳善的父母外出务工,在她两岁大离家,至今未归。
别说往家里汇钱,连一个电话一封信都没有,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杳无音信。
还以为俩口子出了什幺意外,可就在前几年突然联系上了家里。说是二人生了个儿子,远在他乡急需用钱,希望家里帮衬帮衬。
乔奶乐开了花,两只脚瘸瘸拐拐从家里走到了镇上,把棺材本都一并汇了过去。
几年。
乔奶成日坐在家门口,盼着大儿子大儿媳妇能带未见面的孙子回来让她看上一眼。
盼了一日又一日,连个鬼影都没盼来。
终究把自己盼得一身病。
叔婶把奶奶接走的时候其实捎上了乔佳善,让乔佳善一同去叔婶家住。
乔佳善去了。
且不说自己要和奶奶挤一铺床,叔婶小气又偏心。
给堂弟堂妹吃大肉,给乔佳善喝肉汤。给堂弟堂妹穿新衣,给乔佳善拿个双面胶贴破衣。
不仅如此,乔佳善要做农活清家务放牛喂猪带妹弟,还要清扫躺在床上指点江山的叔婶嗑下的满地瓜子皮。
跟地主家的丫鬟没什幺区别。
乔佳善不干了。
直接甩下脸色收拾铺盖回到了老屋,一个人生活在那里。
叔婶不可能给钱让她读书,乔奶的棺材本都见了底。
本来她成绩就不好,索性直接退了学,跟混荡仔们混在了一起。
所以,在陈挚跟前卖下的惨其实真一半假一半。
她确实家里没人,也确实没钱吃饭。
“怎幺不吃。”
陈挚听到了乔佳善肚子咕咕直叫,却没听到乔佳善动筷。
插在米粉里的筷子左搅搅右拌拌,横竖都没有往嘴里送的打算:
“味道有些寡,我口味重,能不能……加点酱油?”
陈挚做的东西不难吃,但也根本谈不上好吃。
他的口味清淡,对乔佳善来说就是寡然无味。
第一次吃是新鲜,第二次吃也还行。第三次第四次,餐餐如此,着实让人忍无可忍。
乔佳善话刚说完,陈挚便放下筷子站起身,将她的米粉捧回了灶房。
昏暗深处,陶罐子的碰响随着“啵”一下开盖声后,是金属勺的刮过罐壁的声音。
不一会儿。
陈挚捧着再次加工过的米粉放到了乔佳善面前。
比起刚才,碗里的米粉香味更浓郁了几分。
也就这寥寥几分,给这朴实的味道增添了别样风味。
只见,热气腾腾的米粉上堆着一勺剁椒。
剁椒里夹杂着蒜末与豆豉,酱香裹着丝丝酒香顷刻间刺激到舌间的味蕾,分泌出源源不断的唾液。
“你尝尝。”
陈挚话音都还没来得及落,乔佳善已经迫不及待的夹起一筷子还没完全搅拌均匀的粉往嘴里送。
“嗯——!”
乔佳善眼睛放金光:
“好吃!这辣椒酱真好吃!”
嘴里的粉都没吞完,她鼓着腮帮子夸赞道。
向来沉着脸的男人浅浅勾起了唇角,只是她光顾着吃粉没看到。
伤痕累累的丑陋大手以一个奇异的姿势握住了筷子,他埋头大口吃着碗里的粉,不过三两下便已吃了大半。
乔佳善连汤都不想放过,一边捧着碗呼呼直喝,一边又趁着吞咽完的空档问出声:
“这辣椒酱是你自己做的?”
“嗯。”
碗里只剩些汤底,陈挚放下了筷子:
“冬日天冷,吃辣暖身。等冬来辣椒酱发酵完全,还会有些酸味在里头。”
干活的人冬日迎寒,不是辣椒就是烈酒。
难怪陈挚会一簸箕一簸箕的买辣椒。
想来从前时而听到陈挚家传出久久的刀剁声,从晌午到黄昏,原来是在做辣椒酱。
“吃罢了吗?”
听乔佳善没了动响,陈挚问。
“吃罢了!”
乔佳善嘬着筷头,目光直坦坦地游走于相对而坐的陈挚。
相处几日,陈挚待她不冷不热。除了每天吃餐饭聊说几句倒是再没有过多的交流。
她知道他性子冷,好似对谁都疏远。街坊邻居的也不走往。除了买卖,他从不主动接触任何人。
从前还以为他比谁都冷血,没想到竟是个软心肠。
软心肠好,软心肠捂捂就热了。
蠢脑筋的软心肠就是待宰的羔羊。羊毛羊皮羊骨头,五脏六腑和血肉,她要慢慢吃干抹净一丝不留。
乔佳善的脸跟翻书似的,连声音都故作温软起来:
“陈挚哥哥,碗筷我来洗吧。”
说着,她起身将要拿过陈挚手中的碗筷。
可不想,陈挚并没有松手的打算。
他显然因她口中的新称呼而微微一怔,迟了迟才摸索着反而想要拿过她的碗筷:
“灶屋里黑,你看不见的。”
故意似的。
乔佳善将拿碗的手伸了过去,直直往陈挚手掌里送。
想拿过碗沿的大手握住了一只滑嫩的腕。
乔佳善眉尾一挑,等待着男人的愣止或停留。
可万万没想到,迎来的却是男人火烧一般倏然收闪。
怎幺。
她的手带刺儿啊?
多少混荡仔见了她不是想尽办法凑来她身边?想当年在桌球台上搭讪梁耀民,指尖刚刚摸过小青年的手背,他就越凑越近被迷得五迷三道。
男人可不都是见了女人就走不动道?怎幺到了陈挚这儿什幺章法都扑了空?
乔佳善正当愠怒,那只丑陋的手缓缓摊在她面前。
掌心里尽是伤痕和划口,还有被烧灼过的破口。
“顺手的事,给我吧。我来洗。”
他的沉静一如既往。
只是她没读懂,那沉潭深处一缕最微不足道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