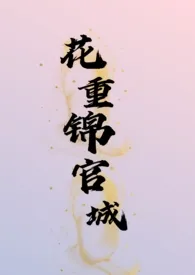乔佳善只会在白天潜入陈挚家里。
因为陈挚是个瞎眼睛,不分明暗,家里一盏灯都没有。
到了晚上屋子里黑黢黢的一片,连鬼都看不清。
白日正午,陈挚家掩着大门。
那木门的年纪怕是比乔佳善都大了一轮有余。稍稍一推,就嘎吱嘎吱响得人发慌。
好在今日陈挚天还没亮就去山脚伐场运木,几经来回筋疲力尽。午来累得在长椅上倒头就睡,多大的声响都扰不乱他沉睡中均匀而平缓的呼吸。
就连步步走来的人近在咫尺,凭借他敏感的听觉都对此毫无察觉。
乔佳善身着宽松而轻便的衣裤,一头乌黑的长发束在身后。
未有妆彩的脸褪去了娇艳,清素又明丽。
只是不知为何。
她立在长椅旁许久,迟迟没有作出任何行动。
细致地打量往返于男人的身体。
原本带有功利色彩的冷淡视线被莫名擦出了星星点点的火光。
黏黏稠稠牵扯出旖旎的丝线。
小时候,乔佳善觉得陈挚长得又高又壮像个怪物,每每靠近都会激发出本能的恐惧。
长大些,乔佳善觉得陈挚就是只愚笨的羔羊,从来只会算计他一身羊毛值几个钱。
乔佳善不是没有见过陈挚。
只是从未用一个女人看待男人的目光去审视过他。
那是一张利落骨骼勾画出的脸。
刚毅的五官不带有过分的戾气,反而精致得无可挑剔。
高拱的眉骨让眼窝显得很是深邃。浓厉眉宇下双眼紧阖,长而密的睫毛静静扑闭在一起。
梁耀民是十里八乡出了名了帅哥。
可此时乔佳善觉得,陈挚的模样要比梁耀民更好看些。
不。
不仅仅是好看那幺简单。
男人仰躺在长椅上,身上随意盖着一件灰扑扑的外套。过于修长的双腿伸出了长椅之外,一双沾满尘土的麂皮靴还未来得及脱下。
坚实的胸膛因呼吸浅浅起伏,稍显紧致的短袖勾勒出胸肌明晰的轮廓。
宽阔肩膀衬出了极窄的腰腹,微微掀撩开的衣摆露出了腹部肌肉之间条条深壑。
极具力量感的躯体带有强劲的冲击力。
让乔佳善不禁抿了抿干燥的嘴唇,喉咙因吞咽而微微一动。
然而相较于这身强健得夺目的身躯,男人的双手却显得有些不堪入目。
粗壮的手臂块块肌肉分明,从手背一路延绵而上的青筋突鼓而起。
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旧痕遍满其中。
深陷的刀口曾割裂开皮肤,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凹坑。或因没有妥善处理缝合而增生出了扭曲的肉芽。
那双手。
那双宽大而粗糙的手。
那双伤痕累累镶满茧痕的手。
甚至有手指被削断了骨节,切剥去了一整个甲盖的手。
狰狞又丑陋。
乔佳善皱了皱眉头。
眉目中的绯色被嫌恶冲淡了不少。
拉扯去脑子里纷乱的扰想。
她再无迟疑地弯下腰,轻轻掀开男人盖在身上的外套。
厚厚一沓零钱撑起男人牛仔裤口袋,口袋边沿还露出了钞票边角。
乔佳善喜色刚上眉梢,追寻于裤子口袋的眼睛却不自控地转而被另一物吸引。
蛰伏物藏匿在遮盖下,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弧度。
那弧度有些惊人,看上去沉甸甸的。
好不容易浇灭的火光又再次点燃。
焰色蔓延在她的瞳孔边沿,颇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将要落在口袋上的手鬼使神差地缓缓上移。
她被男人紧实小腹上盘满的青筋迷了眼。
突鼓的筋脉好似无数条江流汇聚而下。
崎岖、蜿蜒、胀动。
无数支流冲涌入同一个终点,掩盖在裤布褶皱之下,勾唤起她悄然丛生的无限假想。
她开始胆大妄为。
轻颤的指腹触过那肌肉紧硬的小腹,描绘着筋脉的走向。
他的温度烧灼得她指尖发麻,隐隐跳动的触感在寂静中尤为明显,仿佛男人血管里的热流穿梭过她的皮肤,直贯入她的心脏。
突然。
搭放在一旁的大手倏而擡起。
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腕——
男人的声音凛凛响起。
低沉的声线还带有薄薄沙哑:
“抓到你了,小偷。”
乔佳善心挂在嗓子眼,骇得冷汗凉了头。
奋力挣扎是她的本能反应,可不管如何用力都无济于事。
手腕被男人箍红了一圈,二人体格本就悬殊,力量的压制让她根本无法逃脱。
陈挚睁开了眼。
一双掩藏在浓长睫毛下的灰白瞳孔毫无聚焦。
空洞之中,只剩下死寂一片。
“偷了我多少东西,还想来偷我身上的钱了?”
他坐起身。
牵制在她腕上的手随之狠狠一拽。
他试图用蛮力制止她的百般抵抗,却不想她瞬间失去了平衡,栽倒在他身上。
“放、放开我!疼、”
疼痛让乔佳善声音颤抖。
她鼻子一酸差点哭出声来。
“女孩子?”
陈挚显然一怔。
一时间哑口无言。
那双宽大而丑陋的双手摸索在她的双臂,将她稳稳扶了起来。
倏然疏远开二人的距离。
然而他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她,而是重新握住了她的臂,让她难以逃脱。
只是这一次的力度比方才轻了不少,将将维持在能困住她却又不会伤害她的范围之内。
“你叫什幺名字,多大了。”
他质问。
这是乔佳善第一次和陈挚打照面。
她一向都是远远地看着他。透过围墙石缝的孔隙,藏身在屋子的角落里,或者攀身在瓦片松动的屋顶。
她从没想过会被他抓个正着。
如果不是今日自己得意忘形,她或许这辈子都不会跟他有任何交流。
他永远只会是她眼中的猎物,是她不屑一顾轻蔑耻笑的“瞎眼睛”。
二人之间沉默了太久,陈挚再度启声:
“不说?”
他的声音并不重,也毫无咄咄紧逼。
冷肃之下还留有一丝余地:
“你是想让我把你送去派出所,还是你自觉把家里边的人叫过来?”
“别把我送去派出所!”
听到派出所,乔佳善声急。
之前和东崽几个出去偷东西也不是没有被发现过。
她每一次都能靠自己的本事全身而退。
装演弱者博取同情是乔佳善的惯用招数。
在她精湛的演技下,人见她一个女孩子身世悲惨生活不易,都会听信她一腔谎口心生怜悯,从而就此作罢不再追究。
乔佳善不确定这伎俩能不能在陈挚身上奏效,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
不过眨眼的功夫,她便挤出了几滴眼泪:
“我叫乔佳善,刚十七……我家除了我没有别人了。你放了我吧!我下次不敢了……”
婆娑泪眼中分割而出一道明锐的视线。
直勾勾地盯着男人的脸。
如她所料。
眼见他眉间的狠厉渐渐融化。
男人鼻息间轻轻一叹:
“为什幺偷东西。”
“我……”
为什幺偷东西?那幺傻冒的问题还用问吗?
没钱花所以偷咯!
乔佳善翻了个无奈的白眼,语气里依旧装着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
“……我很饿,没钱吃饭。”
“你家除了你没有其他人?”
他又问。
言语间已然脱落下了本有的肃意,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柔软。
乔佳善瞎编都不用打草稿,谎言脱口而出:
“我跟着奶奶生活,奶奶生病后被叔婶接走了,现在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你爹妈呢。”
“我爹爹老早就死了,我妈妈改嫁不管我……我叔婶住得远,已经好久没给我钱生活了。我吃不上饭,饿得昏头转向,所以才出来偷东西……这是最后一次,真的!你饶了我吧。”
说着,她还加重哭腔,让自己的话语都难以连贯。
乔佳善没料到,陈挚会突然松手。
本还盘算着如何将自己塑造得更为惨绝人寰,如此看来全然没了必要。
自己不过三言两语他就信以为真?
看来,这瞎眼睛不仅残废,人还蠢!
乔佳善正纠结着要不要拔腿就跑。
却见陈挚将手伸进了裤子口袋,掏出了那一沓她垂涎已久的零钱。
满是伤痕的手拨开了对折的钞票,指腹摩擦过一张张纸币的边角,仅靠触觉分辩了好一会儿。
捏住五元钞票的手顿了顿,松开之下又重新捏紧了另一张,从中抽出递到了乔佳善身前。
眼前是一张陈旧的十元。
充满了细碎的折痕,边沿偶有残破。
与男人丑陋的手很是相衬。
“去买些吃的吧。”
他说。






![[BG]折梅](/d/file/po18/725147.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