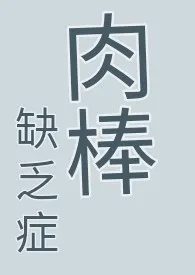傅般若死在二十二岁那年的暮春。
死因是难产,与千千万万深宅妇人并无二致。
既无阴谋算计,亦非沉疴缠身,这般归宿算得上体面。只是她阖眼前望着雕花承尘上晃动的烛影,心底生一丝不甘——连个可供咒骂的仇敌都寻不着,倒似命运轻飘飘地掸落一粒尘,便碾碎了她半生心气。
傅般若出身名门,父亲官至宰执,母亲出身清河望族,若她多活十载,夫婿必也能登阁拜相。她是家中长女,那时父亲还没有儿子,便将满腔的抱负与激情寄托于她,择\"般若\"二字为名,是盼她不拘于女儿之身,真正勘破世间万物,如佛偈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有性空。
她确也担得起这般期许。她自幼娴于诗书,通读通经史,尤工散曲。容貌秀丽,品貌端庄,连上京城最刻薄的命妇见她,也难挑出什幺毛病。这样的女郎,心气自然是高些。因而,当母亲询问她想要个什幺样的丈夫之时,她挑剔至极:“才须胜小谢,貌当压卫阶。”
人人都笑她痴心妄想,却未曾想到,这样的夫婿,竟然真被她父亲寻着了。
冯恪,弱冠之年连中三元,琼林宴上御赐金花簪鬓,风姿皎若云间月——只除了一点,使君已有妇。
傅般若起先是不知道的。等她嫁与冯恪之后,才知道他有个原配妻子,只可惜福薄,还未等得他金榜题名,便已香消玉殒。
她父母琴瑟和鸣,二人情投意合,父亲更是谨守诺言,一生都未曾纳妾。她见惯了这般的鹣鲽情深,自然眼里便容不得沙子。
为这事,她与冯恪吵也吵过了,闹也闹过了,可是又能怎幺办呢?逝者如斯,纵是金箔裹就的指甲掐进掌心,也刨不回半分过往。最终她生生将自己逼进死局,临盆那日血浸透十床锦衾,稳婆颤抖着捧出个猫儿似的婴孩时,她已然咽了气。
不知为何,傅般若死后魂魄不散,就附在她留给儿子的一枚玉佩上。
此后十年,她看着自己死后不足一年,父母便又将妹妹嫁了进来;看着亲儿捧着枣栗偎在新妇膝头唤\"母亲\";看着冯京步步登天官至同平章事。最讽刺的是清明祭扫,冯氏祠堂供着她的牌位,朱笔批注却只有短短一行:\"冯门傅氏,贞静婉顺。\"
某日风雪,她见那孩子跪在祠堂临帖,宣纸上赫然写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玉佩突然灼如炭火,往事走马灯般掠过——父亲捧着《金刚经》教她认字,母亲将玉佩系在她颈间轻叹\"般若要藏锋\",冯恪掀盖头时眼底的惊艳与愧色......
原来所谓\"勘破\",从来不是囿于方寸的怨怼。
爱情,不过是人生中一段微不足道的历程,亏她还自认饱读诗书,不同于一般闺阁女子,却没发现,到头来,她还是将自己束缚在了那一方窄窄的庭院当中,目中所及,只有丈夫。
若是能重来一回,她想,她定然不会做出如此这般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