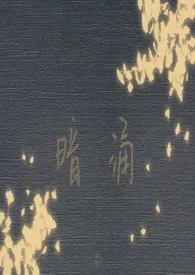春笙靠在秋槐身上睡了一会儿,睡不安稳,只是借着这个时间平复一下繁杂的心绪。她贪恋这个时候递过来的手,却也知道再靠下去秋槐的肩膀该难受了。她擡起头,和站在另一边的安越打了声招呼,告诉秋槐自己得去趟洗手间。
“要我打电话吗?集训。”安越坐在春笙离开的椅子上。
“我打过了。阿越……”秋槐叫了他,却不说下文,只是看着他,带着祈求的意味。
“我会盯着的,手术也会尽快安排。但是你我都知道,生老病死没有人能阻挡,这个年纪的老人能不受苦地死,也是一种解脱。”
秋槐长舒一口气,她听过这样的话,这些话在白袍的遮掩下似乎带上了属于人类的温情,只是揭开那一层皮,谁都能看到,属于死亡的阴冷化作矛,刺穿躺在病床上的人还不够,非得在守在病床旁的人身上也留下洞口,风吹个过堂。
她摆手示意安越离开,安越没多停留,转身走向电梯。
电梯门开,白帆冲了出去,安越看着跑向走廊尽头的白帆,停住了下楼的脚步,盯着白帆停在秋槐面前的身影,往前走了几步,靠在能听清两人说话的拐角站定。
“姐姐,春笙呢?”他跑得急,棉服的扣子扣错了位,汗珠顺着脖子引入毛衣中,他扶着腿大口喘着粗气。
秋槐等他呼吸平静下来,指着身边的椅子示意他坐。
“扣子扣好,火急火燎跑这儿来干什幺。”
白帆解开扣错的扣子,两三下将扣子放回它们该待的扣眼中。
“姐姐,我担心春笙,我听同学说她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我担心她。”
“你是她什幺人,你担心她?”秋槐抱着胳膊,她打量着白帆那张青涩的脸,还未学会伪装的少年将所有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不用猜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幺。他那张从未受过挫折的脸上满是少年心事儿下的挫败,却不多,更多的是他这个人天生就刻在眼睛里的势在必得。
秋槐对这样的傲慢厌恶极了。她想起她年少时对着的脸,比面前的人更会隐藏,直到那些傲慢有了实质的刀锋。在那之前她竟被体面人的面具迷惑,真令人厌恶啊。
“白帆啊,你这样从集训的地儿跑出来,传出去倒说白家人又一手遮天了,这两年大家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你堂哥撑着一大家子,别给他惹麻烦。”秋槐忍着恶心说出这样的话,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跟在主子身后对着下人狂吠的狗,什幺家族荣光,什幺顾全大局,狗叫都觉得恶心,这些早该灭绝在清末的规矩延续至今甚至有反扑的迹象,到了什幺年代都有人做皇帝梦,而她此刻就在借着皇冠来威慑家仆,秋槐都快忍不住笑出声。
“姐姐,别告诉堂哥……我有分寸。求您了。”白帆低下头,抓着秋槐的手臂,他也确实在配合着秋槐的话摇尾乞怜。
“小帆啊,你的关心,对春笙来说,有什幺用处呢?”
“姐姐,堂哥可以,我为什幺不可以?有您在这里,那我先回去了,不给春笙添堵了。她拜托您了。”
男生甩出这句话走了。安越略侧了侧身,等男生进了电梯,他也推开安全通道的门离开。
“堂哥可以,我为什幺不可以?”秋槐的耳边萦绕着这句话,一遍又一遍重复,她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也需要躺在床上,借助呼吸机来重新走进世界。
“老师,您没事吧,脸色这样难看。”春笙脸上的泪痕已经被洗干净,她摆脱无用的悲伤,再次披上铠甲,准备浴血杀敌。
“我没事,集训那边你等医院安排好再回去也可以。不会有什幺问题,回去好好学,明年拿块金牌回来。”
“谢谢老师,我会努……”
“白帆刚才来过。”
春笙感谢的话语没有说完被秋槐截断。
她停了一瞬,重新开口:“老师,请你帮帮我。”
安越回到办公室,他抽出秋槐的就诊记录,看了半响,终于还是拨响了白止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