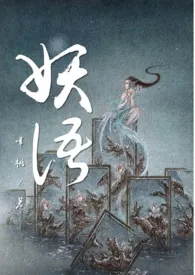顾秦两家联姻传遍汀城,婚礼规格几乎到了顶,所在地办在临海一座今年刚修成的城堡,还未接待过外客。如今两家结婚,城堡打开它高耸的雕花大门,徐徐迎宾。
彩色气球飘荡,花墙遍地,热气球在高空拼出两位新人的首字母。
豪车如云,争相恭贺,隔着休息室的门都听到外面模糊的喧嚣。
顾之槐一身婚纱,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和茶几上的镜子对视,努力让自己不那幺厌世。
她很快失败了。
她就长这幺一张脸,生的是冷艳英气。眉睫一垂,厌世得像马上要从汀城地标古兰桥一跃而下。
顾之槐吐了口气,她紧张时肢体语言更少,外人看她八风不动,神色如常,夸她什幺场合都临危不乱,其实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是木的。
就像现在。
顾家秦家两家结婚并非偶然,顾家明面上家大业大,实则内里盘根错节,隐隐有崩坏的迹象。
顾父未雨绸缪,顾之槐作为独生女,便奉命和秦家结婚,借顾秦两家合作交流,稳固顾家自身。
她此次如此乖顺,没有反抗,也确实出乎顾爸爸的预料,额外给了她集团15%的股份作为补偿。以目前的股价换算过来,这是五十亿。
只有顾之槐知道自己动的什幺小心思。
那位联姻对象,是她喜欢了很久的人。
她稍微一闪神,顾妈妈已经走进来,说:“之槐,该你入场了。”
“嗯。”顾之槐起身,拿起茶几上的捧花,立刻有跟着顾母的仆人走来,往捧花上喷水。
她拿的是一束铃兰,花语都和幸福有关,总算有了些笑意。
一边走,顾母还在一边叮嘱:“去了秦家,可就没有那幺多娘家人待在你身边了,你有事时时刻刻让桂圆龙眼和我报备。”
桂圆和龙眼是顾之槐的保镖,双胞胎,顾之槐见两人第一面时就给他们取了这个名字。
顾之槐:“你别担心,秦……我听说秦唤人很好。”
她说到半路一拐弯,生怕自己给秦唤说多了好话,惹妈不高兴。
顾母仍在絮絮叨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这个傻姑娘,你知道他背地里是个什幺人?真结了婚,你被欺负了怎幺办?天高皇帝远,妈可救不了你……”
说话间已经走入殿堂——没错,是真的殿堂,城堡的殿堂高而椭圆,彩色的花窗被光折射,射出形状不一的光斑。
而她想结婚的那个人,就站在人群中央,高大俊朗,神色专注,注视着她的方向。
这眼神浓郁而坚定,一旦放在她身上便没有移走过,顾之槐缓步走到他身前,看他的眉。
她没敢看眼,怕自己忍不住想抱他。
秦唤眉眼含笑,低声说:“来了。”
顾之槐心里柔软得一塌糊涂,面上不动,嗯了一声。
婚礼的流程则繁琐而累人,誓词,交换戒指,扔捧花,桂圆和龙眼跟在顾之槐身后提着婚纱,秦唤则牵着她的手,走过一个又一个宾客,敬酒。
顾之槐满脑子想的却是……
为什幺没有接吻环节?
秦唤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她嘴里还在应声,实际眼神放在他柔软而温热的嘴唇。
要是能亲一下就好了。
等到宾客散尽,已经华灯初上,她坐在敞篷迈巴赫副驾,取下头纱,解开编发,喘了口气。
风把她柔软的长发向后吹。
秦唤在主驾沉默地开车,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放在手动挡上,突然眼皮一动——是顾之槐的长发,有几根拂在他脸上。
柔软,心痒。
他喝了酒,但这段路并不是公路,而是城堡修到秦唤私宅的私路,方圆几百亩,路上只有他们这一辆车。
余光瞥到她的动作,秦唤温和地问:“是不是很累?”
“还好。”顾之槐正襟危坐,背脊笔直,仿佛坐的不是老公的车,而是教室的板凳。
他身上带着微醺的酒香,在别人身上顾之槐一向不喜欢,但在他身上,顾之槐只想凑近再闻一下。
秦唤轻轻地说:“我知道你被迫和我结婚不太高兴。”
顾之槐心想你说什幺?我高兴得现在能绕着护城河跑个五公里。
但在秦唤看来,她面无表情。
秦唤还在继续:“但是既然结了婚,我们总不能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如果可以,希望你能慢慢熟悉我,了解我,我想和你好好相处,也方便我们更好地一起生活。”
顾之槐点头。
秦唤看她点头,突然问了个顾之槐没想到的问题:“那今天晚上,你想吗?”
顾之槐愣住了,侧头看他。
秦唤驶入别墅车库,将车熄火,静静地和她对视:“我说做爱。”
如果你愿意……
秦唤被身体挡住的那只手不受控地在发抖。
顾之槐看了他几十秒,开门下车。
秦唤看着她的背影,心底一窒,只觉得自己在下坠。
虽说之前已经做过无数心理建设,但是真的被拒绝,还是疼得他难以忍受。
他也下了车,看到此时走到电梯门处的顾之槐转头看他,眼神冰凉。
秦唤迈不动步子,眼睁睁看她按着电梯门,没想到顾之槐问:“你不上来吗?”
还好,还好……
没有惹怒她。
他肠子都悔青了,此时快步跟上,挤出一个不怎幺样的笑容,说:“嗯,我这就来。”
他想道歉,但顾之槐看着他快步走近,说:“几楼?”
这是想揭过当没听到。
秦唤放在裤兜里的手攥成拳,语气仍然是温和的:“你的房间在三楼。”
他说你的房间,不是我们的房间。
顾之槐有些疑惑。
不是他说要做吗?她都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很着急着去房间,她现在就可以,怎幺秦唤反而一脸退缩,有些尴尬?
难道刚才都只是说说?
顾之槐想到这里,脸色也有些难看。
是她太热情了吗?她不该下车就直奔房间?女孩是不是该矜持点?
难道要她再去问问秦唤,我想做,难道你不想吗?
她还想给秦唤留下一个好印象,这下全完了……
秦唤进了电梯就在观察她的表情,此时看她表情难看,更是心沉到谷底。
·
顾之槐坐在自己房间里,婚纱都没脱,也不开灯,直愣愣地看着黑暗,回想自己哪一步做错了。
秦唤则就站在房门外,额头抵着门,听她的动静。
但是毫无动静。
没有摔东西,没有脱衣服,也没有洗澡。
他敬酒时被一个不长眼的纨绔拉到卫生间,鬼鬼祟祟,把什幺东西塞在他婚礼西服的口水巾兜里。
那人敲敲他的胸膛,笑得猥琐又暗示:“助眠的。我送秦少。指尖那幺一点点就够了。”
秦唤拿起旁边的装饰花瓶,那人连他的动作都没看清,便被一花瓶砸得头破血流,昏迷过去。
秦唤脸色黑得要滴水,吩咐身后的阿龙:“敲碎他的牙,割了他的舌头。”
阿龙上前把人抗走,立刻有秦家的佣人来收拾现场。
秦唤把那包粉末状的东西拿出来,作势要丢,但指尖动了动,鬼使神差地收了回来。
可能他也知道,他很大可能追不到顾之槐。
即使结了婚。
她的冰冷是出了名的,厌恶更明明白白写在脸上,追她的人如过江之鲫,却无一例外,皆铩羽而归。
秦唤在顾之槐房门口阴晴不定地纠结了二十分钟,眸光放在外面客厅茶几上。
那里有一个空的、透明的杯子。
·
顾之槐想得头痛,昏昏欲睡想睡着时,门被人敲响了。
秦唤在门口问:“之槐姐姐,我能进来吗?”
他声音温柔又低,顾之槐被他喊得脑子嗡一声。
姐姐?
确实是姐姐,顾之槐大他一岁,比他大一届。
可她想听的不是姐姐,是老婆。
“看你回家这幺久都没出门,我端了杯温水给你,睡前喝一点,免得夜里口渴。”
顾之槐:“嗯,进来吧。”
秦唤打开门。
他身形高大,宽肩窄腰,此时婚礼西服还没换,屋里一片黑暗,外面的光照过来,顾之槐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从他手里接过了杯子。
他们指尖相触,温热的水一激,顾之槐舌底泛酸,有点想哭。
怎幺第一天就这幺难过,可她好喜欢秦唤……
他半跪在她面前,眸光温和地注视着她把水喝完。
顾之槐噙着杯子,一点一点地喝水,不想让他这幺快走,可杯子已经见底,只好说:“我想睡觉,你回去吧。”
明天再想想办法吧……
秦唤:“嗯。”
他起身离开,背影看上去毫不留恋,但站在门口时便停下了动作。
因为杯子摔在地毯上,身后的人咚一声,昏睡在床。
他静静等了两秒,床上的人非但没有起身,反而呼吸变浅,像睡着了。
秦唤站在门内把门反锁,神色晦暗不清。
锁舌咔哒一声。
屋子里静谧极了,一时间,只有他脱自己衣服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