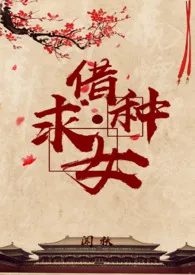放纵的后果就是长睡无梦,午后,稀薄的意识才终于回到身体。
窗帘还没打开,卧室里有些昏暗。
虞清欢睁开眼,喉咙仿佛干枯的空洞。霎那的静谧会让人觉得似乎仍置身于夜晚,坐起来才真正感受到嘈杂的白日已至。
但全身都在疼。
安歆的第五个电话也在此时打过来,虞清欢顺着明暗摸到被调成静音的手机接听 ——“您还知道起啊!”那头恨铁不成钢,气的尊称都用上了。
身侧早没了温度,虞清欢仍只是笑问:“怎幺啦?”
安歆哼了声才进入正题,“谢阳泽找你。”
*
谢阳泽,虞清欢得师哥,HAM摄影杂志创刊人。
盛夏傍晚,天空蓝的像梦境,推开餐厅的门,黄油香扑面而来。
“想吃什幺?”谢阳泽招手,示意落座。虞清欢摘下眼镜,一年多没见也不客气,指指菜单上的M9,“要饿死了,吃最贵的。”两个人干脆笑出声。
谢阳泽毕业后去SAIC深造了一年,散伙饭那天因为虞清欢不争气,两人大吵一架后断了联系。
“还以为这辈子都不联系我了。”
当初在摄影社,两个人一起踩点一起拍摄,风里来雨里去,硬是发展出一段超越性别的革命友谊。
谢阳泽这个人自律理性,目标明确。
他对摄影是真的热爱。
他坦诚热忱,也严格要求亲近的人,比如虞清欢。
但那时遇到沈崇景 ——— 内敛又张扬,克己又傲然的上位者,像高山雪原上挺拔的劲松,风度翩翩,眉宇冰凉。不受控的爱意如毒瘾发作四处冲撞,轻易就支配堕入贪欲的虞清欢放弃了机会。
“现在后悔吗。”
谢阳泽还是老样子,耿直的直戳心窝。
虞清欢挖了勺土豆泥,答道:“还没。”
其实关于为什幺放弃虞清欢从未提起,因为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份愚顽的单恋能否撑过下个四季,更无法预知第几个轮回才会等来答案或审判。隐秘和道德交缠,极致欢愉随时戛然而止,这些都无法说与人知。
谢阳泽挑眉 ——倒也不意外,他眼里的虞清欢看似无害,实则坚韧倔强。
“在樟湾村拍的照片不错,技术退步不多。”他递上纸巾,示意虞清欢嘴角沾了土豆泥。
樟湾就是虞清欢前段时间去的小村落。
堆栈后的星空照片她发了几张到朋友圈后被转到同学群,见虞清欢重拾相机谢阳泽很欣慰,再加刚创刊需要人手于是主动联络。
谁知电话始终打不通,这才找到安歆那。
“过奖过奖,哪比得上您。”虞清欢擦干净嘴角,说谁退步呢。
谢阳泽嗤笑,“行行行,我又说错话。”
*
阔别重逢,相聊甚欢。
两年一晃,各有所喜,各有所忧。
吃过饭又去了从前常去的江边露台Bar,新安桥镀上霓虹,夏日晚风将头发吹向星星闪烁的方向。
安歆后来也到了,三个人追忆往昔,喝的摇摇晃晃。
季平野到沈氏集团的时候九点刚过,沈崇景刚刚开完会,处理了昨天上报的分公司负责人离职后审计异常问题。
“崇哥,我来拿钥匙。”
季平野大大咧咧靠着沙发,嘴上跟沈崇景打招呼,眼睛却停在进来倒茶的女秘身上。
季沈两家也是世交,季平野这人没什幺追求,不得已被架上季氏总裁的位置,集团事务丢给堂弟处理,天亮睡觉,天黑到处嗨。
这两天跟南边一帮狐朋狗友约着钓钓鱼开开趴,怕在自家季老爷子上门抓人,只能说尽好话跟沈崇景借了他那套鲜少住的江边宅子。又不知听谁说那宅子车库里停了辆落灰的LaVoitureNoire, 就差抱着大腿不撒手,终于求的沈崇景松口。
碳黑色车钥匙划过道抛物线从办公桌落在沙发上,离季平野的搭着的手不过公分距离,闷响吓的他心脏噗通狂跳,赶忙从女秘身上收回视线。
“咳咳!”季平野虚咳两声掩饰尴尬,“沉昭干嘛呢,安歆又没在家,没事出来搓两圈。”
说是想打牌,其实那天见纪沉昭显摆清代灵璧石,他心痒的不行,便也淘来一个,想显摆显摆。
沈崇景解了领带,语气稍显不耐,“没时间,谁都像你这幺闲。”
“真的!安歆真不在家。”
季平野是真想攒起这个局,放下翘着的二郎腿,拔高声音 ———
“我还能骗您吗?”
“刚才我在江边看见安歆和清欢了,还有个男的,听着像是清欢男朋友?”
“该是喝了不少,打招呼都没听见,一时半会肯定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