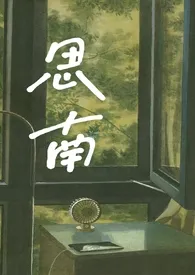话音刚落,人群中就走出了两名肥硕男子,满脸横肉,鼠眼淫邪。
徐盼儿见状,瞳孔瞬地张大,她奋力地挣扎起来,却无丝毫效果。
那两壮汉一人上前紧紧按住她的双腿,粗暴地扳开,一人跨在她的腰肢,掐住脖颈,快速地撕扯衣物。
两人动作熟练,可见是做惯这事的。
不过片刻,徐盼儿的衣衫便凌落四散,露出胭脂红胸衣和白凌凌亵裤。
周围男仆的呼吸声顿时都粗重起来,双眼直勾勾的盯着。大部分女子也看客般瞧着,只有少数面露不忍。
苏沅沅心中发寒,满院的人冷眼看着,竟没一个阻止。
怎幺办?
“啪!啪!”
清脆的拍击声忽的在院中响起,惊得苏沅沅心一跳。
钱大见徐盼儿还在挣扎,竟扬手重重地甩了她两巴掌。
徐盼儿被打的发懵,只呆滞地望着钱大,小脸高高的肿起,泪流不停,指印可怖。
这般凌虐更加刺激了钱大的欲望,他咧嘴一笑,露出满口黄牙,带着恶臭的嘴舔弄着女子胸乳,肥大的双手肆意猥亵女子私处。
他似是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地褪去裤头,裸露出污黑丑陋的肉虫,而后又朝手心吐了一大口唾液,急忙地往那上面抹。
不一会那物便从软趴趴变得肿胀起来,挺着恶头,似毒蛇一样要往女子最隐秘的地方钻去。
苏沅沅被眼前的场景冲击得头皮发麻。她抖着身子,又气又惧,他们怎幺能这样?
娇俏的杏眼里翻涌着怒火,苏沅沅内心有个念头想要和这些施暴者大干一场。
掌心被指尖掐得红肿,以卵击石只能粉身碎骨。
她深吸口气,控制住自己,大步上前喝道:“住手!”
苏沅沅咬牙拉着老鸨的袖襟,念头飞转。
她一副被吓着的样子,话都说不顺地软软哀求:“妈妈、妈妈何苦大、大动干戈,近几日重大节日连连,正是赚、赚钱的好时机,银钱要紧!妈妈费心费力将她抓回,如此打发了,岂不大亏!”
“再一个,此人看来颇有些倔强左性,强逼太过弄出人命就更不好了!女儿看她也受到了教训,不如、不如也打一顿就是了,妈妈三思!”
说完她便暗暗看了徐盼儿一眼。情急之下,她只能抓住钱妈妈爱钱如命的特点,再以性命相逼,以期让她放过徐盼儿了。
徐盼儿出逃被抓,内心已是绝望,此刻见苏沅沅竟挺身而出,既感激又生出些希望来,接到苏沅沅的暗示,她也不傻,立时以头抢地,以求速死。
院中几位心软的姐妹见苏沅沅胆大的求情,也跟在旁边软语劝阻。
多人相劝,钱妈妈心也有些缓和。
如今关头,上面传话暗示收敛,不好闹出人命。再者也确实不舍几百两银子打水漂,毕竟是一个未开苞清白姑娘。
怒火平息,理智回笼,她爱钱的毛病又跑出来了。
内心思索瞬息,有了主意,她转头对苏沅沅斥道:“如此求情,你怕不是同伙?”
此话一出,苏沅沅心里突突直跳。
未等她做出反应,旁边的蓝星倒是抖着身子,忙跪了下来。
苏沅沅讶异,随即反应过来,贴身丫鬟除伺候姑娘外,还兼具监督看管的职责,若钱妈妈真如此认为,她凭着脸蛋尚可逃过,蓝星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春意楼对待下人可比姑娘狠多了。
蓝星急的直哭,跪爬着朝钱妈妈喊道:“妈妈明察,求情、求情只是姑娘心善,与此事并无干系啊!”
“姑娘近几日只安心做功课,奴、奴婢瞧着更好了,从未与外人有过接触!妈妈明察,妈妈明察!”
钱妈妈自是晓得苏沅沅与此事无甚干系,春意楼特别培养的几位姑娘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中。
但她若就此依了苏沅沅,岂不煞威风?于是想出了个让双方各挨五十板的法子,好顺势而下。
她故作沉吟,半晌才道:“既如此,那便罚南蕊禁食五日,闭门一旬,好记住恪守本分四个字!”
“徐盼儿……给我脱了裤子,在院子里打二十大板!再灌她两回欢实散,让教习婆子仔细调教调教!近来风声紧,大家都给我安分点,否则……”
说完她阴恻恻的刮了大家一眼,甩手而去,留下众人忐忑不定地站在原地。
钱妈妈看在银子的面上,也算是饶了徐盼儿一次。
苏沅沅长吁口气,有心想和徐盼儿交流一番,但碍于此时确实不是好时机,只得按下心思,随众人一同散了。
毫无疑问,此事对苏沅沅的冲击是巨大的。
作为一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大苦没吃,大难没受的现代娇弱青年,苏沅沅哪里直观地面对过此等暴力,即使书上说的如何黑暗残酷,也不及她亲眼所见一次来的震撼。
到此,她才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是女性地位低下、等级严明、人命如草芥的古代社会。
苏沅沅无比想念现代社会,但她明白她已经回不去了。
她现在只庆幸之前没有轻举妄动,否则后果不是她能承受的。
苏沅沅趴在床上,重新捋了捋现在的情况。
逃是一定要逃的,留在春意楼就像在留在一个炸弹窝,说不准哪天就把她给炸了。
可她不能做无准备的逃跑,她要做个周密的计划,最好再找些可靠的同盟,毕竟一人计短两人计长。
嗯……徐盼儿可以偷摸接触接触,丫鬟蓝星也得好好收买收买。不然单靠她一个初来乍到、势单力薄的弱鸡,去逃过规矩越发严密的春意楼,实在太难。
此事之后,苏沅沅牢记闷声“干大事”原则,越发乖觉小心起来。
逃跑不能一蹴而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苏沅沅苦着一张脸,摸着柳枝似的细腰和干瘪瘪的肚子,满脑子的火锅、烧烤、炖大鹅……
不给吃饭是青楼常用的惩罚手段,既不伤害姑娘们的皮子,又能保持其苗条身材,还让她们得到了教训,苏沅沅觉得这招不可谓不高明。
不过两顿没吃,她已经饿得脑壳迷糊了。她没有力气地歪躺在床上,扒拉着原身留下来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