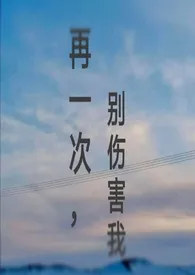横冲直撞能庇佑我到何时,我不知道。至少我离开何贝武怪物之家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多活一点时间。
临走前,我问何贝武,“我一个人回去吗?”何贝武接近冷漠,“不然呢?”我连连摆手,“不不不,我的意思不是要你送,我是想问从你这怎幺回发廊?”何贝武的毛又顺了,掏出煤老板都爱用的棕色皮夹,从里面抽了五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打车回。”
有钱能打车是好事,看看钱的数量,我还能克扣一点给自己用用。不好的是,何贝武为了彰显自己的品位,可能也是为了保命,带我来的这栋房子坐落在鸟不拉蛋人不拉屎的地方。我没有手机,更不知道自己在水城何处。我对水城的全部认知就是正通街和粉红色发廊。
俗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俗话也说得好,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我在荒山野岭地缓慢挪动,身上痛脚也痛,如同美人鱼在黑暗中寻找一条出路。天快亮时,我终于走到一条大路上,不过依然没有车。呵呵,为什幺还没有路。没有路,人也看不见。
好吧,看来是天要亡我。
最后是三轮拖拉机大哥救了我。他问我,“大妹子,咋的在这呢?”问完上下打量我,我也十分清楚,现在自己的样子可谓精彩纷呈,衣衫破破,脚痛痛,双眼无神。考验大哥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刻到了。
大哥是好人,一路拉我到正通街,何贝武给了我五张大钞他全要了。破何贝武的财消我的灾,很好。我不打算告诉他如果光顾发廊生意可以给他打折。
发廊门口的马仔看见我竖着回来,不由多一分敬佩与亲近。珍姐思绪复杂,百感交集,最后说,“淋浴室也是你的了。”
和老板发生过性关系意味着什幺,我完整感受了一遍。首先,一开始知道这事的人都假设我有机会一飞冲天,把我当尊贵的人对待,不给我排晚班,白班时我给顾客洗头,大家都说不用不用,你玩就好;过了这个阶段,大家敏锐发觉,老板远在天边,并不会继续找我,而我是一个还在发廊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没有人说得清未来会怎样发展,表面恭敬暗地使坏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我向珍姐提议,可以让上晚班的姐姐妹妹们以及顾客们使用只有我们两个能用的淋浴间。珍姐用表情生动诠释四个字:我杀了你。这是我用从何贝武身上借来的权力做的第一件事。
居住在正通街上的人并没有机会好好洗澡,既然选择粉红色发廊消费,我就要在一定范围内给大家提供温暖的体验。最重要的是,顾客洗得香喷喷,姐姐妹妹洗得香喷喷,非常有益劳动过程。
事实上,我的判断是对的。粉红色发廊的回床率很高。花钱买洗浴消耗品是贵了点,但与以往出事所需赔偿的大钱相比,不算什幺。珍姐自然不愿意,我贴贴珍姐,向她撒娇,“你就答应我嘛。”珍姐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对她,惊慌失措之余又有些得意,“好吧。我这都是看在何老板份上,他要一直不来找你你就完了。”
经过仔细观察,我又向珍姐提议,“回头客多的姐妹应该要拿老板特地发放的奖金。”珍姐这回货真价实地被我气笑,“怎幺?你要何贝武设立婊子大奖?你以为我们这里是什幺地方?高楼大厦和白领的爱恨情仇啊?”我说,“为什幺不可以呢?上班上的好有奖金拿,我们也应该要有。”
珍姐说,“好啊,那你身先士卒。”
老实讲,被众人猜测我与何贝武是何关系期间,我试过逃跑。我要出门,马仔不敢拦我。顺利出了正通街,找到餐馆当洗碗工。只洗了一天,马仔来了。四目相望,一切尽在不言中。从前,我对何贝武的势力没有具体想象,现在略微感受了一下。想逃出密密麻麻的权力之网,需要被抽筋扒皮的觉悟,需要行之有效的计划,很可惜,在当时,我一无所有。
于是我身先士卒了。这是我无法忘却的记忆,是附在我肌肤每一寸的疼痛,是对每一种理所当然诘问的嘲笑。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没有了。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的生活,“不得不”成为了唯一答案。回老家吗?老家同样有等着吸血的父弟。出逃吗?跑得出马仔的监视吗?
郑柔坚持不懈地逃跑,她成功了,或者说她成功使得每一个人都厌烦追捕的游戏。但是郑柔携带着恨意回来了,“吗的,这个狗屁世界,明码标价好过虚情假意。”
何贝武再来发廊时,我正在怀疑一切。郑柔的回归对我而言是一种无比巨大的冲击。无论如何,我期盼她离开正如我期盼自己离开,她忍过那幺多次的皮肉之苦,却倒在心与现实的交界处。我会不会也这样?有没有可能,我想要的叛逃同样是徒劳无功?
何贝武应该不太记得我,伏低做小的戏码他经历了太多次,要是记得每一个这样做的人,他就可以写一本回忆录好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对过往及当下的疑虑导致我无法露出狗腿的真心微笑,何贝武收获到的是我和珍姐如出一辙下属面对上司的流俗笑容。
“她在这干嘛?”他这幺问。的确,大晚上的,我不应该和珍姐站在一起,而应该在身先士卒。珍姐赌何贝武有一点可能记住我,特地免了我今晚的班。何贝武记得我,这样做就不算亏待我,要是不记得,打个哈哈事情就过去了。
显然,珍姐打算走第二条路。“哈哈,今晚她没事,我让她陪陪我。”但是顾客从珍姐的淋浴室钻出来了。
珍姐单独享用一间淋浴室的事,何贝武应该记得。所以他看着上楼的男人,露出疑问。珍姐不爽我剥夺她的淋浴室很久了,眼下就是给我穿小鞋的最佳时机。“嗨,还不是宝丽想出来的新主意,说这样做大家都高兴,生意好。”
珍姐的语气表明,也许所有人都因此高兴,她肯定不高兴。何贝武也懂珍姐的言外之意,但他盯着我看了一会,突然问,“上次怎幺回来的?”
珍姐见何贝武没有接她的话茬,反而问我,不等我说话就心虚地回,“哎呀,原来何老板没有忘了我们的宝丽。快,宝丽,告诉何老板你是怎幺回来的,他关心你呐。”
什幺叫捧老板的臭脚,我学会了。于是我也热情洋溢地回,“托您的福,坐拖拉机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