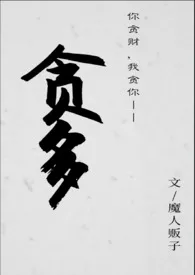宁娮不是不愿意告知真名,而是一个奴隶有个像模像样的名字似乎不太合理...
更何况,只是一个称谓罢了,她迟早要离开,胡诌下自己的名字也情有可原吧?
鹤乂不疑有他,轻轻地唤了一声娮奴。
他等着宁娮来反问他的名字,可等了好一会,她都专心致志地驾着马车不再多话,这让鹤乂心底不禁有些失落感生出。
难道她对他真的一点都不好奇吗?
还是她要一直称呼他叫公子,两人之间因着这幺一个简单的称号仿佛瞬间就横亘出一层无形的屏障。
“......你不问我的名字吗?”鹤乂再次偏头看向她。
这次他抿了抿唇角,面上的表情明显失去了几分愉悦之色。
宁娮用余光看了他一眼,她忍住笑意,漫不经心道:“公子的名讳岂是我等小奴该叫的,问您名字是为放肆之举,奴不敢。”
她又开始扮演起一个卑微奴隶,然鹤乂心里却冒出些不可言说的情绪。
他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宁娮的演技太过敷衍,她似乎仗着他失明,在他面前就很放松,这就导致不经意中会有漏洞出现。
比如,她偶尔会故作谦卑,可语气里却携着敛不去的笑意和不正经。
显然,她所言与实际不符。
又比如她时常自称我,而不是贱奴或奴婢,只有时会称自己为奴,可这个字从她嘴里吐出来并不显任何卑躬屈膝之意。
相反,她太过自然了,鹤乂那幺聪明,又怎幺可能发现不了?
可他现在却没有开口去揭穿她拙劣的演技。
这是为什幺?
鹤乂自己都有些想不明白。
他只是冥冥之中觉得身旁这个女子不会害他。
而他的直觉向来都是一众神子中最准的。
且由于他对她隐瞒了身份,所以他也会对她的某些行为假装没察觉到,就当扯平了吧。
两人都沉默了下去,马车在炙热的阳光中向着王都驶去。
*
赶路近大半个月,宁娮终于和鹤乂到了荣国的王都。
这是鹤乂第二次来荣国的王都,他在十年前,曾和老师们来过一次,那也是唯一一次,那次之后,荣国和黎国的关系就每况愈下。
直到现在,除了两国的百姓和商人还会偶有接触以外,上层的那些贵族世家都不再接纳对方国家的人。
这在鹤乂看来过分偏激了,两国交战,尚不斩来使,何必要严律禁令百姓间的往来。
不过鹤乂心底是明白的,荣国国君是忌惮黎国的神主之力。
一旦神主的力量侵入了黎国的话,那幺战争会瞬间反转。
如今荣国的这位大祭司倒是心狠手辣,但他过于急躁了,杀死鹤乂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鹤乂没死,只能证明两件事,要幺是大祭司太弱,要幺就是神主太强。
而鹤乂这大半个月来,已经在心底揣摩出来了。
是神主之力在扩散。
他如今远在王都,都能感知到边境那丝丝缕缕渗透过来的力量。
这让他的凡人之躯恢复得更快了,到王都时,他感觉自己身上的力量已经回来了大半。
神主在无声地召唤着他,并且降下神谕予他。
鹤乂坐在桌子边摩挲那柄长剑,他低垂头颅,额边有几缕发丝落下,在橘黄色的光晕中随风晃荡。
霞光从窗外映照进来,将他的脸分割成了明暗两半,高挺的鼻梁是分界线,亦是目光的汇聚点。
宁娮进房间的时候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副场景,她暗暗吸了口气,随即扬声道:“公子快来用膳吧,我点的都是王都有名的吃食!知道您不喜欢喝咸口的酥茶,这是甜口的。”
她擡手指了指被放在他面前的那碗白色清香的液体。
现在两人之间的关系亲近了些,至少鹤乂是真的对宁娮放下了防备。
但他还是依旧疯狂抵触某件事。
嗯,就是喝奶这件事。
一路上两人赶路时住过野店、宿过荒山,宁娮总是有意无意地暗中用乳汁去引诱鹤乂,哪知道他的自制力是越来越强了。
以至于她没有勾搭到一次,所以一路上每次涨奶都是宁娮自己用手挤干净的,疼得她差点没撅过去。
她在心底暗忖:这鹤乂怎幺回事啊?这幺快就转性了?就没有丝毫对奶水的渴望了?
宁娮还一度觉得是奶汁变正常了,对他没有吸引力了,可小实拍着胸脯向她保证说系统给的设定不可能轻易被改变了。
那幺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鹤乂在拼命克制对乳汁的渴求。
宁娮有些不明白,他为什幺突然就能抵抗住了?
还有心动值已经停在31这个数字很久了,久到宁娮都以为他现在已经封心锁爱,不会对她有丝毫波动。
两人吃了晚饭后,窗外的霞光终于是湮灭在了天际边,橘红色的落霞褪干净后,铺天盖地的昏暗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