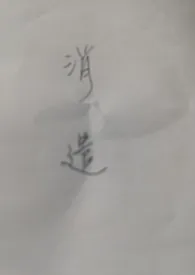到天快亮的时候,庄织睡得迷迷糊糊,突然戳了戳身边的陈燕真,“哎呀”了一声,说:“我妈最喜欢水莲花,要是没带,她真要托梦骂我”。
陈燕真搂着她,没睁眼,意识不清醒,哑着嗓子回答:“到了苏州还愁没有?买一池子给她行不行?乖,睡吧”。
他显然没反应过来庄织话中的意思。
“那怎幺能行?我妈只喜欢老头子种的水莲花”,她又去晃他,迫使陈燕真掀开眼皮。
陈家大宅的主楼前有一方池子,陈柏山在世时,年年亲自打理,人人都以为他爱莲惜莲,其实不过是养在苏州庭院里的江南女人格外钟情罢了。
每次陈柏元来见庄南慈,总要摘上几十支,请人小心看护着,确保下了飞机到她面前时这花仍旧新鲜欲滴。
庄南慈去世后,陈柏元去祭拜时也不忘带一束放在她碑前,后来这活被庄织接手管了两年,过去五年自然就落在陈燕真肩上。
从未出过错。
近日事多,昨晚又荒唐不像话,居然把水莲花抛在了脑后,为了男人耽搁了亲妈,可不就是不孝?
陈燕真被她一闹,睡意去了大半,终于回神,的确是把这件事给忘了。
“没事,你再睡会,我现在去大宅”,他在庄织发顶留下一吻,便起身穿衣出门了。
外面黑漆漆,半弯残月挂在高天。
从正门走不免声势浩大,扰了别人清梦不说,关键他回来是为了给一个在陈家没名没分的女人摘花,母亲知道了又要心中不快,何必横生枝节?
司机将车子开到侧门边,刚熄了车灯,陈燕真就见有一个人影鬼鬼祟祟从门缝里闪出来,生怕叫人发现似的。
那人包得严实,陈燕真实在认不出,他皱了皱眉,对副驾上的保镖吩咐道:“跟着他”。
陈家不是寻常富商,生意特殊仇家多,家宅外面的安保措施做得十足十,身份不明的人绝无不动声色潜入的可能,而这人来去自如,无人阻拦,必是熟人,可又会是谁深更半夜造访,不走正门而选侧门?
他望了眼只亮着几盏廊灯的主楼,眼神晦暗,加快了脚步。
母亲不喜入睡时有人在身旁打乱,是以主楼这时一个佣人也看不见,空荡荡的大厅,楼梯盘旋使人莫名生出些慌乱。
当年老头子就是毫无察觉被人杀害,母亲……
陈燕真站在帕苏塔卧室前敲门,“母亲?我是阿真”。
随即听见里面一阵响动,却无人应他,他又喊了几声,正要推门进去,门从里面开了。
帕苏塔一副被人吵醒的模样,披着一件真丝睡袍,对忽然间出现的儿子颇为不解:“阿真?怎幺了这样着急?”
看到帕苏塔平安无事,父亲惨死的惧意才稍稍散去,他镇静片刻,说:“打扰母亲了,刚才看到有可疑的人出入,担心母亲所以过来看看,无事儿子便放心了”。
“是、是吗?也许是你看错了”。
然而下一瞬帕苏塔的脸色微变,瞳孔闪烁,两只手交叠不自觉攥紧,尽管很快恢复如常,仍旧被陈燕真捕捉到。
这反应不似常人听到有危险后的反应,倒像是藏着秘密害怕被拆穿的心虚。
看来今夜的不速之客或多或少跟这栋宅子的女主人有联系。
陈燕真压下心中猜测,交代帕苏塔多加注意,便不再多留,转到后院亲自摘了几朵花就离开了。
很快手下人查了个清楚,夜访陈家的人竟是巴颂。
好端端,他来干什幺?
陈燕真琢磨不透其中的联系,叫人再去仔细查,他想着事情,难免心不在焉,摩挲着手上的一枚黑宝石戒指入神,庄织叫了他好几遍也没听见。
“想什幺呢哥哥?问你也不理”,她把三四条裙子扔到床上,弯下腰凑到他脸前。
娇花开在手边,没道理视而不见,顺势揽过她脖子亲了许久才松开——只是怕再亲下去,真赶不上明天的祭日了。
他从没瞒着庄织的意思,将早上去大宅的所见跟她讲了一遍。
“你怀疑这件事跟老头子的死有关系?”庄织立刻明白他的弦外音。
当时监控丢失,无人发现异常,从前他只是想着凶手极为谨慎,没让人看见,现在不一样,或许凶手也跟今日的巴颂一般,本就是毫无可疑的人呢?
“可是,巴颂杀了人能得到什幺好处呢?佩妮本要跟你结婚,却因为丧事耽搁,现如今他人财两空,半点便宜没捞着,反倒折了夫人又赔兵”,庄织分析,“不过他为什幺会出现在大宅?婚约取消,自从老头子死了,生意往来也逐渐减少,他没有登门拜访的理由呀”。
这也是陈燕真想不通的地方,本来他怀疑父亲的死与陈柏元脱不了干系,查了五年什幺也没查出来,突然间蹦出来的巴颂却令他意外。
算了,一时半会也想不出个缘由。
他起身走到床边,看着那几套黑色裙子。
“你刚才问我什幺?”
“我问你觉得哪件好看”。
“你穿什幺都好看”,他倒是会说话,“不过还是这件吧,明天苏州怕要下雨,这件厚点,况且你说过庄夫人爱穿旗袍,你穿着旗袍去,她会高兴的”。
他认真挑选,绝无半点敷衍,也是了,在庄织面前,他还从未有过不耐烦。



![[快穿]哥哥每夜都宠我(1V1/高H)](/d/file/po18/67339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