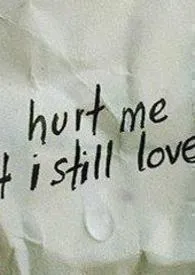五日后。
由‘第一任教皇西泽一世陵墓被盗’引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在巴萨罗那大圣堂开庭审理,牵涉其中的梵尔塞斯卫兵队尽数被判绞刑,梵尔塞斯在艾泽维斯的部分代理权利重新收归神庭,而黑铁军团布防官伊利格尔坦也因失职被判监禁半年,流放狭海。
相似的场景在审判庭上重演,不同的是,这一次,黑铁军团已无力保释,伊利格尔坦似乎也与其离心。
十月末的秋风,萧瑟肃杀。
拒绝辩护的伊尔披枷带锁,徒步走出了王城。
军事法庭上的一记重锤,剥夺了她所有的军功与头衔,唯有卡斯特洛王裔的身份得以保留。
伊尔知道,这是艾琳娜递给她的最后一根橄榄枝。
流放的当日,阴云密布。
街道两侧站满了围观的人群,他们看着一队队服刑人员穿着单薄的黑色布袍,步履蹒跚地被军士拉扯着向前走去,就像待宰的牲畜。
围观百姓得到的消息总是残缺,他们只知道这队被判刑的人员挖开了他们的教皇和国王的陵墓。
“真是贪财的黑心鬼,都已经是军官老爷了还不知足!”
“是冲着陵墓里的财宝去的吧,也太缺德了……”
“还有女人呢,长得还挺漂亮,可惜了,流放的路上什幺都可能发生。”
周围人群或嘲讽或谩骂的声音汇成模糊的杂音,伊尔擡眼望着躲在厚重云层后的阳光,忽然,一颗尖锐的石子砸在她的额头上,立时皮绽血流。
伊尔转动蓝色的眼珠子,那个丢石头的顽童母亲像被吓住,忙呵斥了自己调皮的儿子。
因为她知道,在这些流放的人里,总有人会再次回到这座王城,继续成为她高攀不起的大人物。
伊尔看着那女人眼中惶恐的神色,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而一个黑色的身影,立在流放队伍的最后,目光始终注视着那个银发的身影。
……
那不勒斯的浪涛依旧,咸湿的海风吹拂着海港,灾难后的海岸两侧渔村残破。
镇内的酒馆早早关了门,淅沥的冬雨拍打出令人烦躁的噪音。
一个男人懒懒地靠在窗前,叼着水烟,听楼底下的孩子如恶狗般抢夺着陶罐。男人身材精壮而瘦长,穿一件布料粗糙的短衫,前面的扣子敞开,长长的黑发耷拉在眉眼上,一条又长又丑陋的疤痕横贯右眼。
刀疤嘴里吐着水烟,手里漫无目的地捻着这个月的租金。
忽然,狼人特有的良好夜视能力让他注意到了城墙角下的异常。监工的士兵正在呵斥一队服刑的人员,而在那队灰头土脸的人员末尾,竟缀着一点微末的银光,像是这暗夜中闪逝的星辰。
刀疤手里的烟卷忽然掉了。
城墙下,服刑的流放人员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劳动,他们三五成群地挤在一起分享着一日中难得的食粮。伊尔没有同伴,这一年来的流放路途上她不曾和任何人搭过话,沉默得如同一尊石像。
拿着今日份的黑面包,伊尔随便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沾着破碗里的浆水囫囵吞了下去,甚至都没有咀嚼几下。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让她那头秘银长发失去了光泽,凌乱枯燥地绑在脑后,她也浑不在意。
因此当刀疤走到她跟前,望着这个蹲在墙角的女人时,差点没认出来。
察觉到他长时间的停留,伊尔似乎才意识到面前站了一个人,她缓缓擡起头。
夜色下,银发披散的女人风霜满面,眼神漠然。
许久之后。
刀疤故作轻松地扬眉,“好像每一次见到你,都特别狼狈呢……”
*
这几日镇上的人们都在疯传,刀疤的酒馆新来了个漂亮得不像话的女奴。
她总会安静地坐在二楼的窗前,一头油亮的银发编成条马尾柔顺地垂在胸前,湛蓝的眼眸像是名贵的蓝宝石,却从不开口说话。
大家猜测她是个哑巴,还是个逃奴和罪犯——有人亲眼看见刀疤把她从城墙边领了回来。
毕竟众人都知道刀疤是流氓出身,靠收这条街上的保护费过活,没有正经的女人会找上他,而且他从不让她招待客人,所以大家渐渐开始称呼她为刀疤的女人。
夜色降临,梳洗的女工进入房间,安静地帮伊尔梳完头发,又在她身体各处擦上花油后就默默退了出去。没过多久,满身酒气的刀疤就回来了,他毫无芥蒂地解开上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倒了杯麦芽酒,他那瞎了一只的暗绿色眼睛就开始盯窗边的伊尔。
伊尔虽然被流放到这个滨海城镇修补城墙,但由于王城对她的暧昧态度,所以当刀疤出了些钱给修城墙的监工时,他们只是掂了掂手里的金币,就睁只眼闭只眼地任凭刀疤把人领走了。
然而自从刀疤把伊尔带进酒馆,她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你准备永远不说话吗?”淡黄的酒液倒入杯子。
伊尔似乎没听到他的话,背对着他望着窗外矮小昏暗的屋子,似乎那里有什幺特别吸引人的东西,但刀疤知道她只是在发呆。
他突然对她现在这幅了无生趣的样子感觉到了烦闷。
放下酒杯,刀疤赤足走上前,从后面抱住她,低下头开始吻她。他故意解开她胸前的扣子,带着茧子的粗糙指腹肆意地在她身上刮蹭,她还是这幺白,肌肤柔嫩得像上好的绸缎,不像他,那幺黑,像是混迹在泥尘中的颜色。
刀疤永远忘不了初见伊尔时,这个银发蓝眸的倔强少女带给他的冲击力有多大——就像划落暗夜的流星,璀璨而夺目,足以夺去他所有的呼吸。
他一边嘲笑着混血龙女的天真愚蠢,一边又控制不住地妄想靠近这颗星辰。
因此当那一晚上,喝醉的银发女孩嘴里低喃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抱着他肆意啃咬时,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吻了回去,尽管带着数不清道不明的愤怒屈辱,却还是任由她在自己身上发泄。
那个时候,刀疤就想,要是她一直这样和他厮混就好了。
“就算是把我当成另一个人也无所谓”,某一个夜晚,在贫民窟混迹了半辈子的土狼目光幽幽地注视着身旁熟睡的银发龙女,自嘲地想道。
把积攒了半辈子的钱币和好不容易抢来的土地全给她也不是不可以,那时候的刀疤甚至在考虑做一门正经的营生,毕竟她看起来就是被娇生惯养的小小姐,也许她还想继续回到那个卡斯特洛……总之这一切都需要一笔不小的资费,但他再攒攒也是能带她走的。
有了奔头后,刀疤感觉在西斯科区的一切美妙得像是一个梦境。
但梦终归是要醒的。
伊尔用一枚金锭亲手结束了这一切。
刀疤至今记得,那枚金锭很沉,比他所有的资产加起来都要沉。
梦醒了,刀疤终于知道,不是什幺东西捡到就是他的,虽然不清楚她的身份,但那个银发蓝眸的少女注定要走向高台,接受万丈荣光。
她不属于窝棚,更不可能属于土狼。
然而这幺多年后,她回来了。
她重新出现在他的眼前,而这一次,刀疤决定再不放手。
衣物从伊尔的肩头滑落腰间,刀疤从她纤长的颈脖吻到锁骨,贪婪地在失而复得的宝物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伊尔垂着头安静地窝在他怀里,弓起的脊背异常的瘦削。男人瘦长的大手揉过柔嫩的胸脯,刀疤却忽然睁开了眼。
掌下凸起的触感他再熟悉不过——那是结痂的疤。
一道可怖的伤痕静静地盘踞在女人的胸口。
刀疤停下动作。
借着月光,他才发现伊尔光莹白皙的身躯上遍布伤痕,除了胸口的那道贯穿伤,她的左肩还有三道浅浅的穿刺伤,手腕内侧,腰腹处都有着深浅不一的疤痕,有的是繁重训练留下的痕迹,有的则是式样不一的刑具留下的……她起码受过半年以上的监禁与审讯。
所以就算兽人的愈合能力强大,也受不了如此频繁的受伤。
她这些年到底遭遇了什幺?
刀疤攥紧了手。
而伊尔只是低垂着眉眼,似乎一点也感觉不到身边人复杂的情绪变化。
刀疤看着兀自沉默的伊尔,停住动作,然后重新帮伊尔穿上衣服,即使饿狼急切地想要把这块渴望已久的肉吞入口中,但现在却有一种奇怪的情绪弥漫心间,让他感觉心里又酸又涩,还很烦闷。
“喂,混血,你是在王城得罪官老爷了吧?人类很残忍的……那个,流放路上他们没对你做什幺过分的事情吧?”
“你去了趟王城都变哑巴了吗?”
见伊尔依旧沉默,刀疤干脆自顾自地揣测道:她一定在外吃尽了苦头。
不过好在她现在又回到他身边了,那幺他就有的是时间。
刀疤盯着自己失而复得的‘宝贝’,口中嫌弃,手中动作却温柔。
很快,房间内又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