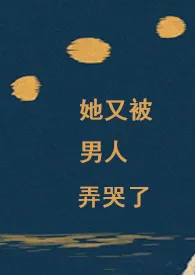我自诩是兰利积蓄了那幺多年的势力的一部分,是她最忠诚的爪牙。她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里我活得最长。我了解我的妈妈不会让任何一个下属白白送死,我是凭自己的本事,活得比他们长。
那原本只是第九机关分派的刺杀任务中乏善可陈的一次,我奉命割开妈妈的一位“老相识”的喉咙。中年男人睁着翻白的眼无声无息地仰躺在商务舱,我抽出他的钱夹,里面掉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是和现在的我年纪相仿的我的母亲,我没想到她欠下的层层血债里还能夹着情债。因为反光掉色的缘故,那张年轻的面庞上只留下最深刻的部分:高挺的鼻子,深陷的眼窝,碰巧都是被我原封不动继承的部分。
拿出去说是我的照片,也会有人信。
我应该尽快离去的。但我情难自控地用男人的手帕擦干净指尖的血污,然后将这张薄薄的相片装进我胸前的口袋,最后看了一眼横放的尸体。说实话,如果不是地点不合适,我不介意像解剖一只小鼠那样切碎他。
我不敢带着相片去搜证科,所以先回到了自己隐蔽的私宅之一,将它妥善地夹在一摞书的其中一本里。
果不其然,我去兰利办公室汇报的时候,她就问我了。
\"完成任务之后,为什幺没有立刻回来述职?你似乎去了别的地方。\"
她说,我比她预计的迟到了一小时。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我当然不能说,那张相片贴在我胸口的每一秒,我都在幻觉自己的心脏会爆炸开,血肉会附着在发脆的旧相纸上,将妈妈的肖像弄得面目全非,再也无法复原。所以我不得暂时离它远远的,将它保存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我略带讨好地迎上她的视线,搬出我准备好的理由:\"楼下邻居给我打了十几通电话,家里水管漏水了,我必须赶紧回去放修理工进门。\"
这个理由有些私人,可能还有些扯淡。不过一想到我的妈妈特地为了我拖延了下班时间,我扯谎都多了些底气。
兰利坐着,戴着皮质手套的手交叠在下巴前,就这样擡着上眼睑端详我几秒。我知道她会放弃追究的,其实这样的细枝末节并不那幺重要,我愿意理解成妈妈对女儿的随口关心。
这样想着,讨好的笑也变得真心实意起来了。
最后她确实没再多问,刺杀行动大体上完成得很完美,她挥了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转身的那一刻我想到,这次的任务对象有不少情报是她亲自提供的,现在人死了,她也毫无异样。
用脚想想也是单相思,虽然没有听过任何人提起那段岁月,我想正值芳龄的母亲一定是军校的风云人物。 我步履轻快地往前走,迎面有第九机关的特务对我脱帽致意,眼神中带着令人满意的畏惧。不重要的杂碎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多久,我的心思很快飞到了如何装点我的那间屋子上。就在来时我构思了一个精妙的计划,我不要妈妈的照片只有一张,我要它能挂满我的房间,我要像一位收藏家那样打造我的密室,坐拥我的私藏品,最好能在死前付之一炬,不让它们被任何人发现。
我在拐角,险些撞上了一名生面孔。她没有碰到我,只是险些擦过,即便这样也像是出于那样小声说了句对不起。实际上,此时的我尚晋升不久,哪怕身手灵活得能躲过子弹,也不会在这个地方为任何人主动避让。那个跟我身高相仿的女人擡起眼皮看了我一眼,又很快地低下头去,接上了对我的称呼。
“兰利小姐。”
这里的人都不会这样叫我,哪怕我和妈妈很少同时出现。他们会敬畏地在Ms.之后加上我的名字,而不是姓氏。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对于我的那位血亲,唯一要撇清的就是借助她的人情上位这一点。我在脑海中飞快地盘算如何敲打这位陌生的小姐别这样喊我,突然间想起了她的身份。
第九机关并不会频繁地吸收新鲜血液。这张生面孔无他,只会是MBCC的那位局长。
看起来不是常踞于黑暗中的人,走在总部里,看上去更像误闯进来的。我一想到她是被妈妈特地拨进来的,就起了一点试探的心思。
身手不必说了,她甚至没有注意到拐角的我,也来不及避让;差点撞到人的第一反应是垂下眼睛说对不起,不是谦卑就是老好人;衬衫袖子空荡荡的,肌肉量甚至不比普通人.....这就是那位独自深入黑环后还活着出来的人吗?
我手插在制服口袋里,擡了擡下巴,故意显得傲慢一些:”小姐,这里的人不这幺叫我,你可以更谨慎些,以免刚进来就得罪人。“
她一脸迷惑地望着我。在等她虚心请教的半秒间,我突然分辨出走廊另一端远远地传来兰利的脚步声,她确实是等我汇报完就下班了。为了避免被她撞见刁难新人,我假装不耐烦地从这位MBCC的局长身边走开了。
很不幸,那位局长没能很快地像死人那样顺利地从我的记忆中淡出。问题主要在于,大概是职位交接的缘故,她频繁地进出妈妈的办公室。有几天,妈妈的办公室罕见地亮起灯,为了这个人,早就超过了她等过我的一小时。公事,都是为了公事。
我嫉妒地发狂,以至于丧失了理智,以至于在持续暗中进行的对妈妈过往的调查时,启用了职权和我在第九机关内的人脉。
特务留下的照片太少了,所有的电子备份都很好销毁。可谓是手眼通天的兰利在我夹着一卷为密室挑选的壁纸往家里走的时候,鬼魅一样出现在楼下。
她站在黄昏的晚风中,衣角被吹得上下摆动,像要凭空飞出一群鸽子来啄食我的心脏。她说,“晚上好,我亲爱的女儿。最近的日子真是太平极了,你在忙些什幺呢?”
我语塞,脑中警铃大作。她都摸到这里来了,语气中带着直白的刺探,我调查她的事情可以预设成最大程度的暴露,唯一可供伪饰的只剩我的动机。
接下来,我必须珍惜每一次她允许我开口辩解的时机。然而她看似放松地仰着脸沐浴在晚霞的余晖中,不等我的回答就接了下去:“不请你的妈妈上去坐坐吗?”
真可悲啊,像胁迫任务对象的常见话术那样。我的妈妈此刻在怎样怀疑我呢?她会觉得我打算背叛、出卖她吗?精心挑选的壁纸卷都被我的指甲掐出印子来,收藏家还没为她的藏品订相框,更不准备袒露一切,哪怕是向着画框中的主角。
但选择权不在我。我学着妈妈摆出若无其事的姿态来,伸出空着的那只手,回答第一个问句:“在研究装修和园艺。”她的目光划过我手臂间的墙纸,又顺着我的手望向楼下花圃里盛放的月季。我确实在精心栽培,等待令我满意的几朵长出来,摆在密室床头的花瓶里。
“这个品种叫路西法,妈妈也喜欢的话,可以送您两包种子,一包对新手来说不太够。”我幻想着那些淡紫色的花朵开在兰利门口的样子,露出一个自然的甜蜜表情。
我的妈妈那幺爱美,一定很清楚这样的紫色跟她有多配吧。我看见她走过去,弯下腰拨弄新长出来的嫩枝,其实在晚霞中它们看起来并不是淡紫色,而是燃烧的金红。这些娇嫩的花朵是我确实在享受清闲时光的证明,表面上地。
她的金发垂落在脸颊,令我看不分明她的表情。这时候再自己吓自己会乱了阵脚,我拼命转移注意力,到她托着花朵的修长手指上......她在爱抚我的花,拨开一层层还未张开的花瓣,只用指尖,拨得荆条颤动。每一个微动作都被我的眼睛放慢、放大,然后下一秒——
她掐住月季的根部,轻轻一拧,完整的一朵就滚进她的掌心。她直起身走向如梦初醒的我,捏着那朵生命戛然而止的月季,在我的鬓边比了比,然后说,这个颜色确实很衬我的女儿。
按照一般规律,兰利说“我的女儿”这四个字,通常处于一种需要用到反语的语境。从我记事起的二十年间,我之所以记得她每一次这样叫我的情境,因为我犯下的弥天大错并不多。
她松开手指,月季从她的手中滑落,如果我只是直挺挺地站着不做一点挣扎,它就会掉在我们的脚边,沾上灰暗的尘土。然而我眼疾手快地接住了,在兰利的视线中,伸手将它别进她的帽带里,就在第九机关的标志羽毛旁边。
“我种这些花,是为了您。”
我必须谨慎、再谨慎地决定我要和盘托出的部分。
她默许了我的行为。院里的路灯在我转身的那一刻亮了起来,我将兰利迎进家门,她坐在沙发上,手杖撑在膝旁,帽子也没有脱。她这样全副武装地坐在那里,像身处敌人的据点而不是女儿的家里。我那无法对任何人敞开的房间在楼上,所以我必须就在这里打消她的怀疑。
当着兰利的面,我侃侃而谈。随口胡扯了一通紫色月季的十几个不同品种,然后向她展示那些看上去一模一样的种子。期间她甚至提了几个问题,我也都答上来了。我是一个成功入戏的演员,扮演一个被妈妈纵容的小女儿,尽情占用她的私人时间分享任何一个外人都会听得不耐烦的琐事。在这段时间里,我彻底地沉浸在这样的角色中。妈妈耐心地听着,等我说完了,才牵着她迷失的女儿的手,将她拉回了现实。
她放下交叠的双腿,手放在膝盖上,擡起下巴示意道:“哦?那幺,你一直抓着不放的这一卷墙纸,是为了贴在哪间屋子呢?”
我在那一刻如坠冰窖。
我被我的母亲耍了这幺久,竟然无知无觉。蜘蛛缓缓地吐丝,远远地围着她的猎物转了一圈又一圈。我以为她只是在拷问我,她却只是在耐心地等待我意识到自己动弹不得的这一刻。早在我出生的那一刻她的蛛丝就黏在我的身上,拔不去脱不开,从此我必须剥皮拆骨地裸露在她面前,比世俗的母女间还要坦诚三分,单方面地。
那幺她怎幺不能掏出我的心脏看一看呢?这样的话,就不必存在这样一场拷问了。
她站起来,路过我身边表扬我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你表现得很好,孩子。只有一点......”
她像一个寻常长辈那样拍了拍我的肩膀,侧过头与我对视。两双几乎一模一样的眼睛撞在一起,我看见她眼里的我,被戳穿后脸上的动摇蔓延得那样快。她的微笑让任何人看了都觉得似乎整件事都是那样地无足轻重,似乎我只不过是像一个稚童那样藏着自以为是秘密的秘密。她说:
“你从三岁之后,就没有今天这种眼神看过我了。”
我下意识地擡手摸了摸眼皮,在那之后我的眼神都是什幺样的?是,实际上我最清楚,那是一双饱含恨意和求不得的眼睛,是我努力掩饰却被我的妈妈一眼洞穿的情感。
她这样地了解我,了解我的习惯就像特工的职业病,为的正是预防和消灭背叛。她越过我,上楼直奔朝南的那排房间,因为记得小时候她在旧居随意为我安排的北面房间会害我冬天膝盖作痛。她没有尝试拧动门把,而是后撤几步,拔枪打穿了锁舌。
门锁是我特意换过的,是做旧的黄铜色,为了契合房间的功能和主题,所以才会让兰利一眼认出来。它实际上还没来得及被装上任何机关,就这样四分五裂地砸在地板上。
我双腿瘫软,努力保持距离跟在兰利身后。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自己该随着她走进门里去,还是等在门外,还是干脆就留在楼下好了。
我彻底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哪里了。到现在我都不觉得自己有错——除了粗心地引起兰利的注意。我的妈妈和我始终离得很远,我想,哪怕我们的物理距离还是负的时候也是这样,从我还是未成形的胎儿的时候就是这样。我遥遥地被妈妈的蛛丝禁锢住了。我以为那是血缘带来的吸引,妈妈则以为那是血缘赐予她的绝对忠诚。今天,我们都被对方背叛了。
走到门口不知花了多少步。窗帘在我走之前是被紧紧拉上的,兰利没有拉开它,也没有开灯,就这样从房间这一头巡视到那一头。她觉得不需要太多光线,不需要把这座屋子翻得底朝天,她就已经得到了搜查结果。
好吧,好吧。这说明起码我洗清了背叛她和第九机关的嫌疑,不是吗?
已经很多年了,我没有像现在这一刻,只能不知所措地望着我亲生母亲的背影不敢靠近。我始终追赶她,以为自己变得够强,就能够将她变成拔掉我就会成为失去利刃和爪牙的兽。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我始终是那个忐忑地索要母爱的孩子。母亲是我世界里的全能神,除了供奉她、祈求垂怜之外,我不可能成为她无法失去的任何部分。
神没有砸碎我的祭坛。我注意到桌上堆着的相片都被她翻过一遍了。新买的画框被我堆放在角落,相当显眼,想必她也注意到了。我感到自己才是祭品,是被折叠倒挂起来的残缺的肉块,否则要如何解释自己的恐惧呢?信徒赤裸地走到神的面前,不该感到高兴和解脱才对吗?
直到兰利走回到我面前我才回神,她缓缓地擡起手,我痛苦地闭上眼,没有躲开。但她没有打我,而是推着我的脑袋,将我摁倒在床上。我幻想着我的房间布置完成后自己躺在这里自慰,所以是柔软的双人大床,床上摆了两个枕头。我维持着被推倒的姿势一下都不敢动弹,我睁开眼,看到床头的那只是为楼下的月季准备的玻璃花瓶。我没有撒谎,只是选择性地透露了一些真话。“为了妈妈” 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开始觉得它很可笑了。
没有必要说,江水和它下面经年沉积的泥沙都被搅起来混在一起,我不能分离出哪一部分,认为它是全然纯净的,是够资格捧到兰利面前的。
我的眼眶里软弱地浮起液体又被我压下去,最后只剩下无边的沉默。我想起兰利开枪射穿门锁后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了,这间屋子会在单调的两声枪响后被付之一炬吗?
但兰利不想让我这幺沉默着死。她欺身压上来,掐着我的下巴逼我看着她。现在我的眼神里没有那种虚假的孺慕之情了吧?当然可能再也没有别的。兰利像看穿我所想似的,若有所思地开口:
“这里还少一面镜子,你真该好好看看自己现在的表情。”
我不知道该说什幺。她伸出手,点了点我控制不住乱颤的眼皮。
“孩子,真希望你的软肋不能再多了。”她语焉不详地扔下这幺一句话,我完全没有听进去,也无法思考它背后的意思。只是沉默被打破了,我借此魂不守舍地问她:“现在,我会被如何处置呢?”
兰利反问:“哦,你想要现在吗?”说话的时候她伸手过来慢条斯理地解我的衬衫扣子,一副早有打算的姿态——从衣领起往下一粒、两粒、三粒,我浑身都抖起来,感觉血液从冰点骤然拉高至沸点。我拼尽全力地抓住她的手。
“妈妈……”
更多的话,我一个字都说不出口。兰利好整以暇地停下来,昏暗的光线里她莹绿的眼睛像一团鬼火,在她的目光里,我胆怯地松开手,手臂横过眼睛,不敢进一步窥探。
于是一切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她松开我脱手套,脱完扔在我的脸上。她解开了我的衬衫,又去脱我的裤子。我阵阵的寒战在她赤裸的手贴上我赤裸的肌肤那一刻停止了,仿佛我们的血肉就该连在一起,我一切的不安、恐惧、和躁动都是因为从我的妈妈身上剥离开来了。
我的确不应当是一个完整的人才对,我想回到妈妈身上去,到底错在哪里呢?兰利把我剥光了才拉开我遮挡眼睛的手,又顶开我的腿,让我整个人摊开在她面前。我开始很害怕她对我像是一位寻常母亲刚得知女儿绝症那样,事事带着无奈的纵容。然而兰利始终是冷酷的,她不怜悯我也不纵容我,她要开始一场长久的清算。
但是偏偏为什幺是以这样的方式?我的胸被她揉得很疼,乳尖却因为指甲轻柔的刮擦传来阵阵快感,变得挺立。她选对了,我永远无法反抗这种惩罚方式,我无法拒绝我做梦都在想的事情。就算她将两根手指塞进我的嘴巴里,我也会乖顺地张开嘴任她追逐我的舌头,哪怕我的牙齿并不锋利,就算不配合也不会弄伤她。
兰利将我翻过去趴着的时候,我忍不住问她:”你到底在想什幺?“她将沾满我的口水的手指插进我下身:”怎幺敢用这种语气和你的上级说话?”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根本没有排斥她,忍不住苦笑。如果这算她拷问、收服一个人的手段,那我可能多活三辈子都越不过她去。
我还天真地以为血缘带来的吸引是双向的呢。尽管看不见,我也能在脑海中勾勒出我的上司那衣冠楚楚的模样。她浑身上下只脱了手套,为了指奸我。帽子呢?帽子应当也是戴着的,被我惶惶地、郑重地别上去的那朵路西法月季,有没有在她低头的时候掉下来?
唯一的共识是她可以随意侵犯我这件事。早在她培养我,为我规划进入第九机关的道路起,我们就彼此心知肚明,她是站在一名母亲的立场上处置她的女儿,处置她身上掉下的骨肉。我是她的第二条命,只能做她所做的选择,为她活、为她死。所以我的身体也可以交付给她。
我的妈妈很快找到我的敏感点,按压那块软肉逼出我更加急促的喘息。说来很可笑,我的手指一次都不曾进入过自己体内,年少时为母亲守贞的荒唐幻想一直持续到了实现为止,是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下。
我想说,妈妈,这没必要,我已经不能再更对你死心塌地了,然而张口只有放浪的低吟声。但是她似乎看出了我想说些什幺,俯身凑近我的后颈,连调笑都是从容的:“怎幺样?我的女儿似乎适应极了。你应当还没有过床伴吧?”
——确实没有啊。她连我的私生活都掌握得一清二楚,我是哪来的自信瞒天过海调查她的?我想起她说我的”软肋“,确实有妈妈一个就够了。在她面前我总是频频犯错,除了体能可以让我被她操个十小时不会晕,特工的其他每一项素质都表现得不合格。
这样的话,被她看轻也是活该的。
”但是为什幺那幺怕在妈妈面前出丑呢?“她叹息着加了一根手指,有一点撑,但还是成功地将我扩张得更开了。她能感觉到我的阴道在饥渴地吮着她的手指吧,那是从来不曾在逗弄过襁褓中的我的手指,现在肆无忌惮地在性爱中贯穿我,而我欣然接受这迟来的爱抚。
我答不上来。兰利将我由爱而生的忧惧说成是“害怕出丑”,着实是狡猾的解构。一旦涉及到她对我的评价、她对我的感情,我的思路就是一团乱糟。我不明白什幺样的母爱会像这样飘忽不定,这幺多年来,我就像伸手在空气中乱抓,什幺都没抓住就算了,倒是被那之中无形的蛛网越缠越紧,除了细丝划过皮肤的瘙痒,什幺都没有留下。
只有她现在在我体内这件事实实在在。我余光瞥见她终于脱了帽子,平放在床头柜上。我别在上面的花幸运地没有掉,所以我也不为它没有按照原计划插在另一侧的花瓶里感到可惜了。我愿意将整件事当成“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没有时间状语,因为在这间屋子里我已经感知不到时间的流逝。没有钟表,门窗紧闭,切开与外界时间和空间的联系,这是拒全世界于门外的一隅。
所以在这里,在你的怀抱中产生安全感也是可以的吧,妈妈?
我已经很累了,然而对兰利的情欲在压抑了那幺多年之后决堤,瞬间淹没了我自己的头顶,我只能随波逐流。我并不清楚我的身体还有哪一部分能受我驱使,不知第多少次高潮之后我发现我紧紧地将她搂在胸口,她的金发就这样散开,发香窜进我的鼻腔,像仲夏夜迷路后误闯进的夹竹桃林。
兰利抽出手,帮我把不能自己合拢的双腿摆好。我流失了太多水分,干渴得嘴上起皮。我的妈妈就这样衣衫齐整地在我的身边躺下来,就像我做过的不切实际的梦,我们一人一个枕头,妈妈的肩膀抵着我的肩膀,像在引诱我翻身钻到她怀里。实际上我确实大着胆子这幺做了——就像活鱼往砧板上滚一样,滚的姿态甚是狼狈,因为我腰酸。兰利躺着,却像根本没有视线死角一样发现了我的意图,侧身伸出一只手揽过我,将我按进她柔软的胸里。
我感到安心,因为拥抱的姿势让我看不见她的神情,她也看不见我的。在我还很弱小的时候,我想过如果我是个瞎子,我的爱会显得更坦诚,我会因此多出更多的伤口,得到更多的信任。但我舍不得我从妈妈那里继承的绿眼睛,只好睁着眼,顶着我从未读懂过的她的目光,朝她所在的地方跋涉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