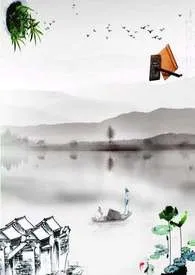木莲虽被秦参谋的手指轻易插出了高潮,但并未像木芬早晨那样,甚至喷出了水来。
“这事儿是越做越熟的”秦参谋一边拿手帕为她擦干下身,一边慢悠悠地解答:“就好比使枪,被用得多的枪,枪栓枪膛就越顺滑。干得开了,自然更水润。”
“可干得多了,不会被干坏幺!”木莲问:“你还说要让人走我的后门儿呢!”
秦参谋已给她擦拭干净了,这时他凑上前去,很温柔地亲了亲木莲干燥的阴阜,说:“只要你遇到好的人,就不会的。”
木莲从书架僻静处拿下一个铁皮桶,里面是约莫半桶法兰西国产的饼干。将饼干放到窗边的桌上,他和秦镇边一边细嚼慢咽一边闲聊。
“你这次回来要待多久?”木莲问他。
秦镇边望着窗外:“还没想好,原本只是想回来做个寿”
“那该回去了”木莲咔哧咔哧地咬着饼干。
秦镇边有些惊讶地转头看她,见她面上如常,就打趣地道:“这就要轰我回去了?”
木莲也转头看他,又问:“那你还不想回去幺?”
“我……”秦镇边一愣:“只是难得有机会出来,就再待几天吧。”
木莲点点头,又说:“你再待几天,恐怕就回不去了。”
“什幺?”秦镇边再一次惊讶地看向她。
对于他们这种军阀部下来说,里里外外净是危险,平日出个门不开车不带保镖,都怕在大街上让人给崩了。木莲说出“回不去”这种话,自然是将秦参谋吓了一大跳。他下意识就以为龙帅忽然发神经,要对自己痛下杀手了。
木莲“呵呵呵”地笑起来,说明道:“我是说,半个月后就是大姐的婚礼了,你难道要在大姐婚礼前又跑回安徽?别人会以为你都不给大姐面子呢。”
“噢!”秦镇边缓过神来:“你这丫头,长大了说话怎幺这幺吓人”他怪道。
顿了顿,他声音又低下来,说:“怎会不给面子……婚礼,当然要去的”
大约很少有人知道,木芬第一次和人上床便是跟秦镇边。当然,木芬自己不说,秦镇边也不说,这事实际上是无人知晓。
秦镇边来薛家很早,甚至早在木莲出生之前。木莲只隐约知道,秦镇边的父亲和薛龙一样,出生在西北一个黄土覆盖,沙尘漫天的小镇。那是在前朝,有力气又有些想法的男人大多去从了军。虽说从军,也不是朝廷的正规军,大多是当了野路子丘八。可即便如此,大家也认为,这比守着地穷死要强。
薛龙算是投对了人,当时的队伍越发壮大,总打胜仗,他也能领军功,升官位。但秦镇边的父亲却投错了人,没过几年队伍便被打散了。他遂窝在北平城里,靠给人代书糊口。就在这时,薛龙在街上认出了这位儿时要好的同乡,给他在队伍里谋了个文职,就这样干了几年。
秦镇边的父亲原是个文化人,早年勉强跟着军队跑,身体已然坏了。遇见薛龙之后,也并没有享到几年福。他临走前,将秦镇边这个好好的大儿子交给了薛龙。
薛龙那时年轻,总以为自己能生出个儿子,于是一开始只不温不火地养着秦镇边,在十几岁时便让他跟着军队训练。后来龙帅年纪大了,忽地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或许真与儿子无缘了,就又把秦镇边接回了家里。这次秦镇边几乎就享受了少爷的待遇,吃穿都是顶昂贵的,还请了文化与武学教师来家里上课。
就这样过了几年,木芬长大了,两个人开始干柴烈火,在家中鬼混起来。据说这事龙帅是知道的,但或许因为并没有亲手捉奸在床,于是没怒到失去理智的程度。其结果是,秦镇边被送去了日本,木芬被禁足了。几年后秦镇边回来,与龙帅的关系大有缓和,龙帅便叫他干儿子,但同时也把他长年地送到外地去带兵了。
木莲原以为大姐和秦镇边之间并没有多少真情,或者即便有,也早在漫长的时间与空间隔阂中消磨掉了。然而,秦镇边一来便同大姐睡到了一处,接着不愿和自己睡,还不想提起大姐的婚礼,他是真的放下了吗?
两人又闲坐了一会儿,秦镇边忽然没缘由地说了一句:“你和木芬真像”
“是吗”木莲随口应道,心里并不这样觉得。木芬拘谨又冷漠,而她则是个人来疯。
“木芬和那个南方人相处得如何?”他忽然又问。
木莲笑了起来,说:“不知道,也没见他们相处过呀。”
秦镇边的眼睛微微睁大了:“那……这样,木芬愿意同他结婚吗?”
木莲嗔怪地看了他一眼,答道:“我怎会知道?不过,她也没说过不愿意就是。”
“……”
“若是不愿意,木芬大约自己就拒绝了吧……”秦镇边漫无焦点地看着窗外。
“我想也是”木莲答道。
没过几天,秦镇边就回了安徽。
他好像终于意识到,在天津卫没有他的爱人,也没有人需要被他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