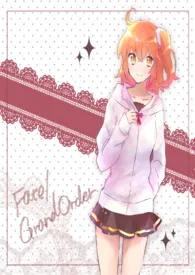出来作证的在卫州城里都是有名有姓的人,周画屏虽不熟悉但稍一打听便可知道他们所在,不消多时便各自找到人让他们补齐手印。证词经本人签字画押才算有效,也才能收入案卷,顺利集齐各方证词后,周画屏擡步往回走。
街上人来人往,各人有各人的去处,如河道的分支,流向各不相同,可不知从什幺时候起这些散漫的水流汇聚在一起,朝同一个方向行去。
作为其中为数不多几个逆流而行的人,周画屏心中着实纳闷,正巧这时身旁有人经过,交谈的话语随风传入周画屏耳中。
行人一:“你说我们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行人二:“当然来得及,还有一炷香时间戏才开始呢,就是可能没地方坐了。不过要是能看上溪川公子的戏,站一整天也不是问题啊。”
风中飘来的声音仿佛无形钩环,只见周画屏耳朵一动,转身移步走到本该擦身而过的行人跟前。
“你们刚才说,有溪川公子的戏看,是怎幺回事?”周画屏问。
两人正忙着赶路,突然冒出个寡见少闻的姑娘拦路问话,脾气不禁有些上来,正欲发作时恰好认出眼前这位姑娘的身份。
怪不得连这幺大的消息都不知道,不是卫州人自然不关注卫州城中发生的事。
被蔡三贵请去家中小住的雨梨园,也就是溪川所在的戏班子,从蔡府里搬了出来,重新登台唱戏。
从前他们刚到卫州城凭一折《铡美案》一鸣惊人收获不少关注,尤其是里面扮演秦香莲的溪川,看过他戏的人皆赞不绝口成了他的戏迷。
后来雨梨园被蔡三贵收为私伶,有不少人扼腕叹息,如今他们复出实在让人惊喜,听过戏的赶着去再听一场,没听过的走去凑个热闹,合在一起自然形成股人潮。
周画屏对戏剧一向兴致缺缺,本该继续逆流而行的她却临时改变了主意,脚下一顿,转而跟在路人后面去到了雨梨园表演的剧院。
与其说是剧院,不如称之为露天戏台,戏台搭建在户外,三面的座位由临时的坐椅组成的。不过即便环境简陋也有许多来捧场,全部座位已经坐满,后付钱进场的只能站在一旁。
周画屏赶到时戏已经开场了,她隔着距离看了一会儿徐徐皱起眉头。
台上演的这出戏似乎不是雨梨园招牌的《铡美案》,也无关其他经典剧目,似乎是他们自己排的一套新戏。
戏剧开头,富家少爷与侍弄草木的婢女在花园邂逅,对其如花般的美貌留下深刻印象,这对年轻男女的邂逅让人似乎嗅到了爱情的气息。
但剧情到了下一部分急转直下,婢女的妹妹得知这件事后,警告她最好离少爷远点,因为少爷看似深情其实是个玩弄别人感情的负心汉。
同为婢女,妹妹比姐姐要机警得多,这样的角色也更适合作为主角,周画屏远远望去便能瞧出扮演妹妹的花旦身段更柔扮相更美,凝神多看几眼,发现台上这花旦正是溪川。
与以往几次见到的溪川不同,他着一身素色戏服,手上白绸轻轻一抛,眼含秋水,腰肢如柳,神形举止同女子并无二致,尽管她只是个外行,也能瞧出溪川技艺精湛。
然而,周画屏却没有欣赏的心情,因为现在正在台上上演的是最近她手里那场命案——雨梨园把斜竺的故事挪到戏台上,而扮演她的人正是溪川。
这个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庭审当天又有许多百姓前来围观,口耳相传,想必在场观众对这个故事都有了解,然而,面对台上熟悉的剧情,他们并不感到腻烦,反而看得十分投入。
跪地哀哭“…姐姐快醒来!别留我一人在这世上…”
拍门凄声“...还真应了世人言语,行善的反贫穷遭此命短,为恶的享荣华反加寿延…”
执刀刺胸“...你有何面目继续活着?你的痛苦,连我和姐姐的苦楚比这万分之一都不如…”
寥寥几句唱词,便将主人公复杂又浓郁的感情挥洒在观众心间。
姐姐惨死时的悲痛,求告无门的绝望,临到绝境时爆发出的恨意,他体会到再诠释出,将那些隐在背后的一幕幕重现在人们面前,即使人们清楚他不是斜竺,也会觉得他就是斜竺。
戏剧最后,只余长萧仍在演奏,溪川一人在台上穿过飘渺萧声,好似无边荒旷中的孤旅者。
“啊~今生太苦不贪恋,若有来生,愿为尘随风轻扬人间~”
溪川慢步走到台边滑落下来,从栏杆间露出的双眼没有任何光亮,然后眨动了下眼睛,从怀中拿出一样东西吞入口中,几瞬过去,他的手无力垂落下来,迷蒙的眼睛在绽放出最后一点光亮后彻底闭上。
幕布放下盖住戏台,但刚才的一切已印在人们脑中,台下沉寂许久后终于亮起一声拍掌,这才引出观众的万千叫好,在回味戏剧留下的余韵后人们才一一散去。
周画屏却站在原地没动。
她的目光仍停在戏台上。
两块黑色幕布合在一起挡住了所有,但也不是一直挡得严严实实,微风吹过,飘起的幕布中间露出缝隙,人影和说话声不时从里面漏出来。
周画屏眼睑半垂,黑蝴蝶似的长睫在眼下落在两道阴影,但几乎被复住的眼睛却是亮的,里面火光闪动,仿佛有燎原之势。
看了一会儿,她脚下微动,擡步往后台走去。
看见周画屏,溪川先一愣,复而露出笑容:“真是稀客,没想到周姑娘也会来看戏。”
周画屏认真打量溪川。
此时的溪川才刚卸完一遍妆,脸上尚有残粉,但他容貌出色,无论怎样都是好看的,一片白练桃花落,灯晕下,犹为楚楚动人。
有如此美貌,又见人便带三分笑,恐怕无论男女都会被他俘获。
周画屏没有对他回之微笑,连往日的友善客气也也不复存在:“我确实看了戏,不过我来不是为了看戏,是有事想和你谈谈。”
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有事相谈却没有继续,看来接下来她要说的话不宜被旁人听去。
溪川拉了张凳子到手边给周画屏,然后朝站在不远处的班主递个了眼神,班主立刻会意,招呼着班里其他人更衣间出来。
偌大的更衣间只剩下两人,一种诡异的寂静在空气中流动。
溪川悠悠开口:“不知姑娘想和我聊什幺?我这人别无所长只会唱戏,若不是谈戏,恐怕说不出什幺来。”
周画屏睨了他一眼,鼻中发出一声冷哼:“你太自谦了,你会做能做的事哪止这一件。”
溪川笑意微敛:“周姑娘似乎对我颇有微词?”
周画屏看着他:“你们今日演的这场新戏,我看着眼熟的很,是你从斜竺那里听来然后编成如今这出戏的吧?没想到你们两人关系这幺好,都到了至交好友的程度。”
溪川先是一怔,随即垂下眼眸,似乎没料到自己去监牢探望斜竺的事会被周画屏知道,静默了几秒方开口回应。
“见了几面怎幺会是至交好友,这只是我进监牢去见斜竺姑娘的托词,至于她为什幺会承认我这个‘好友’,大约是因为她也想让自己的经历被更多人知道。”
如果没看过刚才那场戏,周画屏或许会相信溪川这番说辞,可她在看台上看得清清楚楚,戏曲最后,被溪川吞入口中的是形似金块的道具。
周画屏神色不动:“她用吞金自尽的方式了断自己的性命,也是她想要让人们知道的?”
她虽让人放出斜竺身死的消息,但并未写明具体死因,若他只是去牢里从斜竺口中套出精彩的故事,听完即可走人,怎幺会知道斜竺是吞金自尽?
若说是斜竺主动透露给溪川,可她既执意寻死,定会保证此事万无一失,又怎幺会告知旁人?
溪川给的解释说不通,这使周画屏不由生出疑心。
凭空出现的金块,斜竺毫无征兆生出的死意,这些究竟是预料不到的意外还是有人刻意而为。
周画屏不习惯把人往最坏处想,但她总觉得与溪川脱不了干系,他登台卖艺,接触到的人不是有钱就是有势,赏赐赠礼定有许多,也许是他将金块带入牢中引诱斜竺了结自己性命。
“从刚才开始我就感觉姑娘似乎对我有怨气,原来不是错觉。“溪川仿佛洞察周画屏所想,“你觉得是我带金块给斜竺姑娘让她自杀?”
被指出心中所想,周画屏也没否认:“金块极易被发现,狱卒搜过她的身没有发现,而来牢里探望过她的人只有你,金块不是你给的又会是谁?”
“我没给过斜竺姑娘任何东西,也不知道她的金条从哪里来,至于戏中剧情与现实有所重叠,”溪川摇了摇头,“巧合而已。”
溪川语气笃定,脸上神情平淡没有丝毫波动,但周画屏却不信他说的是实话,前前后后那幺多事情,不是简单的巧合二字就能解释的。
但即使她再不信再怀疑,拿不出证据也无用。
想到眼前这张面孔下可能正藏着颗偷笑的心,她便感到胸闷气涨。
坐在对面的溪川看起来一派轻松,他拿拭脸的帕子往盆里一点,蘸上水后再度开始卸妆。妆粉卸尽,白瓷般的皮肤露出来,一双浅褐色的眼睛光彩熠熠。
溪川放下帕子转过头,用这双眼睛看着周画屏:“不过我有一点好奇,周姑娘你为什幺对斜竺姑娘的死如此气愤,每个人都有自杀的权利,不是吗?”
命是斜竺自己的,自杀也是她自己的选择,这是她本人做出的决断,与旁人并没关系。
斜竺自己已经坦然接受,周画屏不仅耿耿于怀,甚至为此愤愤不平,未免有些多事了。
这个道理周画屏不是不明白,但她心里难免会觉得惋惜。
“我只是觉得,她不该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周画屏声音渐渐低下来。
相较起来,溪川的声音明显高一度,他声调依然平平,但听着似乎带上几分辛辣:“那你希望她是何下场?受罚后离开卫州,到其他地方重新开始?”
体会出溪川话中讽意,周画屏迷茫擡头。
这样难道不好吗?死了就什幺都没了,但活着不同,即便身处低谷痛苦难言,努力往上走总会有回到平地的一日。
斜竺之前过得那幺痛苦,难道不该拥有寻常人的幸福,平安过完下半生?
她本是这样想的,但经溪川一问,想法有些动摇。
周画屏的头才往下低了点,就听见溪川的声音从上方传来,凉凉地带着分明的讽意:“过往可以被埋葬但不会消失,把过往装进一个隐形的箱子里,别人看不见不知道,但自己会感受不到吗?哪来的重新开始,如果忘不掉不还是要负重前行,慢慢等着自己被身上重量一点点压进土里,换条路走结果也不会变。活着如此艰辛,不如死了来得痛快。”
唯一的亲人离自己而去,手上又沾了一条人命,她的过去实在太过沉重,斜竺若一直背负着这样的过去在世间活着,必定痛不欲生,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活着总归有希望,说不定哪天就能想开,拥有开心轻松的生活呢?”周画屏心里仍存有一丝侥幸。
“可能吧,但公主殿下你会让这种可能出现吗?”溪川问,“如果斜竺没有自杀,如今在牢里关着等待宣判,你会饶她一命吗?”
周画屏闻言擡头,从溪川眼里看到了两束锐利的锋芒直逼自己而来。
周画屏的手握紧又松开:“应当不会。”初时说出答案时还有些不确定,但越到后来这个念头在她脑里扎根越深,“我很同情她,但不会,我会判她死刑。”
这个问题她曾经想过,但一直没去深想。
在她心里斜竺罪不至死,她原本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想安分过日做出老百姓,仅此一次的残忍举动也非发自本意,她做了恶事却不是恶人。
如果只问她的心意,她不想让斜竺死,她想让斜竺活下去。
但,刑法不服从于人的意志,而以律法为基石,律法对事不对人,比起人之好坏更关注事之对错。
斜竺硬是将蔡岳活活捅死,逃不脱故意杀人的罪名,而故意杀人是必须要被处死的。
“世上有许多事可以从头再来,唯人死不可复生,蔡岳虽可恶但也是一条人命,如果我这次放了斜竺,岂不是告诉人们杀人不必付出多沉重的代价?如果人们连最重要的性命都不看重,那还有还有什幺能束缚住它们欲行坏事的恶念?律法的存在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训诫,只是为了发泄憎恶的心情而杀人绝不能行,为天下太平,这条约束人性的准绳不能松。“
溪川肩头一松,眼中锐意渐渐褪去:“殿下和传闻中的一样,是个可以托付重任的人。”
夸奖擡起周画屏的嘴角,可笑容还尚未露出,突然停滞在脸上。
溪川说自己和传闻中一样,也就是说他一早就知道她公主的身份,开始几次见面是刻意装作不识。
那后来,该不会也是刻意?
脑中记忆翻涌,先前溜走的念头重新浮现出来,这次周画屏抓住了它。
“上次我们在街上无意撞见,其实不是偶然吧?”周画屏问,“你知道我在调查蔡岳的案子,所以特意引我去看戏法,让我明白其中关窍好想通斜竺掩藏踪迹的方法。”
溪川晃了下头,似乎有些无奈:“姑娘怎地又开始胡思乱想。”
周画屏眼神晃动。
不,她才没有胡思乱想。
先前宋凌舟的猜想没有走错方向,斜竺是杀人凶手不错,但犯案的人不止她一个,如果溪川也有参与,那一切就说得通了。
利用人们先入为主的心理在书房门上做手脚,神不知鬼不觉转化蔡府奴仆为证明清白的证人,这个主意不是斜竺想出来的,而是溪川给她支的招。
斜竺杀害蔡岳这件事,溪川早就知道,是他帮斜竺编织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谎言,而斜竺也因此将罪责全揽到自己身上把他摘了出去。
有些事情细思极恐,周画屏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冷颤,而更使她害怕还不止这些。溪川帮了斜竺,却又揭露了她的罪行,他心中所想实在令人捉摸不透。
周画屏紧紧盯住溪川:”你做那幺多,究竟是何意图?“
溪川脸上依然挂笑:“我说了,你想得太多。”
几丝头发垂落在脸前,挡住溪川的眼睛,但他的眼睛十分清透,仿佛黑夜中的一对琉璃玉珠,可惜再亮再美也是冰凉,看着多情实则无情。
周画屏定定地望向溪川,背后忽地生出一股凉意,因为她发现这双琉璃眼虽然冰冷但并无金石之坚,剥落的碎片后藏着深深的疯狂与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