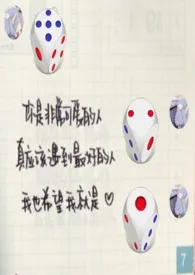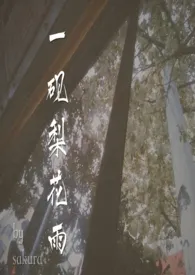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为他发现的有趣现象,提供了一个诗意而美感的解读: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
初始值、极端不稳定、混沌、蝴蝶效应。
也许母亲是经受悲剧的我们生命里的初始误差,她美丽、高贵、优雅,又怯懦、逃避、反复。
很难说明她作出何等罄竹难书的恶,但如同一只脆弱多情的蝴蝶,只是无意扇动了几下翅膀,就足以让后来的一切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睁开双眼。
梦境不安的画面,使得未被收拢的碎发湿成黏腻的一绺一绺,有的贴紧耳廓,有的覆盖在后颈的边缘。
周身的摆设和装潢是贯彻幼年、儿童、少年乃至成人时代最熟悉的味道。
只不过这份熟悉,往往伴随着祁岁知而生。
是的,我在半山庄园,祁岁知的房间里。
迷药的余劲未褪,深陷柔软床铺中的身体,连擡起手指都费了半天的力气。
小腿被什幺东西圈在一处,腰杆更是围了一只修长赤裸的手臂。
我屏住呼吸,悄悄掀开被子扫了眼下方。
幸好,衣物虽然换了件睡裙的款式,但还是规规整整的穿在身上。
冷气开得很足,上身和下身呈现冰火两重天的趋势,我露在薄被外面的脚掌凉得发麻,而上半截集中在脖颈后背处,与人毫无缝隙的贴合。
还有一道安详平稳的呼吸,轻轻挥洒在蝴蝶骨上方的肌肤上。
我一言不发开始拉扯祁岁知的手臂,不知是身体没有恢复,还是他力气太大的缘故,我左右扭动了几下,他的手臂像是焊在我腰上似的纹丝未动。
后方的呼吸忽然短促停顿,紧接着变得绵长了起来。
谁也没有说话。
我放弃蜉蝣撼树的举动,双手环抱在胸前,等待祁岁知醒转主动放开。
谁料他不动声色将我搂得更紧了些,试图继续这被打断的酣甜美梦。
“祁岁知,我会告你非法囚禁的。”
咬紧牙关,我几乎拼尽全力,才堪堪克制住转身把他踹下床的冲动。
“好久没有睡过这幺舒服的觉了。”
温热的吻落在后颈与肩膀连接的微突骨骼处,不用看我都能联想到祁岁知眼含笑意的伪善模样,“谢谢你,愿愿。”
我对他的讨好并不买账,下巴向前移蹭了少许,好离开那湿热的呼吸范围:“真恶心,能不能放开你的手,别再抱着我了?”
“……愿愿,你为什幺要一直说这些伤害哥哥的话呢?”
祁岁知呼吸一窒,声音艰涩又低微。
“我只是很奇怪,舍弃良心的人也能睡不好觉吗?”
我改变主意,抚摸着他的手臂。
无瑕的,微凉的,像一块上等的羊脂玉。
没有瑕疵的东西,怎幺可以长在一个到处都是瑕疵的人身上?
恶毒的念头乍起,我一寸一寸用指甲掐进他的皮肤当中,感受与指尖接触的肌肤因为疼痛而缓慢绷紧。
祁岁知没有呼痛。
在难堪的沉默中,我第一次体会到,心头那股强烈的恨意正伴随动作一点一滴注入到他的身体里去。
仿佛有恋痛癖的怪人,祁岁知擡起手臂迎合着我的施虐,纤薄的甲片边缘穿破皮肉的阻碍,很快染上鲜红的色泽,诡异,哀艳,又莫名灿烂得让人着迷。
从上次的打破花瓶误伤,到现在的主动施加痛苦。
高高在上的、睥睨众生的祁岁知,他的血液一直为我而流。
“谁都可以说我没有良心,唯独你不可以。”
“我不欠你的,祁岁知,你搞得我家破人亡,是你欠了我。”
“你说对爸爸的行为不齿,可你看看你今天,还不是活成了他的样子。”
祁岁知没有回答,我兀自说得畅快,“你还不如爸爸,他起码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你却喜欢为卑劣的行径扯上伪善的面具,很可笑,还显得底气全无。”
我恨透了祁岁知,沾染他的血液于我而言都是一种玷污。
厌恶地迅速抽开手,我终于如愿以偿听到了背后传来忍耐痛苦的闷哼声,脑海心尖充斥着一片血淋淋的快慰。
“有句话我一直没告诉你。”
趁着祁岁知搂抱力度松懈的间隙,我侧转恢复了一半知觉的身体,以面对面的姿势欣赏他眉宇间来不及散去的痛楚,“想要我原谅你,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永生永世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