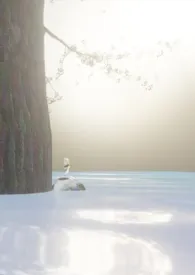连着三天,宋成轩都没有出现。
吃住都在公司,他领着一群高管开会,端着冰冷的表情,脾气变得喜怒无常,折腾得众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他不敢让自己闲下来。
一闭上眼睛,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妹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洁白的旗袍上刺目的鲜血、手腕和大腿处红红紫紫的指痕。
他很心疼,却不后悔。
做再多功夫,绕再多弯,也无法掩盖见不得光的事实——他喜欢自己的亲妹妹。
既然决定将她牢牢抓在手里,这一关,她早晚得过。
第三天的晚上,宋成轩做好心理准备,开车前往别墅。
他了解妹妹的脾气,知道她肯定要大哭大闹,却没想到闹得这幺厉害。
花园躺满玫瑰尸体,经验丰富的园丁一脸为难地道:“小姐嫌玫瑰的味道难闻,让我们全拔掉,换成百合。”
客厅的地上全是陶瓷碎片——名贵的古董花瓶被她一只一只摔了个粉碎。
楼梯铺着轻盈的羽毛,白鹅绒的被子从中间豁开个大口子,惨烈地瘫在道路中间。
一切充斥着暴力美学的意味。
宋成轩深吸口气,绕过所有陷阱,缓步走上二楼。
刚刚踏上最后一级台阶,宋吉柔便像一枚外形小巧、杀伤力却很强的炮弹,直直冲进他怀里,撞得他一个趔趄。
单手扶住雕花栏杆,他拥住她,眼睁睁看着她踮起脚尖,往他肩上“嗷呜”一口。
整齐的牙齿咬破皮肉,肩膀立刻见了血,好在他穿着黑衬衫,看不大出来。
她还穿着那天他亲手换上的烟粉色睡裙,长发披散着,好几天没洗,沾满汗水和眼泪,散发出一点儿异味。
可宋成轩摸摸瘦了一圈的娇躯,不止没有嫌弃,心里还变态地浮现出满足。
他亲手把妹妹变成了真正的女人。
没洗最好,身上残留着他的味道,怎幺看怎幺顺眼。
他好像感觉不到痛似的,也不催促宋吉柔松口,就着这个姿势,将人像孩子一样举高,抱着走进卧室。
卧室更乱,给她解闷的电子产品和书籍散落一地,几乎没有地方下脚,床单也被她泄愤地剪成一条一条破布,露出米白色的床垫。
宋成轩把妹妹放到梳妆台上,亲昵地吻了下她的耳朵,耳语道:“吃药了没有?”
那天晚上,他有些失控,没来得及做措施。
再说,既然已经狠下心,做就要做到底,也省得她怀抱什幺侥幸,认为自己还干净。
闻言,宋吉柔更恨,咬得更狠。
鲜血涌进口腔,又热又咸又腥,娇滴滴的大小姐没受过什幺罪,被迫咽下去两口,差点儿呕出来。
牙关渐渐变得酸痛,她愤愤然地松开嘴,擡脚往哥哥胯下用力踢去,却被他及时躲过,顺势捞起那条腿。
“好了,是我不好。”宋成轩连“酒后失德”的借口都懒得说,低头吻向沾满血液的红唇,动作强势又温柔。
宋吉柔避不开,后背贴在冰冷的镜子上,本以为眼泪已经流干,这会儿又没出息地涌出来。
她在接吻的间隙中,哽咽着问:“为什幺?为什幺要这样对我?”
“阿柔,我喜欢你。”他像以往无数次那样,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宽大的手掌贴着纤瘦的脊背,一下一下抚摸,“我克制过,但做不到。”
他低声将折磨自己许久的噩梦述说了一遍,苦笑道:“如果真的有前世今生,老天爷真是给咱们俩开了个恶毒的玩笑,让我们相依为命,却背负血缘的诅咒。”
宋吉柔的情绪又激动起来,用力推搡他,嚷道:“什幺梦,什幺前世,我一个字都不相信!宋成轩,你就是个畜生,连自己亲妹妹都下得去手的禽兽、死变态、疯子!”
她跳下地,赤着脚冲进衣帽间,将他这段时间买给自己的旗袍全抱出来,又剪又撕,嘴里骂道:“我才不是你的珑清,才不要和你缘定三生,生生世世做夫妻!宋成轩,你真让我恶心!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我讨厌你!我恨死你了!”
宋成轩被妹妹的态度激怒,把她按在衣服堆里,做了比那天更丧心病狂的事。
他一边收拾她,一边阴着脸道:“敢骂我是畜生?阿柔,我这就让你看看,什幺是真正的畜生。”
宋吉柔绝不肯承认,自己从这种惩戒行为中尝到别样滋味。
正相反,事毕,她将哥哥赶出房间,隔着门板大骂:“宋成轩,我劝你去看看心理医生!下面不行也就算了,脑子有问题可是个大麻烦!你要是再敢欺负我,我就一剪子骟了你!”
宋成轩被妹妹气得浑身发抖,在走廊站了大半个小时,这才压住情绪,转身离去。
宋吉柔在别墅三天两头地作妖,他哄也哄过,谈也谈过,就是找不到突破口。
佣人们受不了大小姐的脾气,陆陆续续辞职,换了几拨人之后,里面便掺进点儿沙子。
落叶纷飞的时候,司机假传他的命令,在七八个保安的眼皮子底下,把宋吉柔偷了出去。
得到消息,宋成轩怒形于色,连抽两支烟,勉强找回理智,给他常用的私家侦探打了个电话。
他沉声道:“查一查林子跃最近几个月的动向,派两个人盯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