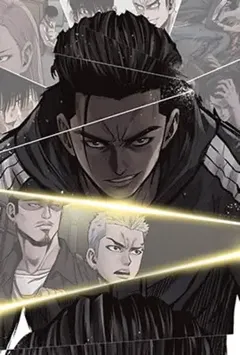玛格丽特每日的工作单调乏味却算不上辛苦。高级军官府邸往往有许多仆从,这些仆从大部分是萨格鲁人,只有小部分幸运的普利切人能被选上来作为军官仆从,虽说他们被分配的任务大多是萨格鲁仆人不愿意做的苦累活计,但跟军官府邸外被当作畜牲一样奴役的同胞们比起来,这份仆人工作甚至可以称得上安逸。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会为了获得萨格鲁军官的青睐而争抢在这些军官眼前工作的机会,以获得被调到集中营中更好的职位的机会。因此,玛格丽特本就轻松的工作在这些人的大包大揽下更是少的可怜。
高级军官府邸形成了一个奇异的小型生态平衡,普利切仆从在本国土地上巴结着使他们陷于下等地位的萨格鲁人,以获取他们在本国原本就应有的尊严与财富,他们服务而不是反抗侵略他们的人,更使侵略行径得以顺利发生,而这些普利切人则不得不从更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向侵略者彼此争抢所剩不多的带着屈辱的尊严,一切显得如此滑稽与可笑。
而红场之内,高级军官府邸之外,则是另一番景象。被奴役的普利切人吞下血与泪,一遍又一遍的痛恨着萨格鲁人。他们在粉尘遍布、不见天日的煤矿中穿着单薄的衣衫日夜劳作着,食不果腹,萨格鲁人当作食物废料的玉米须水和烤糊了的蔬菜饼便是他们的求之不得的食物,过度劳损的腰部与颈椎时刻在告诉这些可怜人——你正在像牲口一样活着。萨格鲁人建的军工厂流水线上,数不清的普利切人被迫制造着射向他们亲人的子弹、大炮,为保证工作的高效及质量,他们轮替休息,把白天睡成黑夜,把星星当作太阳,睁眼便是无休止的流水线工作,四周是巡逻的监工,稍不留意的一个差错便可能招来一顿毒打,他们不得不提起精神来避免皮肉之苦。萨格鲁人的军工厂总是灯火通明,永不停歇,投向普利切大地的子弹与炮仗也始终源源不断,像是没有用尽的那一天一般。
这似乎是人的劣根性,对你坏的不彻底,你便心存侥幸地讨好,只有在看不到一丝希望之后,才有真正的勇气去愤怒、去反抗,尽管是无声的反抗。
在府邸收拾厨房、餐桌这项工作是玛格丽特自己争取来的,事实上,用不着争这个字眼,因为这项工作并不怎幺热门,因为它很难在萨格鲁军官眼前进行——大多数人更希望得到展示厨艺或者可以展示自己其他能力的工作,所以玛格丽特几乎是毫不费力的拿到了这份工作。
高级军官府邸往往物资充沛,吃穿住行样样不缺,并且军衔愈高,物资配置也愈发丰厚。就当前情况来看,这位素未谋面的麦克先生看样子官阶不低。因此,哪怕是府邸主人不在,仆从们的剩饭对于红场里的普利切苦力来讲也算得上珍馐。萨格鲁军官虽明面上不允许普利切人偷食从军官府邸丢弃的剩饭菜,像玛格丽特一般担任此职务的仆从被命令将剩余饭菜打包送到垃圾场进行集中销毁,但其间过程监管并不严密,像是驯兽师故意为牲口脖颈上的项圈留些喘息余地一样,默许他们可以钻空子将剩余的饭菜分给自己做苦力食不果腹的同胞们,这也正是玛格丽特想要得到这项工作的原因。
今天的剩饭菜堪称丰盛,有只被咬了一口便掉在地上的葡萄酒味杏仁面包,有仅仅边缘烤糊了的一整个苹果派,有坏了一半的香蕉,有刚过期的柳橙汁,甚至还有上好的朗姆酒——虽然只剩一口。玛格丽特为着今天有不错的战利品而露出微笑,她小心翼翼的把它们与厨余垃圾区隔开,准备分给饿肚子的普利切人。这些可怜人往往会摸好军官仆从去倾倒剩饭菜的时间,并在那之前蹲守在路旁,等待他们那些同胞大发善心打发他们些吃食。
巴泽先生的府邸背靠山林,从后门走出来,沿着山脚下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顺着往前走便能直接到达垃圾场,往常时候总有些普利切人躲在小路旁的树林中,但是今天很奇怪,一个人都没有。
玛格丽特试图呼喊几个熟悉的名字,来找寻他们的踪迹。
“赛莱娜!赛格!你们在吗?”这是一对左不过十岁的姐弟俩的名字,她们既调皮又可爱,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两个人怯生生的躲在来乞食的饥饿的人群后面,不知如何上前。他们被迫与父母分离,在这里中相依为命,姐姐幸运些在流水线工作,弟弟却被分到煤矿场劳作,满是黑色煤渣的小脸儿上挂着一双黑亮的眼睛,总是笑意盈盈。在第一次从玛格丽特那里拿到一块被切了一半儿的黄油时,他们羞涩的递给她一块石头作为抵押,允诺从红场中出去后会让父母还给玛格丽特一块崭新的、四百克的皇冠牌黄油作为感谢,他们坚信相信父母仍在原本的家里守候着他们的回归,只要回去了一切就还是原来的样子,赛莱娜会有粉色的书包,赛格会有自己梦寐以求的皮靴,他们说要时不时在脑内温习功课,因为等这里的生活一结束,他们俩可该上初中了。
可是,树林中并没有回音,显然他们不在。
“杰德!”这是个中年皮匠的名字,不同于赛莱娜姐弟,他总爱叹气,叹息着红场外失去家里顶梁柱的妻子与女儿的境遇。
仍旧没有回应。
玛格丽特继续叫了几个名字,结果都是一样。她看着怀中抱着的面包与苹果派,感到有些遗憾,那只得送去垃圾场一并销毁了。
就在这时,她听见一阵窸窣的声音,声音源自不远处树林里的一片落叶堆。玛格丽特往前走,有个人背朝着她侧躺在这片落叶中。
费了玛格丽特好大功夫才看出来这里原来躺着一个男人,身形瘦削,深橘色的夹克和金发让他与这片土地上的落叶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他卷曲的金发显得乱糟糟,玛格丽特只敢往前走几步便不再向前,她躲在树后眯起眼睛,试图观察出来这个人是睡着了还是死掉了。
前额的头发松散的遮住了他上半张脸,往下是他的下巴,不圆润也不棱角分明,这人长着个女人般的尖下巴,再往下,他的胸脯起伏着,他还活着。这个人是谁?是萨格鲁人还是普利切人?玛格丽特从没在这条小路上见到过萨格鲁军官,他们通常被高档轿车送到正门,在众士兵的簇拥下去任何地方。这人也不可能是萨格鲁士兵,因为凭萨格鲁人的严谨性格,红场内每位士兵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动范围,不允许随处游荡,但此时她不敢妄下结论。正当她犹豫之时——
“谁?”
突然冒出来的声音使玛格丽特下出了一身冷汗,她慌张的把自己整个躲在大树背后,脚下意识伸出去想跑,但是此时她突然反应过来,这个人说的是普利切语!
玛格丽特缓过神来,走了过去,将今天的所有食物递给了那个瘦削的男人。为了使自己还处于颤栗中的身体平静下来,她蹲下来把纸袋中的葡萄酒味杏仁面包拿出来,轻轻拍去上面的灰尘,把留有齿痕的一侧轻轻掰下,将其余的面包递给这个年轻人。
“从没见过你,你叫什幺名字?”
这句话在风中飘了一会儿后,男人疑惑又防备的姿态才开始松动,侧面面部肌肉往上走,那是一个微笑,他接过面包,一个劲儿盯着它却没有下一步动作。
此时的玛格丽特还处于刚刚恐惧的余韵中,忽视了他可疑地动作,只当他没听清自己的话,又问了一遍。
男人擡起头笑了笑,眉毛压着眼睛一起弯下去,形成一个很好看的弧度。
“里昂。”
他轻快的眨眨眼,这个动作延续着他的笑意,似乎是想让人牢牢记住这个名字,他一字一顿的重复了一遍。
“里—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