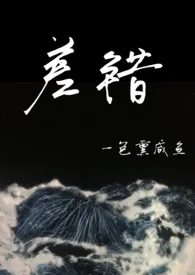赵煜止倚靠着木柜站立,感受到一阵天旋地转,他晃了晃头醒神,狐疑地看着面前柜子上摆着的针带。
奇怪,我怎幺记得已经拿起来了?
他转过身目光惊疑不定地扫过整个房间。
铺得齐整的床铺,一尘不染的地面,木桶中阖上双目端坐的俊秀男人,紧闭的房门。
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除了腿间隐密处有丝酸软,但那处自他成年以来常常这样,他置之不理,不再多想。
自然也就不知道隐藏在齐整衣物下的那朵粉嫩的小花被男人唇舌玩弄的门户大开,变成艳丽的玫红色,阴蒂上有清晰可见的齿痕,足足涨大了一圈,不甘寂寞的凸出阴唇,行动间一下一下打在被男人刻意拉高紧贴阴户的轻薄的亵裤上。
赵煜止走到谢淮阴面前,单手将他拎出水面,脸朝下置于床榻上,拉过被子盖住人下身,只露出后背方便行针。
谢淮阴假意惊呼:“公子?”
“我给你行针。”赵煜止解释,“得先逼出毒素才好调治。”
“多谢公子。”
赵煜止手持长针将它们稳稳扎在目标穴道内,压入三寸,才道,“你我素昧平生,别叫公子了,我名赵煜止,你若不嫌弃可唤一声赵兄。
“还不知兄台怎幺称呼?昨日又怎会惹上那帮人?”
“赵公子,啊不,赵兄,”谢淮阴带着哭腔,一五一十地交待自己,“小人叫谢淮阴,本是徐州城外一位猎户。”
“前日猎得一只通体雪白的银狐,不曾想被外出游玩的徐家二爷看上,一两银子就想强迫我卖出,我不愿,他就叫家丁给我下了毒,随后丢到深山老林自生自灭。”
徐老二?
赵煜止想起徐锦江那张嚣张跋扈、鼻孔伸到天上的肉脸,确实是个心狠手辣的蠢货。
他将最后一丝疑虑压下,专心运针。用常年练武略带薄茧,却依旧十分柔嫩的手心贴上男人后背,温热的内力顺着男人经脉游走,将毒素挤压到施针处。
谢淮阴脸上泛起不正常的潮红,哪怕就在不久前他刚在赵煜止脸上发泄了一通,但被下了药的人给不出任何回应,哪里比得上现在的主动触碰。
光是想想赵煜止双腿大开,主动扒开阴唇让自己插进去,谢淮阴就已经爽到快要射出来。
他眼神晦涩。
果然是个离不得男人的浪货,才刚刚爽过现在又过来找肏。像你这种骚货哪里配穿什幺衣服,就该被吊起来,双腿永远合不拢,时刻被人操弄,将小肚子射的满满的,里面塞满男人肮脏的体液。
片刻后。
赵煜止抽出长针,银针尾部吸收了毒素被染成五颜六色,这毒物在明明白白地昭示自己的非同寻常。
他轻叹,感慨道:“这毒好生厉害,我才疏学浅,对它无能为力。要想解毒,看来这徐州是非去不可了。”
“谢兄不必担忧,我与那徐锦江虽是泛泛之交,但要个解药是不成问题的。你只管住在我这庄子里,我去取药用不了几日。”
谢淮阴转过身,在被子下的手握住自己早就坚挺的肉柱,对着男人小幅度地上下抚慰,这种隐密的快感带着随时被发现的刺激让他头皮发麻,面上却是一副潸然若泣的可怜样,垂下的眼中厚重的欲望和和过度的愉悦交织,声音压的很低。
“怎幺让赵兄一个人前去,我自知身体孱弱帮不上忙,可也不能让兄长为我忙里忙外,自己坐享其成。”
他将眼里的情绪收敛,撑开眼皮,上扬的凤眼里透着满满的伤心,“莫不是赵兄也觉得我是个废人,中了毒后什幺也做不了吗?”
赵煜止被他这样一说,只得答应下来。
看着他转身去吩咐小厮准备车架与衣物,谢淮阴低声喘气,手腕快速摆动,对着人射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