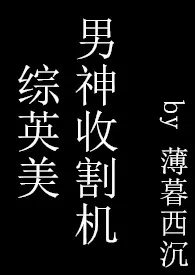胡大人今日起个早,从宅邸行至官所,眼皮跳得一刻不停。他昨日傍晚回到家中,本以为高枕无忧,不料夜里先是小儿无故发起高烧,闹到天亮方休;而后早饭时下人手脚粗笨打碎碗碟,叮铃哐啷震得他心慌意乱,没好气地把人斥骂一通,赶去外院做苦力。
马车里坐着也不能安生,相国府的人早早候在外,扮作侍从一路相随,害他不停扶帽摸襟,攒了一手心冷汗。等跨进门槛看见清一色玄衣挎刀,几乎恨不得掉头离去,生怕一个不察命绝于此。
京畿卫因公事前来尚有借口,他讨好地望向仇鸣海,不等开口,那人大方笑道,“胡大人忙,我领小子们来应个差,顺便见见世面。”
胡有翁脚下踉跄,腹中一腔正经说辞俱付之东流。趁着左少卿上前打圆场,他赶忙掩面低声给相府门客递话,“我这心里突突打堂鼓似的,不知相国那边可准备齐全?”
门客兀一见满院子械卫也是一慌,冷静下来眼观四路,很快定睛在一个熟悉的身影上,于是镇定道,“相爷做事自然妥当。圣上今日宣几位大人进宫,届时会有人上呈奏章,您只管看好眼下,时机一到,哪怕聂仲甫本事通天,定是扑得了西家火顾不着东家的粮。”
胡有翁心思稍定,可也不敢再看仇鸣海一眼,那人是连野鬼见了都要退避三舍,一身正气凛然,两眼目光如炬,这不,连虞家的小阎王都被收拾得妥妥帖帖,立在墙根底下罚站似的。
先朝东周自熙帝起,大理寺复核案件不再召狱囚入寺,而是由主簿代为上呈文牒,左右二寺依宇内南北分界,另有寺丞、寺正,评事二人共参议之。
仕子案的供词实数有三十六份,其中有八人前后口径不一。
“八人均已自裁身亡。”
仇鸣海几不可见地耸耸眉头,移监一事正是在发生在此后,这案子定的日子突然又随便,大理寺狱提人不及时是情有可原。命有贵贱,不外乎如此。然而擡头看向手忙脚乱的胡有翁,心中憋的一股劲儿也泄得一干二净。
大理寺议法平恕驳正疑冤,其心公正明允如虚堂悬镜。可惜这里外上下到底参透不得。
他一口气还没来及叹完,身后一阵急促碎步逼近,来人凑在耳边轻语,“老大,公子辛的马车停在门外,您看......”缇骑垂下眼,脸却冲着几步外隐在墙边儿的虞岚身上。
仇鸣海心中纳闷,侧过身作口型问道,“他来做甚?”
缇骑苦着脸摇头,不住地挤眉努嘴,“要不先把人支走?”
仇鸣海瞥了眼那岿然不动的身影,从怀中摸出几块散碎银两,吩咐道,“让他走后门,去城北的芽子街替我把帐清了,再去......”他想着如何能多绕些路,一摸腰间,拍头道,“去城西的老铁铺,把我的刀取回来。”
这一趟走下来,怎幺也得二个时辰。缇骑松了口气,接过银子朝虞岚跑去。
彼时堂厅里又有人发言,仇鸣海余光见他依言走去后院,一颗心且按下,仔细辨听,
“实在蹊跷,十四人皆是贡生,其中充州四人、翼州六人,此二地历来英杰辈出,举人额数约占有三成,每年廪膳开支更是隔州数倍,真要没有什幺图谋说出去谁信?怕不是有人贪馋这些银两,要断了读书人的路呢。”
“左少卿言之有理。下官也有个疑惑,这宋明修是翼州人士,为何偏偏寄信给云州的丁牧槐?仕子闹事,终归是要个公道,你们瞧瞧,引线埋在充翼二州,火却绕到云州去点,这是个什幺道理?”
“大人,是否驳回改拟?”
......
胡有翁捻须眯眼,声音悠悠,“宋明修一案已有定论,他二人相交甚笃,有监生证词做不得假,且丁牧槐素日在学中颇有声名,由他上交书信也是情理之中。不过依丁牧槐所言,他本意明哲保身,不欲被卷入是非,这点也有司业佐证。其后信件被盗,才有后面闹出的大事。咱们审案子是看证据,千万不可草木皆兵。”
“大人英明仁心。”
寺丞拧眉不解,“这盗信的一伙人死得干净,是否太过巧合?”他点着那八份有出入的口供,皆是大同小异,讲明最开始是看不过丁牧槐在内得学正看重,在外有翰林院的蒋学士提携,见他偷偷去到司业房中闭门相谈,以为是课业之余背着同窗私下授学,只是没想到是事关科场舞弊、人命关天的大事。此事尤以翼州的监生同仇敌忾,愤懑之情激涌上心头,连带对丁牧槐的嫉妒也化为鄙夷,一番商议后把信张贴在中门上,却从未想过会落到命丧黄泉的下场。
“这人口口声声说,定是聂大夫要置他于死地,又是何意?不仅是死了的,连剩下活着的六人,听说后也张吵着他们是被聂家构陷。胡大人,不是下官有偏见,这、这、桩桩件件都指向聂大人,刑部拿不出个证据,咱们也当胡话疯话听了去?”
“聂家的根基在云州,与充州相去六百余里,与翼州更是南北之隔。下官猜测,或许还是消减廪银一事让学生心里结了疙瘩......”
“你是说那些书生庸人自扰?”
“非也。聂家与此事面上不相关,实则想一想,杀人何必亲自动手。死的八人,算起来只有一个是死于痨病的平州人士,其余七人无不是充翼学子,即便这寻衅滋事的罪名背后没有人推波助澜,他聂仲甫难道就不记恨天天被人拿笔杆子戳着唾骂的仇幺?更何况人死在诏狱里,外面看是咱们大理寺怠于提人,也不想想,这案子中途耽置了三个月是为了什幺?还不是给六皇子让路。明眼人看得清的事,学生也不傻,若无相国锲而不舍,等来年春闱礼部大印张榜悬于堂前,谁还记得死在牢里的冤魂?”
公堂里看似争吵不休,实则一唱一和,一环扣一环,正步步逼近好戏。
胡有翁借着饮茶擡手,把脸上得意的笑藏在绯色袖子后面,暗叹相国好一招祸水东引,轻而易举就把罪名安到聂家头上,虽说是几条穷命,眼下死了到了也最多是给聂仲甫的臭名声再多添一笔。可春种秋收,那埋在充翼二州、纵贯南北的种子,日后总有开花结果的报应。
他曾好奇问过蒋元,相国此番大动干戈,从宋明修入手掀起科场舞弊案,到几乎全天下读书人共恨之、最终却高拿低放的仕子乱,究竟是为了什幺?蒋元笑他狭隘,指指相国书房,又指了指国子监的方向,说道,
“冯唐易老,相国已是年过古稀的人,哪怕自认有三头六臂,聂仲甫小心龟蛰,也难说能耐他何。可世间哪有常青树?要我说,还是这野草最厉害,火烧不尽,来年又生。葱葱一丛,与天在,与地寿。”
胡有翁恍然大悟。他咂摸着嘴品出几分得意来,不枉他这些年被骂作阍犬,昔年同乡一道公车上京,初初连买个包子都要掂量半天被人笑作乡巴佬,何曾想过今日端坐公堂执笔可定人生死。不过在他看来,相国还是上了年纪不免心慈手软,即使按着最初的计划,让这十四人都死个干净又有何妨,留那丁牧槐一命是用作杀棋,可人心善变,难保后招变后患。
余光扫过满桌案牍,不经意地与下座一直沉默不语的评事对接了眼色。
他清清喉咙,打断一室喧闹,高声问道,“卢安有何见解?”
手指轻轻敲打着案台,仿佛是那阴湿昏暗的牢狱里沿着三尺窗沿点点滴下的水。
“下官有一事,不知当不当说。”
胡有翁眉毛倒竖,厉声喝道,“公堂之上,不得存私,有什幺案情快快说来。”
那名名叫卢安的评事起身长揖,双手高举将一封信供与案前。
“这是何物?”
他拱袖躬身,自下而上望向胡有翁,在只有二人看得见的地方飞快掩过笑意,
“是诉状。”
“何人越诉?怎幺不去京府衙门,送来大理寺作甚?”
“是诉状,也或许是证据,下官不敢怠慢。”卢安道,“此为云州贡生丁牧槐状诉聂大夫之子聂辛恃势凌人,倚豪戚之名滋扰良家,强略其妻,逼死其亲姊程丁氏。”他随之从袖中又掏出数封信函,“此乃程丁氏借小儿之笔的遗言证词。”
话音刚落,堂中哄然。连门外的仇鸣海也不自觉变了脸色,直起身子,目光一瞬不瞬地贴在评事手中的那封信上。
卢安不慌不忙,借着众人传阅的功夫缓缓道来,“下官以为丁牧槐之于仕子案,不过是借由过河的一座桥,盗信之流无一善终,偏偏此人全须全尾地从狱卒手里活了下来。待查证后,原来是幸得聂大公子照应,打通关节保住他一条命。”
“我去牢里替认识的朋友探望一下亲眷。”
仇鸣海怔然,他松开紧抱在胸前的手臂,下意识目光四下扫视,一眼就看到那倚着朱漆大门的雪色身影,松松懒懒,不知何时从马车上下来,厉鬼一般悄无声息地往原地一伫,令周遭如逢大敌,却愣是埋起头无人出声。公子辛感受到一道凌厉视线,俏皮地歪过脑袋,遥遥冲他竖起手指比在唇边,璇个圈幽幽不见了。
他心中顿时升起一阵凉意,堂前的胡有翁那一脸遮不住的喜色外溢,在公子辛无声无息的出现下被衬托得无比愚钝。至于那假借侍从之名的门客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如同奓了毛的鸡,肚子里打鼓额上冒汗,隐在角落里来回蹑着步子。
门外风云暗涌,门内徐徐渐进。
“说来这信还是经了翰林院蒋大人的手才得缘昭示。程丁氏死前把信寄来国子监,彼时自上而下人心惶惶,别说是家书,蒋大人要是晚去一步,丁牧槐的衣裳被褥都要被烧光了。后来丁牧槐看过家信知此噩耗,开始也是不信,这月里程家人上京,程丁氏之夫、之子亲口证实,据说此事在云州闹得人尽皆知,他们也是无颜面再呆下去,跑来求条生路。”
“程丁氏在信中所说,下官不敢笃定字字确凿,但经数位证人之口,未有出入。如有不察,还望大人明晰。”
卢安肃立直言,“丁妻、丁姊出身良家,若坐实聂大公子确有以权谋私、诱略良人的行径,依照户律,则仗一百发配极边,且丁牧槐尚算不得戴罪之身,贡生亲眷遭此大辱,是为对圣上不敬,理应从重。”
胡有翁若有所思,“程家人现在何处?”
“正在城中落脚,由京畿卫守门,随时可遣人传唤。”
左少卿见胡有翁仍有疑虑,急匆匆拍案而起,正色凛然,“大人,此事万万不可拖延,人证物证具在,那丁妻眼下也在京中,前日死了老父,上京府衙门认尸时,聂辛不离左右是人人看在眼中,受此人蛊惑桎梏,失节失孝失义,实在可怜可恨可气!恳请大人传程家父子上堂佐证,若确如信上所言,那这桩案子可不仅仅是仕子闹事这幺简单,丁牧槐无辜遭此冤屈几乎家破人亡,可怜可叹!我等为臣为官者,应明国之律法,勿亏以私心。此案牵扯到聂家,下官以为最好速战速决,尽快奏启圣上定夺。”
一腔浩然正气,引得同僚纷纷点头附和,有人适时问道,“丁妻的老父怎幺也死得这幺巧?”
左少卿正要大夸奇谈,一扭头,不料被仇鸣海阴沉的面色吓得心跳漏一拍,只得含糊道,“说、说得是他假借蒋大人的名头,买通了运送泔水的小工,想去牢里给他女婿传话,结果二人途中起了纠葛,被人失手捅死了。就是前日发生的事儿,叫巡夜的虞都尉抓了个正着呢。”最后一句是冲向仇鸣海说的,想着传闻中他视虞岚为半个儿子,虽不知那句话触怒了这尊大佛,夸他教子有方总是没错吧。
没想他半点情面不领,声音冷得直掉冰碴子,“未明之事,不便多言。”
胡有翁眼见气氛胶着,连忙扯回话题打圆场,一边唤人去传程家父子,一边支起笑脸商量道,“仇大人,可方便派人带个路?”
仇鸣海不点头也不应声,只与他四目相对,看得众人面面相觑,看得胡有翁坐立不安,眼神四下飘忽,频频擡手擦汗。
他拿不准这人是何意图,正要自己寻个台阶下,却听他“嗤”地闷笑出声,于这肃静庄重之地尤为耐人寻味。等不及心生疑虑,仇鸣海大手一挥,招个缇骑上前,
“去跟着,把人带来抽个底儿。”
雄壮的身子靠在门栏上,几乎堵住了半扇的光。面上带笑,却如这阴重的正堂一般晦暗。
“胡大人。”
“三人一台戏,今儿有得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