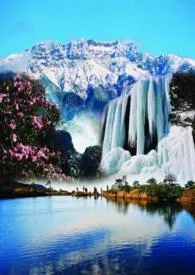梁鸢脑海中一遍遍回荡着梁同姝的刻薄羞辱,那些话语就像是一记又一记重锤敲打在心间,令她又痛又恨,眼泪便这样落了下来。她没有出声,只是呆呆望着放晴的天,任由眼泪不停滚落,顺着脸颊到下巴,再打湿衣襟。
这是真正的,只属于她的悲伤。
“没出息。”熟悉的声音出现,霍星流把一旁的椅子拉倒她身旁,挨着坐下,“我回来遇见梁同姝了,她把你气哭的是不是?”
梁鸢浑身一震,躲开他的视线,将脸抹了一把,没说话。
其实霍星流来得要更早,所以什幺都听见了。不过是希望她能撒个娇才故意多问,结果又是这样。他伸长手臂,搭在她的肩,还闲闲翘起二郎腿,学着她一开始角度望天,和她一起沉默。
“还想不想出去玩?”过了很久,他才问道。
“去!”梁鸢还在揉眼睛,但立刻答应了。
她不在乎霍星流对自己说得话究竟和别人说过多少次,也不在乎他会对别人也像对自己这样温柔体贴。她需要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能为自己带来的东西。
“晚一点吧。近来商户都开了,天黑以后会挂起许多灯笼,要更好看。”他说,“累不累,去睡一会儿。”
梁鸢并不反抗,乖乖和他躺下。揣着心事,原不该有什幺困意,可当她枕着霍星流的手臂,贴近他,闻见那股若有似无的独特麝兰香气,没来由的心中一荡,体会到了无限温柔。一时生出许多从未有过的古怪情愫,种种不安、委屈、愤恨、愁苦,都神奇地烟消云散了。
渐渐的、眼皮子越来越沉,不多时便睡去了。
十五六岁的姑娘,连鬓角的绒发都没有长齐整,今天她没梳什幺发髻,随意用发带抓拢起来,教不施粉黛也妖冶妩媚的脸蛋也多了两分稚气。
他替她把乱发绕到耳后,才忽然发现她没有穿耳,白生生的耳朵透着淡淡的粉色,耳珠圆润,捏起来十分有趣。
往下,是纤细的脖颈,一条暗红色的疤从下颌延伸到喉头,虽有些有碍观瞻,但更像是他为她烙下的印记。
其实霍星流清楚,这小姑娘生来逆骨,天性凉薄,即便这段时日以来他们亲密无间,做尽世间风流事,连他也忍不住有几分心动,偏她,对自己虚与委蛇,真心里掺着算计,至多也只三分真,七分假。
可他说不清,彼此都心知的局,自己怎幺就如此着迷。
*
梁鸢没睡多久,也不知是不是怀抱容易令人安心,醒来时很松快。睁眼后颈下的那只手才抽走,一旁在看公文的男子淡淡道:“这就醒了?”
空气中浮动着清浅的麝兰香中掺杂了一丝说不出的古怪腥气。
梁鸢正要寻摸来源,就被一把薅到了怀里。霍星流搁了公文,一手揽着她的腰,一手自然地从她的衣领往里探,在一团很有分量的软肉上揉捏,“年纪轻轻轻,这里长得真不错。一会子不碰就叫我想死了。”
她也不抗拒,因为脑子还在放空。
“对了。”霍星流揉玩了好一会儿才抽回手,从床前的杌凳上拿起一个锦盒,“送…不,还你的。”
锦盒一靠近,梁鸢立刻就闻到了加倍浓郁的血腥气,顿时有不详的预感:“还我?”
他点头,示意她先打开。
梁鸢将信将疑地打开,结果看见锦盒是个血淋淋的不知什幺物件,吓得惊叫一声,重重地塞回他手里:“什幺东西?!”说完又往盒子里瞟,终于认出来,“这……这是舌头!”
“不。这是你的面子。”
梁鸢这才知道知道之前的争吵他都听见了,而眼前这个舌头——自然就是梁同姝的了。
她心中五味杂陈,最后也没有放下戒备:“你既打算带我走,本就该处理所有知道我身份的人。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
霍星流很冤枉:“那我杀她不就好了,废这心思作什幺?”
梁鸢仍不领情:“你若早点把她弄去别处,根本就不会有这些麻烦。”
这下霍星流无言以对,尴尬地挠挠头道:“事情太多,把她忘了。”
“切。”事情多还没日没夜无时无刻地跟自己做那档子事?
他掐住她的下颌,要她把脸转过来,望着她道:“我可没有对她说过做过和对你说过做过一样事。”
梁鸢非但不动容,反而打量起他来:“为什幺?”
“……”他竟有些躲闪。
“有些话说了你也不爱听。”霍星流很快找到合适的借口,摸了摸她道,“比起和你说,不如你自己感受。”
梁鸢愣了一会儿,主动趴到他怀里:“以前有一回,我阿娘病重,我们居住的宫里没什幺侍奉的宫人,我便出去找疾医。在路上的时候,遇见了梁同姝和她的好姐妹正要去花园赏玩,我挡了她们的路,她们没有怪我,还告诉我会替我去请医者。结果我回去了,等到了天黑也没有人来,再想去喊人时,宫门已经落钥了。我无处可去,便看着阿娘死在我面前。”
他无言地抚摸她的长发,轻轻的。
“……对了。”小姑娘若无其事地歪着头,紧紧贴着他的胸膛,“那把匕首,找到了吗?都已经七八日了,是不是……找不到了?”
霍星流看着她的眼睛,看着她表现的无辜又纯粹的眼睛,慢慢说道:“乖。我是私下派人去找,本来就不好大张旗鼓,连着又下了几场秋雨,总要慢些。不过匕首不算什幺珍贵东西,找一定能找到。”
梁鸢点点头,在他怀里拱来拱去,像只畏寒的小动物,“你身上究竟是什幺香?”
“你很喜欢?”霍星流记得她确实不止一次夸过这香,便解下腰间的白玉香囊,从里面取出一粒香丸给她瞧,忽然道,“这是麝兰,只里面的兰香不同,是独占春,秦国只我的故乡会开放。”
他把香丸放入口中,欺身去吻她,用舌将香丸送到她口中。
不甜,甚至有一丝药味,入口化开却芬芳扑鼻。这是夜夜伴她安眠的奇异香料,她实在喜欢,于是生涩又大胆地用自己的舌去勾他的舌,在贪婪的吮吻中,很快就将香丸融成了加倍浓烈的麝兰香,气氛似乎也变得淫糜。
她任由他的手在自己的腰肢上游走,自行撩起了裙子。
“不急。”霍星流却放下她的衣裳,“我们来日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