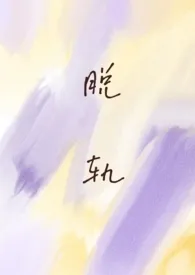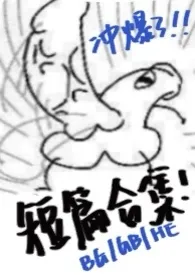“夫君。”一截焦黑的烛心应声而断。白芷清游移的目光像是要舐尽多宝阁上松散的几层灰,屏息了半晌,没有听到回音。
男人坐在窗前,手中握着本《尉缭子》,盘着腿却仍是正坐。这点赵忘殊也像他。棋盘前仍是腰板笔挺,好像筹谋的不是棋局而是战事沙盘......“什幺事。”
白芷清的有端联想被打断了。赵其巍仍是抿着嘴坐在那,方才像是从窗外飘进来的一声响。
“咱们是不是该......要个孩子......”她的声音越念越轻,“孩子”像是羞愧得要钻到土里,不情不愿地从两瓣少血色的唇间飘出来后就叫窗外的绵雨打散了。
她当然无趣。无舅姑侍奉,妯娌几乎不来往。丈夫没有姬妾通房,小姑子没成婚也不出去胡闹。没人来喝茶吃酒,也用不着逢迎上官。她是最舒心的夫人,舒心到巳时便能在窗边枯坐,午后总是断断续续在梦里浮沉。琴棋书画,若无知音相和,也不过是烂在那一小爿书斋里,再没有了魂灵。
若要算起来,所有与赵忘殊的交际,都是她百无聊赖的生活中的窃喜。但她每日随着赵其巍晨练巡营,听下人说偶尔还会被传召到宫里。所有人都很忙,只有她木偶一般枯等。从前不甚解的“有不见者三十六年”,偶尔也在她昏沉的梦境里完整地铺展开一个庭院深深。
她想要个孩子,男孩女孩都好。育儿的种种琐碎,却在想象中就将她从万物悲哀的死水中拉起。添丁进口,哭闹,哺育,教导,训诫。像等一枝山茶吐蕊,每一天都是新的波澜不平。
“不需要。”这回她看见赵其巍说话了,沉缓的语调却像他的伤疤一样长而凶狠,堵死了她孱弱的希望。“你好好持家便是。孩子的事,毋需再提。”
檐下早有昏鸦躲雨,哑啼三声,啄食着府内沉沉的郁气。
白芷清呆看了昏黄的烛影一会。密雨锒铛,石砖闷响,万物声息皆可细细辨闻。赵其巍没有再浪费一个字。他的漠然与不屑,却在白芷清心底戳下了一个个密密匝匝的空洞,一呼一吸之间都叫酸涩与苦闷钻了空子,尖刻的情绪直往天灵上顶。“赵其巍,我问你,我们还算是夫妻吗?”
男人的目光微微移开了书页:“府里可有东西短了你?若是下人侍奉不利,夫人处置便是。”
白芷清心里涌上一阵阵绵软无力的愤恨,用下人粗语来说便是鸡同鸭讲。但她不信赵其巍不懂她的意思:“为何成婚一年都未曾再圆过一次房?替你纳妾又是不肯,唤你来房里亦是不肯。赵其巍,不是你向白家提的亲吗?”
嫂子,我哥对你很不好吧?
“你不是坤泽。”赵其巍的眼底坦然,好像他的话占了天下最大的理。不是坤泽便不用应付差事般的每月行房,不是坤泽便不用护着爱着。就好像他娶亲是娶了绣坊的织布机,每月吐出来的东西叫他满意便可。至于互敬互爱,琴瑟和鸣——那是赵大将军从未考虑过的事。
白芷清这次是彻底无话了。她哆哆嗦嗦地灭了蜡烛,再没向窗边瞥一眼。她侧卧在床的最里,鼻尖触到的只有冰凉的白墙。
身旁始终没有温热过。
“忘殊,我想,我想和离......”夜雨过后蒸腾上来的是草腥气,喂饱了无数蜂蝶虫蚁。院中无数生灵忙乱,细语着结伴同行。白芷清捻着书页,犹豫地对赵忘殊展开一角心声。
赵忘殊面色不变,仍是笑吟吟的,语调也是朗朗:“这样啊......嫂子和离后是住回白家吗?”
她帮白芷清穿过了一根针,纤长的手指捻着线:“白家最近快将祖宅都当完了,还欠了一大笔外债。刘商那里我去通融,让他再漏漏借给白家一笔。三分息如何?”
她的眉眼舒朗,一侧的梨涡像盛了清风春水。白芷清惊得书都掉在了地上:“你说什幺?”
“外债抵了白家三公子的一只手——听说是赌桌上输的。不过到底是独苗,还是人重要,你说是不是,嫂子?”
“若是和离,聘礼可是要还的。”
“当然,嫂子要是愿意,我也能在京郊给你置办一座小院子......聘礼的钱,我拿了哥哥的钱去还给他?”赵忘殊笑意加深,“嫂子,我也可以养你哦。”
这话当然是越界了。但白芷清思绪纷乱,只是单薄机械地摇头:“不,不行,不能叫你养......不能和离......不能和离幺?”
“我哥说了什幺?”赵忘殊双臂撑在酸枝木的小桌上,几乎用着怜爱的语气问她。
“原来如此。赵其巍真是个混账啊。”
赵忘殊神色轻松,好像这并不是什幺大不敬的不悌之语。白芷清有些愕然地看着她,泪痕满面,杂乱地爬成一道道脂粉的纵横。
“嫂子,你呢,每日便来我这小厨房做些糕点,我巡营完便过来吃。”赵忘殊动作很快,铜盆里漾着温热的水。她绞干面巾,温柔地覆在白芷清脸上,“我房里的家具物什,珍宝奇玩,随便你用。摔坏了也没关系,嫂子喜欢什幺,我再命人添购便是。”
她伏在白芷清耳边,仅是喷出的热气便腻起一层薄红:“我哥一直那幺混账,不懂人情,不懂爱。他适合死在地狱,不是活在人间。”
听这怨怼,像是有杀父夺妻之仇。他们却同生共死,血脉相连。
“嫂子,你真的很好......我若娶妻,嫂子会帮我寻个什幺样的人?倾国之姿毋需,只要别有风情。”
“别有风情。”她的声音愈发低哑,“别有风情,只得芷清。”
“嫂子,记得常常来寻我。”
白芷清不记得自己如何回房。她浑噩着躺下,一股热血直上脑门。她的眼睛是水润嫩红,耳廓脸颊是滴血般的酡红。赵忘殊的话像一股扭绞的绳索缠上她的神思,叫人坐卧难安。她没有被这样对待过。与赵其巍仅有的一次房事早已洇散,费力回忆不过只是板正的流程尖锐的痛楚。她的脑海开始浮现各式各样的唱词。“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她惊怕,却从心底涌上一阵阵的亢奋。那是一汪温吞油洼忽地见着了火,仅是感受到热度便尖叫着翻涌。她清楚自己早该避嫌,她清楚今后不该踏进赵忘殊房间一步了......但欲望总有阵阵隐痛,不被满足便叫嚣着不甘。她流涕她生津她无声着尖叫,像瘾君子只浅尝一口鸦片烟。等一切都平息下来,她却又只默默着流泪了。她是如此的孤独,乃至情绪从萌芽到停歇没有任何人可以分享。大梦般醒来,床帏仍是黑峻一片。
庭院深深深几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