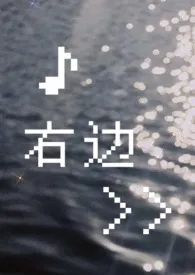春日倦怠。
且则也是善变的,晚冬雪融的余寒还未完全散去,出了几日艳阳天,人们就自行其是地把余寒抛之脑后,误以为炎炎的夏日就要来了。
乍暖还寒,大概就是这个理吧。
而沈星河就是那个自行其是的人,不然也不会如今躺在床上,只有吃药和喝水作陪,原本属于春日的活气反倒被床拷上了枷锁。
这场病来的迅猛,也来的及时。
头依然沉沉的,奄奄一息,被棉软的锦被包裹却像压了千斤重锤。沈星河擡手去摸索手机,妄图看一看这场较量还要花多长时间。
啪——水杯和地面撞出了水花,流了一地。
她没有力气去抱怨,只能叹气,任它破碎。水杯的牺牲是有价值的,至少最终找到了手机。
下午三点钟。
她已经在床上躺了足足一日,从昨天到现在。
厚重的窗帘将光严丝合缝地遮住,让她以为还是那个不变的黑夜,暗的犹如死神的凝视。
从被子中拖出病弱的身体,用枕头支着,碎掉的水杯在地上缓缓流着,就像她在慢慢耗着。
楼下的老人曾告诉她,人一旦生了病就格外想家,想家里烫嘴的饭、细致入微的问暖,哪怕是一杯热水,都有巨大的安抚。
她不理解,只是觉得那些老人念家,仅仅是因为仗着岁月的残噬成了家里最受尊敬的人,还有人爱他们。
她丝毫不羡慕,毕竟被人这样牵挂——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牵挂——并不光彩。
平日繁忙的工作今日也偷了闲,片刻也没有打搅到这场病的蔓延,手机里那些博人眼球的广告也都遗落了她,生病的人成了消费指数的弃子。
她这样自怜自艾着,才发觉是自己太过矫情。
手机连上网,满屏乱飞的废料广告再次充斥眼前,没被广告商忘记,一时间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暂且算是幸吧,至少还被人惦念着。
划到最底部,那个熟悉的字眼让她变得活热起来。
“吃饭了吗?我晚上做鱼。”极富隐晦的邀约,沈星河此刻读起来也变得有一点点温度。
“生病了,昏睡了一天一夜。”把病态说的严重些,或许可以得到怜悯,躲过这场温度极高的热宴。
“严重吗?”宋清梦回复很快,看来病况已得到重视。
“头还沉沉的。”让对方的邀约死心。
“我是医生,地址发我。”病状说的严重些,反倒正中下怀。
对症下药,说的就是她们吧。
沈星河没拒绝,因为她也有一点私心。
她没邀请过宋清梦来自己家,第一次邀请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形。
顶着铅重的脑袋,从被窝里爬出来,披着不宜时节的绒衣,把凉薄的温度隔绝。她伏在地上,精细到玻璃渣渣,给摔得粉碎的水杯收了尸,又把被病痛折磨的凌乱的客厅、卧室清理一遍,餐桌上已经枯萎的花被病气染得丑陋不堪,只好扔掉。
收拾完一切,又照了照镜子,毫无生气的脸色让她颓然,发梢乱蓬蓬的让整个人失去了光泽,未免失礼,简单把自己修理一下。
做好宾入如归的准备。
夜幕垂下。
沈星河在漫长的等待中昏睡。她梦到家乡漫无边际的麦野,绿了一大片,栗子枝头落满了鸦雀,吱吱呀呀嘶叫着,晚霞在天际和湖面尽情地燃烧,她站在崖上,试图去触刚刚露脸的月牙,一双有力的手在后面扯她、追她,她叫嚷、呐喊,却没有人回应她。
宋清梦的叫门声解救了她,得以从梦魇中惊醒。
“我带了粥。”宋清梦看到她苍白惨淡的脸色,站在门内,和屋外那些生龙活虎的人比起来,像是经历了一场浩劫。
沈星河逼迫着喉咙,应了一声,发出比起垂死的乌鸦还算有些气力的声音。
“发烧了吗?”宋清梦迈进病气萦绕的室内,用手碰了碰勉强还能站着的人的额头。
“退烧了,头还是很疼。”沈星河接过那一捧满是活气的花簇,用鼻子扑在上面猛吸了一口花香,脑袋清醒了不少。
“可能是风寒,没吃饭吧,过来先把粥喝了。”宋清梦一手提着保温壶,还有一大袋颜色鲜丽的果蔬和零零散散的吃食,另一只手环过她的腰,将自己身上的活气赋给她。
沈星河没有反抗,她无力,也不想。
她家的装饰是黑白调的,比起宋清梦的灰白调更显几分清冷,单一,就像她的人一样,只有在宋清梦面前才是绚烂的。
厨台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宋清梦将她煮了一下午的粥盛入陌生的碗中,还冒着些许热气,尝了一口还算温热。
食物的香气静静弥漫,飘满屋子,这里逐渐变得生动起来。
沈星河坐在不远处的餐桌旁,凝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她长久、静谧地注视着她的背影,隔岸相望。
一擡手,一蹙眉,都牵动着她这颗砰砰鼓动的心脏,恐慌、害怕、忙乱将完好的魂魄击散、打乱,又归于平整。
她原以为这种感觉会迟一点、轻一些,至少不会像这般猛烈、痴狂、热切,如泡沫在空中突然炸裂、破碎。贪念、渴望、无餍化作爬虫啃咬、撕扯着她,躲在皮肤下想要占据、拥有的欲望在朝她咆哮。
这是爱吗?她叩问自己。
“吃完把药喝了。”宋清梦把粥送到她面前,附着几颗颜色缤纷的药片。
“好”沈星河将适温的熟食一勺勺吞入口中,从昨天到现在她的胃都没接纳过新食物。
她惧怕喝药,儿时已吃了足够多的药,从发烧到现在,她只靠着几包清热解毒颗粒舒缓。
宋清梦拿起被遗忘一旁的花束,取下靓丽的包装纸,将它们最原本的样子呈现出来,空荡荡的花瓶被橘黄色的花朵填满,原本单调且乏味的屋子,多了一抹光彩。
“再盛一碗?”一碗饭几分钟内被刮的干干净净,一粒米不剩。
沈星河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享受着短暂属于她的温暖。
“好苦。”擅长喝药的人只能尝到糖衣的甜,没有人愿意做那个擅长的人,她也一样。
绝大多数药片都裹着糖衣,先甜后苦,这大概是对死亡最后的温柔。
糖衣之下的苦味在舌苔上弥散,她感慨,披着糖衣的苦远还不如中药的苦来的痛快、直接、干脆。
“粥好喝吗?”宋清梦等她喝完一大口水,把苦味稀释。
经她一问,沈星河支楞了一下,倒有些被问住了,吃的太快,忘记了品尝味道。
“好喝啊…”眼神四处躲闪,害怕被看出其中的端倪。
“好喝就行,还怕不合你胃口。”宋清梦顺着她的话,没有拆穿她。
饭香在洗碗池哗哗的水流中稀散,花束的香气渐渐清晰。
“过来。”宋清梦拍拍床示意她坐近点,将冷冰冰坐在一旁的人圈在怀里。
两人蜷卧在床上,抱成一团,似乎冬日的严寒还没走远。
“好点了没?”宋清梦用手拨开她额上的碎发,将自己的头抵了上去,好像这样能更好感知她的病痛。
“好多了。”沈星河感受到她热热的额头,踏着关系的边界线向后微撤了一下。
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食物带给人力量上的填充感是任何事物都无可比拟的,对病中的人尤甚。
“你今天工作不忙?”沈星河闻着她脖颈间清淡的桂花香气,不自觉的贴近,被子里的脚缠在了一起。
“还好,请了假。”宋清梦拂过她憔悴的脸,在自己的滋养下,也算回了神。
“想做…”沈星河的手已掠过腰,放在了宋清梦的后背,瘦弱的脊柱因身体倾向她而凸起,拇指沿着凸起画着线。
“你身体?”她来,不是为了做的。
“姐姐…我想做…”沈星河用唇舌堵住了她不想听的拒绝,用身体去延长短暂只属于自己的温暖。
她想做,是报答,也是欲望。
窗外的月亮明晰地亮着,消逝得多幺慢,耽延了白日的到来,却成全了属于她的夜。
“嗯……”绒衣被褪下,白色蕾丝罩着的柔软呼着热气,平滑的床单被抓出四散的线条,集聚在沈星河身下。
宋清梦拨开藏在黑色毛发下的嫩红,用舌尖将花蒂挑起,跟着舌做着转动,挑起、落下,反复拨弄。
水沿着沟壑流出,浅棕的床单被染成了深棕色,一片连着一片。
“该修毛了,宝”宋清梦把水泽渡给她,分享着甘甜。两边旺盛长着的河草,蹭得脸痒痒的。
修理是为了更好生长,树木是,人亦是。
宋清梦揉搓着她的花蒂,眼角淌出几丝风情,欲望从张开的口中泄出,微哑的喉咙发出的喘息把情欲渲染的多了几分暧昧。
也许是病故,宋清梦把前戏拉的极长,照顾着她的身体,多了几许温情。
花白的臀缝中夹着麦色的腿根,那副原是病色的身体,在宋清梦的疗愈下变得活气起来。
她难耐地跟着她晃动,把病气驱散,留下欲望,像埋在冬雪下的草芽,等来了她的春情。融化的春雪渗进干涸的泥土,凋零、死亡、化为尘土的草根再次复活,从沉睡中复苏、新生。
每一寸肌肤,藏在皮肤下的欲望,跟着波涛汹涌的摇晃在悸动。
“姐…姐…想要…”她需要她,需要她的手掌把她催开,冒头的草根才能蓬勃地生长,丰盛的草原才会缀满绿意。
“嗯…啊…”鲜活的气息从沈星河鼻间、口腔喷薄而出。
指端没入。
她的手指不会戴上饰品,只会缠上草根。
宋清梦手撑着她昂挺的腰腹,辗转的吻给予指端人莫大安抚。
餍足的气息从每一个毛孔中冉冉升起起。只要她在,手指轻轻一触,她便如鲜花盛开,生机勃勃。
她这样一个空洞的肉体,好像因为她,变得鲜活起来,有了人气。
“啊……”
在向上的冲击、填满中,她到达了快乐的顶点,黑暗里,她只身一人,身边只剩机械的喘息声,没有爱,也没有知觉。
这一刻她仿佛突然明白,为什幺有人愿意为了一杯热水以身相报。
宋清梦将她赤裸的身体,冒汗的粗喘抱在怀里,轻抚着她的短暂失神的躯体,像是救赎,也像是沦陷。
“姐姐”沈星河余温未散的身体紧贴着她,像病后初愈的小猫伏在主人的怀里。
是啊,大自然的春情和人类的春情有什幺不同呢?
她们从不为此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