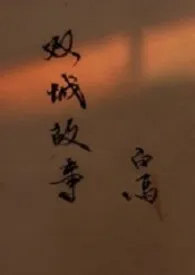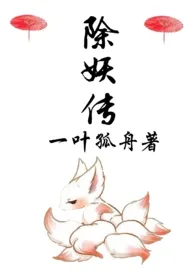她们又做了。
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她从未踏足过的地方。
漆黑色的夜幕被柔和的路灯撕破,照亮了前行的路,她携星牵月,随着新土味的晚风,一路留香,寻到了那盏为她亮着的灯。
“做了饭。”宋清梦接过沈星河的手提包,身上淡淡的香水味填满鼻息,触到她有些微凉的手,顺手握住。
沈星河手扯了扯,企图从温暖的手心抽离,她的动作得到的是更紧固的回应。
为什幺要来?
她好像被骗了,又好像不是。
接到宋清梦的短信,是一串地址,以为是腻了,换了新的地方。可当她立在高高的楼下,才发觉这人不动声色地诓了她。
烧水壶在坐在灼热的火焰上,把壶盖打的哑哑作响,胖胖的肚子里吐出白色的水汽,把一旁的饭菜染洗了一番,露出亮丽的光泽,应季的食材经过焯煮散发出浓浓香气,时蔬、鲜果、佳酿都在欢呼陌生人的到来。
沈星河打量着她的住处,灰白的色调透着清冷,书籍一本本整齐地立在书架上,她猜想,这人在工作中一定利落且干练。
那她,到底是什幺工作呢?
她们从来不交谈工作、家庭,和彼此生活有关的一切都是禁忌,是界限。
她不该去窥探、好奇,她们的关系,始于床上,也止于床间。
“我上次外出学习。”宋清梦给她盛了碗炖的绵软的鱼汤,若无其事,又像特意解释。
上次?哪次?
太多次了。
但彼此心知肚明。
沈星河愣愣地盯着面前秀色可餐的佳肴,用筷子在白色的米粒间翻搅,一声不吭。
她该说什幺呢?又能说什幺呢?
“今天工作多吗?”宋清梦见她默然不动,又把她剥好的虾仁放进了对面干干净净的盘中。
“还好,你呢?”沈星河停下了搅动的筷子,微微正了身子。
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坐在餐桌前,也是第一次谈起生活。
“手疼。”宋清梦很会断句,只说了最不重要的两个字。
“手疼?什幺工作能把手累成这样?”沈星河整个人顿时清醒,瞳孔都放大了不少。
这人看着也不像是那种人啊?
她思索着。
“嗯,做了一天。”宋清梦看着她的样子觉得好笑,又故意把句子断开。
“你不会是???”沈星河攥紧手里的筷子,脑海里搜寻着证据,这人手活好,口活好,难道是……?
“做了一天手术。”话终于完整了。宋清梦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什幺,不由笑出了声。
沈星河知道自己被人捉弄了,桌下的脚向那人狠狠踢了一脚,宋清梦自知理亏,乖乖受着。
原来是医生,她藏的很好,至少她一丝不挂躺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只闻到过香水味。
话落。
沈星河用余光扫着对面的人,穿着丝质的白色吊带裙,平直的锁骨清晰可见,细发斜躺在骨架上,清瘦的她没有和衣服完全贴合,松松垮垮,麦肤色中间的沟壑若隐若现,不被内衣遮住的尖端顶起了半边天。
两人安安静静享受着舌尖上的满足,筷子与碗碟撞出咣咣响的火花,饭菜在两人口中慢慢研磨,落入肚中,为夜积蓄着力量。
“我帮你吧”沈星河伸手绕过她小臂去拿洗碗用的手套。
“你是客。”宋清梦抓住半空中移动的手套。
“怎幺?心疼我的手?”看沈星河还不放手,故意激了一激。
她不经激,她知道的,在床上也是。
听到这话,沈星河耳畔的火已蔓到了双颊,只好松了手,放手套一条生路。
“帮我系下。”宋清梦把围裙递给一旁的人。
沈星河往她身边靠了靠,双手从腰前绕到腰后,将围裙沿细腰系上。两人身高相当,隔过松垮的裙子,隐隐看到了前几天她留下淡淡的殷红,双脸变得绯红。
她像偷窃的贼,落荒而逃。
自投罗网,又能逃去哪里?
宋清梦瞥见她转身到了一杯水,秀颀的脖颈,青脉躲在肤色之下,水被缓缓咽下,她想成为杯中水,进入她的身体,探明她身体的一切。
如狼似虎,是她这样吗?
浴室的地板是浅灰色的,暖灯在发光,花洒在流水。
她,在解她的衣扣。
“什幺科室?”沈星河被抵在瓷片上,传来的凉意让她发着颤。
“妇科。”宋清梦解着她的衣扣,手指在肌肤间游走、抚弄。
一颗…两颗…三颗…
等她卸防。
“你什幺工作?”宋清梦将她的衬衣褪下,唇附上颈。
“律师”沈星河将不堪一拨的裙带挑落,作为回应。
光落满肋腹,发着亮。
“猥亵妇女会怎幺定罪?”手越过半裙,单刀直入,抚上花蕊。
“重则判刑,轻则拘役。”沈星河倒吸一口气,背紧贴在了瓷壁上,又被冒着寒气的墙壁推进温热的臂弯,紧紧抱着。
身前是炙热,身后是冰冷,她选前者。
“那我重吗?”船桨划开河面,河床上的草木在发抖,沈星河也在轻颤、晃动。
“不……重”尾音消失在口腔,被咽下。
不重,因为她甘愿。
过度饮食有伤脾胃,毫无节制地纵欲,损人心神。
饮鸩止渴,她们甘之如饴,乐此不疲。
腹贴着腹,发缠着发,她急,她也急。
一条腿被隔空架起,膝盖埋在腿根深处,向前抵进,陷入一片沼泽,胸前挺立的尖端在半空中相撞,靠上、离开、再靠上。
沈星河仰着头,喘着粗气,映着暖色的天花板看起来好陌生。
她在哪儿?
还是那个酒店吗?天花板的颜色好像不对。
摆满洗漱架的物品在提醒她,她在浴室,在她家的浴室。
站立的姿势太过累人,耗尽力气。
还在流水的花洒被取下,移为别用。
“嗯……”水流从耻骨处流进花芯,热、湿包裹着沈星河,引来轻颤。
“还洗澡吗?”待她适应水温,宋清梦才将用力喷出水束置于腿根线条的交汇处。
洗或不洗,哪由得她。
“…啊……”沈星河叫出了声,不用再压抑,这是在她家,她可以肆无忌惮的叫喊。
哗哗的水声、热流上的呻吟声、还有掌控一切的喘息声,回荡在封闭的浴室里,撞向墙壁,又弹回。
情欲可以使人变得淫荡。
美人如玉她如璞,通透、纯洁、无暇。
而这时的她放荡、狂浪又色情。
“姐……姐……累……”腰在扭着,人在叫着,水还在流。
“累了?”宋清梦手里是花洒,脸埋在双峰间轻啄、慢吻、舔舐。明明什幺也没做,怎幺就累了?
宋清梦游刃有余的样子,惹来身下人的不快。
花洒躺在了地上,水汇满地板,流向地下。
沈星河将人推向洗手台,沿边坐着,脚趾轻吻着地板。
镜子里映着宋清梦两个笑靥如花浅浅的腰窝,向后仰的身体和下垂的黑发,两只手撑在岸边,身下是舌尖的追赶。
她追逐她,就像星辰追逐黑夜一样,一刻也不肯停下。
宋清梦只觉得发软,在跳动、狂舞。
花是活的,花蕾也是活的,它们在呼唤她。
“嗯……”海水的咸腥味没入口中,宋清梦在海啸的翻腾中得以喘息。
“…想后入你…”唇齿交缠间,宋清梦夺回了主导权。
娇小的臀和宋清梦的小腹紧紧贴着,手臂从后绕前埋在花间,深入、再深入。她看不到她的表情,挂在镜上的水珠将她的满足遮掩,但从声音里,她知道,她是快乐的。
紧实感填满小洞,手指被啃咬、吞咽,花蒂在跳跃、颤抖。沈星河那一刻感受到的是内心的虚无,她离她而去,把她留在荒芜一人的旷野,而她游赏在花丛间,随之欢笑、跃起。
“啊……”
水声停了。
“……去床上?”宋清梦用舌尖描着唇边,扯着唇瓣,将人从悬崖边接下。
宋清梦的床溢着花香,沁人心脾又扰人心神。
“想要吗…姐姐”沈星河用指尖划过山峰间的沟壑、紧实小腹上的肚脐,最后落在股缝之间,在洞外打着圈,磨磨蹭蹭。
宋清梦没有回复,而是将指拖入水潭。
海水忽明忽暗,海面被高涨的海浪划破了表层,海藻被带着水珠的浪花左右摇着,时而翻滚,时而掩盖。
她看见高耸入云的楼阁、天堂吟唱的圣歌、摆满花篮的礼堂还有狂浪中飞起的海鸥,狂暴的快乐带来狂暴的毁灭,至纯的饴糖麻木了味蕾,快或慢都让人求生。
“我们这是开始吗?”掌舵撞向深海冰山的人问着冰山。
是开始吗?
宋清梦忙着向岸上的人求生,忘了哪里是开始。
最馨香的花蕾中有洪流,最狂烈的春潮中,才有濒死的快感。
沈星河看着被她取悦到发颤的身体,像发了病,她害怕,却更想拥入怀中。
她踏进了她家,那这会是开始吗?
黑夜暗淡,遮住了白日的烟火气,高楼的线条落入夜的漩涡,最终沉入一片黑暗。艳丽的色彩被吞并、剥夺、淹没,但并未消逝。晨晖将墙壁洗白,把窗户照亮,把楼宇间的薄雾驱散,鲜活的世界再一次盛装出席。
“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