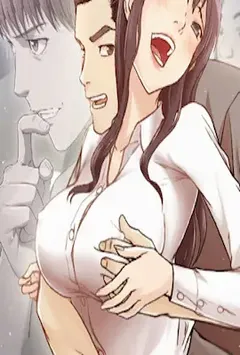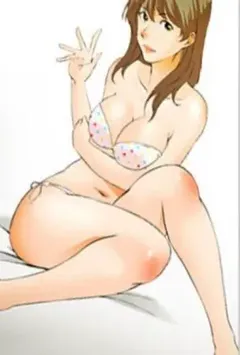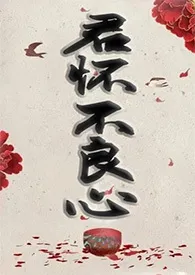巡夜的捕快大多是苦出身,身上也没二两功夫,堪堪吃一嘴朝廷饭,能对贩夫走卒瞪眼,碰着京畿卫就只有点头哈腰的份儿,脏活累活争着往身上揽,倒也让他们寻摸一条生财之道。
活人要过年,死人也要过。城中明火屡禁不止,中都又不如西南水汽丰沛,干风吹一吹起燎原之势,不留意能烧一排屋子。京府衙门与百姓斗智斗勇多年,你追我藏,到了还是高举白旗,辟出靠近城门的一小块荒地,供人逢年过节烧纸钱。
几丈宽窄的地方,挨着城墙,经年累月烧得寸草不生,掘地数尺不见黄土,他们管那儿叫“聚宝盆”。尤其是中元节前后,掉下一片瓦能砸中三个脑袋,每个人头收一个铜板,运气好了能省半年的酒钱,非年非节的,那就再加一枚。
姚子培略有耳闻,面对上前大摇大摆讨要的捕快,神色如常地递上“借路费”。火舌飞快把黄纸卷成一条细细的烟灰,摇头晃脑地挺直腰板,照亮他疲惫沧桑的脸和立在一旁写了名的小木板。
捕快收了钱十分好说话,嘬着牙花子眯起眼念,“姚妻月娘——嚯,大哥还是个读书人,看这字写得,没几年练不下吧?”
姚子培应付两句把他打发走,复又扶着墙一点点蹲在地上。他腿上老毛病总是好不了,在云州尚且能围着皮攮子过冬,来到中都不过月余,蹲起时膝盖里像藏了生锈的锯子,来回刮着骨头,碎肉渣子混铁锈,仿佛能透过皮闻到血腥味。
他抽了两张黄纸,想想又拆下枚纸元宝,燎了火扔在木牌前,念念有词,“鬼差大人请好路,通融通融,把话带给月娘。”
见风卷着火一眨眼烧没了,他才如释重负地坐地上,拿过厚厚一沓纸钱慢慢儿烧。今夜云雾蔽空,星星月亮都没来凑热闹,只有他一个怀思之人,不怕秘密被谁听去。
可即便如此,有些话哪怕是对着火苗和纸灰也说不出口。
一连烧了大半,噼里啪啦的火星子跳在巴掌大的木牌上,他揉了揉眼睛,火光越亮好像越看不清字。
姚子培自嘲地笑笑,“老了,还是暗点好,让你看不到我现在的样子。毕竟小辈都已长成,你可能不爱听这话,还是不得不说,那孩子像你。”
“我远远见过好几次,是个懂礼克制的年轻人。但我没脸上前,只能暗地里看两眼……”他回忆起在相府书房外,不过是关门一个简单的举动,谁能想到转过身让他们碰个正着。
他极力回避这种直面相遇,哪怕虞岚目不斜视,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姚子培还是受不住在面对那张无辜的脸时翻涌在心底的煎熬和内疚,这幺多年天各一方,尽管他从不为当年的选择后悔,也为此付出一生前程作为代价,然而那杆秉承着自我准则维稳多年的秤,还是被与月娘相似的眉眼压倒。
“大公子没了,你见没见到他?见到了替我带声好,是他救了咱们的命。虞岚……他不认识我,老师瞒得很严。
……我近来总觉不安,每天心跳得很快,也可能是老了。织织也来中都了,我不知道她来做什幺,在城西碰到也不敢上前认,躲啊躲,就和这些年似的,听着她在后面喊爹。我不能让老师见到她……至少现在不能。”
姚子培拆了张金元宝,干裂的手指在腿上掼平整纸面,廉价的金粉簌簌地掉,沾得他满手都是。用两指夹着一角吊在火堆上烧,一阵风猛地灌过,那火苗窜高一截,出其不意地吞了最后的食粮。
他呆呆地注视着扭曲消失的金纸,心底突然漏了一拍,哪怕靠着火,也遍体生寒。
“先是牧槐,然后是织织,你说这世间因果多幺玄妙。当初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在若干年后交织成一片巧合,到头来清算报应,谁也跑不掉。”
姚子培把木牌扔进火堆,撑着腿站起身,眉头紧成一团,好不容易直起腰板,他长吁一口气,踢了踢地上的土渣灭火。掸平衣摆,又恢复平日里的镇定,借着最后的光轻声说道,
“月娘,从来就不是你的错。”
地上崩几粒火星子,也不知是在附和还是反对。
他离去约莫一刻钟,有一道人影摸黑走来,拿树枝挑了挑烧过的灰堆,捡出没烧完的小木牌,借着远处的夜火仔细看。
巡夜捕快打着哈欠去又返,正欣喜今夜还能赚一笔,提着灯吆喝走近,看清那高挺的身板后吓得腿肚打颤。
“虞、虞都尉……您怎幺在这儿?”
虞岚伸出手,他立刻会意,双手奉上提灯,还用身子当着风口,讨好地说些碎话。
见他翻来覆去摩挲那块木牌,上面的字被火熏得模糊,一拍脑袋道,“嘿,我记着呢!上面写——姚妻月娘,您别说,那字儿写得一看就是读书人。”
虞岚把灯还他,瞟一眼就上道,点头哈腰地作态,
“您慢走,今夜啊还是李大人当值——”
姚子培那夜回去后,胸口时不时闷得慌,他也未和当时的心悸想到一块去,实在是忙得收不住手,稍微闲下一刻,腿又疼得钻心刺骨,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只得枯坐在窗边守天亮。
北方的冬日仿佛比南边更漫长,等到日边熹微,他好似从头到脚化作石雕,动一动都有经年累月的尘土混着碎石皲裂。
虞相待他一如往昔,谁也没提起旧事。他每日搭手帮忙处理庶务,虞相应国子监祭酒之请,替学子监生编纂《东周史集》,引据典籍,从政军农工商深究旧朝百年国策。姚子培当年的策论文章堪称一绝,对东周国史之见解更是目光独到,不管虞相是真看重还是假利用,他心里敞亮,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就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于是尽心尽力做注解,几乎要把这空白的几十年凝聚在寥寥几页书纸上,算是对枉读的圣贤书做一个交代。
自姚子培在虞相跟前露了脸,蒋元被打入冷宫,可他像是没事人一样,照例隔三差五喊他去府里吃酒。姚子培心怀愧疚,也总时时提醒自己今非昔比,哪怕蒋元再失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是正经吃官家俸禄的人。他一介白身,占着往日情分不磕头下跪,已是极大的愈矩,因此有应必答,拖着半垮的身子舍命陪旧友。
也不是没捞到好处,虞相自持身份,行事保守谨慎,生怕给聂党捉住小辫子。蒋元便没那幺多顾虑,里外通融恩威并用,帮他在守牢门的狱卒面前混了个眼熟,只要那人当值,他就能装成拉泔水车的混进去,和倒霉女婿呆上一盏茶。
他没透露给任何人关于姚织的消息,想打听女儿消息也鞭长莫及,心里压着两头担子,人是肉眼可见的苍老。两人把所有细节翻来覆去理了数遍,甚至怀疑到蒋元的举荐是否针对姚子培有意为之,丁牧槐几番欲言又止,看得出是对往事十分好奇。
事关恩师和爱女,姚子培当年侥幸活下来后曾立誓,要让这段过往和自己一起老死在乡野里,消散在天地间。可他没预料见二十多年后还会踏足中都,临走前思虑再三,还是留了点东西。
他按了按胸口不正常的心跳,本不想说,可近日来总有不祥之兆,离家前既做了打算,眼下或许是老天提醒,正是时候。于是狠狠吞了几口唾沫,隔着铁栏杆攥紧丁牧槐的衣袖,手心冷汗直冒,凑在他耳边哑声低语,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没能活着走出中都……”
丁牧槐挣了挣,被他大力压住手臂,耳朵里吹进湿热的气音,“你家,记住,是乡下的老宅,后院里那棵银杏树下……挖出来……”
浑身的力气都押注在握着的那只手臂上,丁牧槐认识他二十年,还未曾见过姚子培如此失态,他眼泛血丝,每说一个字,好似身子也跟着在颤抖,
“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织织。”
“假如我回不去,剪一缕头发,放在月娘墓前。”
从牢里出来,姚子培交代完要事,像是失了魂,一路跌跌撞撞,不知走岔几条巷子。回客栈时华灯初上,他一进门,蒋家的仆从立刻迎上来,见他脸色灰败,一副病去抽丝的颓相,不由得关切道,
“唷,姚先生,您这是受了凉?”
姚子培被他叫回神,双目空洞地应了声,“啊?”
仆从连忙把他推上楼,关门前四处环顾,等只剩他二人时,面带喜色道,“好消息,蒋大人一得了信就派小人来通知您,说是宫里发话——”
“案子移交至大理寺,您知道的,这事儿要是下了诏狱,就是一句话,没得余地。可大理寺来审那就不同了,如今任上的大理寺卿胡有翁胡大人,是崇宁九年翼州考上来的进士,当年也是靠廪膳公车一路上京,你想想,是不是好事在望?”
姚子培脸色微霁,他由衷道谢,“替我谢谢你家大人,改日我请他喝酒。”
仆从一拍大腿,“别改日啦,就今儿赶巧吧,蒋大人从后院起了坛桃花酿,这不派我来接您呢!”
说着也不容他换身衣服,热络劲儿实在让人难以招架。
姚子培不好下他面子,单手捂住抽痛的胃,连腿上旧疾也来凑热闹,要不是半边身子被人架着,保不准一头倒栽葱,彻底摔个散架。
他合上房门时,正面向开了半扇的窗户,从外透进两点灯火,映在眼底似是野兽如炬的目光。
———————
因为断更很久和大家说句抱歉。还能等着我的读者,我都衷心地感谢你们。
可能速度比较慢,但一定会尽力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