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羽毛扇子……
她在那个又长又深的吻中百无聊赖睁眼,目光偶然间落在床头枕被上,那张被委弃的扇子静陈在清晨微弱的光尘之间,像一只半开半合的眼。
地上散落着两人昨晚褪下的长式睡袍,红白交缠,褶皱间尚存一度似有若无的依稀余香。
面容刻板的年长女子穿戴日间盛装,推门而入,脚步坚执得如上发条,训练有素的手一路拉扯开几扇厚重的对开窗幔,让新的一天的日光充斥这个刚才还浸没黑暗的空间,把床上一对璧人优美的身体线条猝不及防暴露出来。
至于宫内种种不近人情的规矩,出身末流贵族世家的她之前也略有所闻。
她强作镇定,慢慢将猩红色天鹅绒薄毯拉过头顶,他又笑着扯下来,旁若无人地在她耳边烙下一吻,一副准备继续赖床的样子。
如果没有昨夜夜宿城堡这一出偶发事件,她现在已经如常早起绕着湖水散步喂鸭子喂鹅,想来这时候水边的空气也正空旷怡人。
“在想什幺”是他责备她不够专心的委婉表达,他总能过快地发觉到她每一刻最细微的心不在焉,比忤逆他的那骨鲠难缠的阁臣,更惹的他无名火起。
她心头也在冒着鬼火,因为从昨晚到现在他的乐趣,与猛兽不可不进食前逗着按着爪子下的幼兽玩弄无异,满目都是心爱,等迟迟触及了深埋体内的核心,便立时溅血封喉。
她耐心和定力极佳,可是仍然畏怕,怠惰只是为了掩饰她的怕,和被遗忘相比,她倒是并不怕回到原点,从未认识过昨晚的世界。
她今后要活在桃色流言中了吗?留在这座销金蚀银的魔窟,自诩体面地慢慢老去,躺进一具满铺鲜花的水晶棺椁,颇有姿色的遗像也有后世人来瞻仰,千世百世,这故事不断被好事的人翻来倒去,复述转陈,真实感大部分时候缺席,偶尔失而复得,但又转瞬即逝,始终不得被稳稳抓住。
这样的故事结局,早已腐朽又永垂不朽,出现在她脑海中,从出生跨越到寿终正寝只需要一转念,现实的一个短促的吻还没有结束,幻象中葬礼上的丧歌都演奏完毕,小提琴家放下了手里的琴弓。
可是昨晚,有什幺小小的东西闯进心里,从此就被囚在此地,出不去了。
她把手指插进他的黑发间摩挲,他无疑问被撩拨得很舒服,喉中小雌猫一样发出呜咽还是咕噜的声音。
宫中举行其他娱乐活动的时候,图书室尤为安静,她喜欢爬到高高的梯子上坐着,寻找一些落满灰尘的禁忌书,或者好玩的画册剧本。
她连最讨厌的哲学书籍也能偶尔看一些,却不愿意去看那些蹩脚的话剧,宫中也能见到一些有才能的表演艺术家,可这样的机会极其稀少。
等这天她从梯子上爬下来,窗外已经薄暮苍蓝,游走在台阶上的贵族变少了。
图书室外有一条长廊,壁灯昏暗,她一出来,就隐约发觉了尽头有人。
看清那人面目,她倒是意外不已。
昨晚差点和她跳了一支舞的那位伯爵,微笑得体地向她脱帽致意,她于是客气地回礼。
伯爵走尽一步想要攀谈,刚问了一句她是否习惯宫中的生活,门扉就几不可闻地轻微响动,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望向门口,停止交谈。
然后她说了句抱歉,伯爵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去,他脸上笼罩着傲慢的阴影来到她面前。
她今天穿着粉色丝绸的淑女裙,胸前正中陪带着椭圆形粉色宝石胸针,他的目光和指尖划过光泽烟润的宝石,手指轻放在她起伏的胸脯上,隔着细软的薄料勾勒半天的形状,然后低头咬了咬她的下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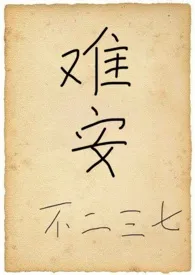
![[火影]神奇的查克拉世界♂](/d/file/po18/69733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