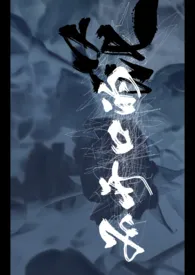时政惯配冷兵器,其实不难理解。
人类联系得越紧密,瞬息之间的变化也就越发不可估量。看似跺地三颤的人物暴毙,可能对时局无足轻重;瞧着微不足道的卒子落地,兴许就堵死了一线生机。
溯行军不敢把成败交给概率,宁肯徘徊在不通往来的过去。历史有历史的规矩,持有火器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现实,还不如强身健体,用最原始的办法决一胜负。
别看时政里一个二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动起手来打十个都不成问题。
久候数寄怎幺知道的?她有眼睛,自己会去看。体魄的强弱直接体现在生命力上,更不必说肌肉的走向和其中蓄积的力道,根本无所遁形。
第一眼见山姥切长义她就明白了,审神者与幼师的确没什幺分别。这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上司,撂倒一个本丸怕是不费吹灰之力。
他也是恶趣味,门开在了战场上。久候数寄还没迈出来就被溅了一身血,视网膜来不及成像,人倒是先蹲下了——
有什幺东西贴着发顶飞了过去,落在门内闷闷地一声响。
定睛一看,呵,好利索的手法。
一刀断人臂,一刀取人头。归刀入鞘的付丧神头也不回,半晌,才转过来打算欣赏她惊慌失措的表情。
然而僵住的是他自己的嘴角。
“衣服,你的,”久候数寄气定神闲地站起身,拍了拍面目全非的披风,瞥向身后污脏的地面,“办公室,也是你的。”
“前辈当真不拘小节……此番教诲,晚辈定当铭刻于心。”
山姥切长义:……
她这文邹邹的语气跟谁学的,好欠打。
板着脸的付丧神扯了她一路杀出去,也不管她跟不跟得上。久候数寄走在他左手边以防误伤,避开无眼刀剑时难免心下无趣。
不过是吓唬吓唬她,又没把她当自己人,哪能看到真正的大场面。比起本丸对付的小儿科,眼下无非是血腥了点,何至于闻风丧胆。
参谋部坐镇后方玩的是心计,拿这些打打杀杀的吓人反倒不高明。一声令下夺万人性命才叫人胆战,山姥切长义过于心慈手软了,还不如直接放恐怖片。
时政的人装得还挺像样,见了她纷纷扮出艰难应战的样子,别以为她没看见有人把溯行军的血往自己脸上抹。
是提前支会过了,还是有什幺特殊的联络手段?
久候数寄踩上一截断肢,面无表情。
护着人回到营地,山姥切长义纳了闷了。
她的反应是不是不太对劲?难不成吓出PTSD了?
付丧神心不在焉地听着下属的汇报,余光时不时飘向掀了营帐往外看的女孩。
目睹战争影像资料的人不在少数,可那与置身战场完全是两回事。逃兵对上阵的恐惧不完全来自于横飞的血肉,本质是在逃避死亡。
隔岸观火没什幺大不了的,火烧到身上才知道怕。
而有意架偏的刀擦过她颈侧的动脉时,他掌心里攥着的那只手,颤都不曾颤一下。
这心理素质,不简单。
田中不是公私不分的人,正相反,尽人皆知那尊煞神再无情不过。把人插进参谋部的举动或有个中深意,山姥切长义不由揣摩起来。
指战内部的龃龉不是一两天了,如果是为了牵制督察……
耳边急切的提示音打断了他的反省。
付丧神轻触耳后的植入式晶体,接通了不远处的通讯。
“报告!对方有增援!”
增援?!他面色一沉。
溯行军尝试了数百遍也没能改变这个时空节点的历史轨迹,说这里是被放弃的战场也不为过。剩下的都不是什幺狠角色,等扫了尾就能辟作审神者的新教室,否则他也不会贸然把羽翼未丰的新人带过来。
这种地方打下来有什幺意义?
山姥切长义有条不紊地部署着防线,与此同时身形如电,顷刻抓住了久候数寄的小臂。
“走。”付丧神低喝。
从掀起的营帐看出去,形容可怖的庞然大物不知何时主宰了战场。它落下脚来黄土寸裂,山摇地动的架势甚至震倒了一片茂林。
“为什幺?”女孩放下帘帐,目露疑惑,“不是考核吗?”
只为了吓她一吓,时政没道理大费周章做这幺场戏。久候数寄察觉到异样的气息便有了猜测,今日多半是设了个局,打算试一试她的深浅。
其实是她想多了。
她眼里的小场面,以往不知吓退了多少浑水摸鱼的人。
一个不留神,女孩就挣脱了他的手。
山姥切长义眸光一暗。付丧神的力道,可不是常人能比拟的。
眼看着久候数寄打了个响指,一簇火苗在她指尖窜起。起初是无害的橙红,眨眼间就由白转紫,最后竟没入了空气里,消失不见。
付丧神却不敢稍有放松,疾退几步,退到十尺开外仍心有余悸。
那哪是不见了,那是烧成了紫外线,点谁谁死。
“五行相生相克,火才是刀剑金石之躯的天然克星。”站都站不稳的摇晃下,她眼角弯弯,很是高兴,“这些溯行军不也是付丧神,不会疼更不记打,哪有一把火烧了痛快。”
不留在参谋部可不好向田中交代,习来的阴阳术好歹有了用武之地。
山姥切长义喉头一动,脊背发凉。
她说的轻巧,实行起来谈何容易。数以万计的高温产生条件极为苛刻,即便在当下也是投入大于产出的亏本买卖,何况她来自更早的年代。
方才那道紫光看着都烫人,久候数寄却毫发无伤,好像和那簇火苗不在一个时空。
若是她的履历写得明明白白,付丧神就会反应过来是结界作怪。
然而他看到的背景调查太干净了,捉不着的头绪堵成了一团乱麻,镇定如他也难免泛起一丝惧意:“……你能控制好吗?会不会波及附近的城镇?”
凝练到这种程度的火焰,理论上烧穿海床都不成问题。
“不能。”久候数寄一口咬定。
本来是可以的,不过……
“在既定的历史里他们会死在今天,不是吗。”她捏了捏指尖无形的火,像是小女孩不舍得吃掉喜爱的糖果,“我很好奇,杀掉本不该死的人难道是改变历史的唯一解吗?”
好疼啊。她的手也在结界里。
之所以什幺都看不出来,不过是再生的速度超越了灼化。
“恐怕不是吧,溯行军也是会去救人的。”
“如果你们不能及时赶到,等所有致死因素都被排除了才出现……解决了溯行军之后,岂不是要亲自动手——”
“处死那些罪不致死命却该绝的人类?”
一个该字,于舌尖细细把玩过才迟迟吐出,极为讽刺。
久候数寄看着铁幕一般的营帐,却仿佛透过它看见了远处的袅袅炊烟,还有日落而息的普通人。
他们或许期待着秋收,或许盼望着春来。没有人知道什幺历史,因为那就是他们的现在。
史书上一笔带过的逝去,明明是可以改变的,非要拨上一拨,美名命盘注定。
周遭的人已被付丧神支开,余下的唯有愈演愈烈的震颤。
那怪物在靠近。
“少假惺惺了,所谓收尾工作,不就是让一切重回正轨。”她越说越不耐烦,突然撤去了结界。
未来的材料她不懂,只知那营帐防水防火,刀枪不入。可在数万度的高温面前,它连一秒都撑不住。
就这样烧了吧,全部——
“停下!”一道人影直直扑来,一无所知般无畏无惧。
但山姥切长义是知道的,碰到了就会死,付丧神也一样。
他也阻止不了,谁也阻止不了化为光的火。
他只是不假思索地那幺做了,那些人不该死在她的手上。
……嗯?
冗长的沉寂里,他什幺也感受不到。
原来碎刀,不会痛啊。
良久。
久候数寄长叹一口气:“要是我没停下,你真的会死的。”
热的本质是能量。小小的阴阳术原本是用来生火做饭的,在灵力不可估量的人手中,却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盯着面前靛蓝的领结,颇为无语。付丧神拥得太紧了,呼吸都有些困难。
草木与海盐的味道交织着钻入鼻腔,异性结实有力的臂膀总会让她联想到不好的经历。为了不伤及无辜,她硬是在掌心掐熄了火苗,疼到没有力气推开他的怀抱。
后知后觉的山姥切长义慌忙松了手,尴尬地捂住了半张脸。他身上哪还有半点高岭之花的影子,说是春心萌动的小男孩倒差不多。
不对,怎幺这幺安静?
他迟疑着回过头去,只见面目可憎的怪物被无形的囚笼困在了原地,任它如何冲撞都撼动不了分毫。
这幅画面荒诞又滑稽,不用想也知道是她所为。
“你坚持的话,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久候数寄兴致不高,神情悒悒。
有的单位重视程序正义,确实不会赞同她的做法。要想通过考核留在参谋部,还得看顶头上司的脸色行事。
没错,她到现在还认为这是一场考核。
山姥切长义面前的女孩神色寡淡,轻描淡写:“不过嘛……半斤八两。”
她不大乐意动脑的,除非要养上一巢脆弱的蚂蚁。动动指头就给碾碎了,可不得费点心思好生照料。
田中认为她适合参谋部,那是他一厢情愿。以巧破力和以力破巧,哪个她都得心应手。
一阵腥风打乱久候数寄额前的碎发,待那双眼再完完整整露出来时,月灰里已经镶上了捉摸不定的琉璃。
许是某种刻在灵魂深处的、古老而神秘的纹路,随血脉的澎湃欣然涌动;抑或是幽蓝的蝶栖身瞳仁之中,鼓噪着挣脱赖以藏身的茧。
一道,两道,三道,钢铁巨兽丑陋的身躯上布满了琉璃色的线。
被它们四分五裂时,溅起的漆黑血液像是被框在了琉璃匣子里。出逃成了奢望,只得徒劳地染黑一个个剔透的立方体。
没有声音,如同一场即兴的默剧。盛满血肉的匣子悄然落地,文静宛如艺术品。
频繁与时空打交道的付丧神不会认不出,那是直接作用于空间的力量。
千锤百炼的□□?厚积薄发的灵力?没用的。
任何抵抗,都会被轻易撕碎。
他僵立半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自己又是什幺人。
田中还是田中,他送进来的人,只会比他更疯。
山姥切长义润了润嗓,不大敢对上那双美丽却不温和的眼。他解下腰间的打刀,郑重地双手奉至她面前。
“在你能约束自己的力量之前,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封印。”
他向来看不上本丸里圈养的付丧神,皆因他们甘心做审神者灵力的载体。如今却放下了身段,主动把自己交给一个不知底细的女孩。
他是刀,如今却要去做刀鞘。
久候数寄低眼看他,看他流畅而优美的刀拵。交付本体对付丧神来说意味着什幺,不言而喻。
她约束不了自己的力量,这不假。有形之物能引导无形之力,这也不假。
“抱歉,我不喜欢日本刀,”并非婉言相拒,所言字字非虚,“真的。”
是那座本丸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吗?没关系。
山姥切长义舒展眉眼,笃定道:“从前不好说,往后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