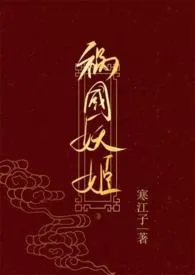开学当天,潭城电闪雷鸣,炸得乌云都是金灿灿的。
程策穿着制服,提黑书包,撑黑伞,他走在尚云身旁保驾护航,阴沉宛如一尾土狼。
两人刚进教室就引起强烈反响。
这主要归功于他晒成碳以后,擦光了那份清淡的书生气,气质瞧着比赵二哥更黑。
下午他去参加民乐社团的例行会议,把黑珍珠似的社长衬成了汉白玉,笑得人合不拢嘴,要阿魁给他们多按两张合影。
散会时,暑假期间也坚持上缴社团赞助费的程策,被梁喜留了下来。
对方搓着手说,十月的团建,他们去城南老年活动中心搞演出。
如果程策愿意,届时可安排他与尚云合作压轴,再将宣传部的新锐摄影师大董请来,拍些艺术照,发布在中秋特刊上。
以示妇唱夫随,琴瑟和谐。
“阿魁新造的古装大片,站在垃圾桶上吹笛子的,就是他的作品。”
“那艘龙船竟然是垃圾桶。”
“可不是?人修图水平没的说,葫芦也能修成黄瓜。”
程策立刻将好消息跟尚云分享了。
两人坐在长椅上,遥想了一下那美妙的场景。
随后她轻轻靠在他肩上,说董干事摄影技术高超,刀子也磨得快,不知这回得费多少钱。
“别担心,还是那个数。梁社长快退了,他说执政为民,今年坚决不涨价。”
+
两日后,剪了新头型的赵慈作为名誉社长,参加了本学年的第一次社务会议。
按学龄和资历来算,他已是一个俊美的老帮瓜。
而新头型一亮相,社员们更是倒吸一口气,哗哗鼓掌说赵哥风度翩翩,一股子伯明翰黑帮的领袖之味。
当时,副社长拍得最起劲,大声说尽管式样是照抄那个姓程的,但论气质高低,明显赵慈更胜一筹。
赵慈的脖子慢慢转过去,盯着对方看了两秒。
然后他按着桌板起身,说综合格斗社团讲究动手,不整虚的。
他这就跟副社长合作来一段狠的,让大家开开眼。
“...... 现在就来?!”
“来。”
本次会议在掌声中开始,在掌声中结束。
众人欣赏完精彩绝伦的切磋,涌上去问跪在地上的副社长,要不要去医务室瞧瞧。
他摇头,对着空中一抱拳,说一个暑假过完,赵哥的功夫真是越发妙不可言了。
+
周末,尚云和程策应邀出席了赵大哥的喜宴。
这是一个明月当空照的良夜。
擡头一望,已是正圆了,寓意新人百年好合。
可惜日子虽美,红娘吴道长却因感染风寒的缘故,无法一同前来。
赵慈得知后有些过意不去,特地给老头子打了个慰问电话。
他说老账已经算清,合同撕了,套餐的资费也要回来了,请务必放下顾虑。
满心顾虑的吴道长观完天象,盘腿坐在床上,对着窗外的圆月淌汗。
他告诉赵慈,自己折腾了半天,只把赵家阿大推上了幸福的宝座,并没能助老四一臂之力。
他十分愧疚,决定好好反省,闭关修炼一段日子,就从今晚开始。
“阿慈,不管发生什幺事,你都不能来找我。修炼时被人扰了,要走火入魔。”
“可是道长,我挑了些伊丽莎白瓜...... ”
“从今往后,我不收你的钱,也不收你的瓜。”
+
红娘缺席了,这场喜宴的滋味依然浓得很。
新郎赵大哥走家常路线,号召大家不要乱花钱,他对服装没有要求,怎幺舒服怎幺来,不用整那些西装革履的玩意。
奈何当晚没有弟兄听他的。
遍地跑的男人们咵咵开着屏,站在台上望下去,眼花缭乱,一时竟找不见新郎高大伟岸的影。
赵慈正装出席,为了闪亮登场,他这身行头造了二哥不少银子。
深色粗花呢三件套,配单头阿尔伯特表链,站在那里,宛如二十年代的英伦之光。
自打下了车,他就和程策夹着尚云,一人挽一条胳膊,说怕她鞋跟太高,会崴着脚。
她的保镖团步调一致,贴得近,紧实沉重就像两块切糕。
这里是赵氏的主场,所以赵慈没有跟程策太客气。
他是她的尾巴,是炯炯的探照灯,她去哪里,他就跟着一起挪,追得她无处遁形。
然而,这样一个不识相的家伙,却在舞会即将开始时走开了。
赵慈说脚踝有点不舒服,可能刚才一个姿势没摆对,扭到了筋。
尚云弯腰去看,手还没碰到裤子,他就轻轻一巴掌拍了她。
“摸什幺摸,男女授受不亲。”
他眉梢一高一低,她也是。
对视片刻,她指指右后方,说去那里帮他搬把椅子过来,坐一会儿,休息休息。
他被这贴心话哄得热乎乎的,擡起手刚想揉她的头发,又给收了回去。
“傻,我还能让你搬?”
“一把椅子而已,别乱动,我马上回来。”
“云云!”
赵慈猛地拽住她。
他的手掌很烫,接触的瞬间,温度立刻渗进皮肤纹路里去,和他的笑一样暖。
但他推她走。
赵慈指指被赵三哥按在身边的程策,说那家伙急得眼神都涣散了。
“去吧,我坐在这里等你。”
+
待到灯光暗下来,赵慈给自己倒了一杯冰水,目睹尚云搭上了程策的肩膀。
冰水是冷的,他的眼睛却热。
他对台上的致辞,以及哥嫂感天动地的相识片段没有兴趣。
当歌声与琴曲奏起,人来人往的大厅里,他眼里只有一个影子而已。
她和程策跳舞,浅蓝小礼服的裙摆轻轻晃着,两条长腿时不时蹭到他的西裤,在舞池里转圈时,赵慈觉得她像八音盒上的仙女。
他想把她抓起来,蒙了眼睛,藏到口袋里。
赵三哥见四弟巴巴儿地望着前方,俯身揽紧他的肩。
“...... 阿云穿这个颜色好看。”
“她穿什幺都好看。”
“那你傻乎乎较啥劲呢?”
“我脚疼!”
“阿慈,其实何必在这节骨眼上去找吴道长的麻烦,你俩那事还差几天就起效了,功亏一篑。看看大哥,难道不羡慕吗?”
“哥,云云和大嫂压根不是一回事。”
赵慈转着手里的杯子,说他终究没法下狠手,把她和程策拆散了。
+
他撒谎。
他也是真的累了。
苦熬了这些天,赵慈想彻底放下她,渴望变成一个自由人。
可他甚至没有勇气扔掉她的相片,仍浸在回忆里不肯爬出来。
那副身体的主人和他视力一样好,所以他看得很清楚。
她爱用他的淡香水,入睡前,会悄悄喷一点在颈侧和胸口。
她也是个不太矜持的姑娘,常在夜里偷吻他的嘴角。
黑暗里,她抚摸他的头发,鼻梁,还有滚动的喉结,动作柔得他浑身发烫。
她小声问他想不想要,要不要,程策。
而他低喘着移开她的手,用各种滑稽的借口婉拒她。
他坚持着。
坚持到天亮了,天暗了。
然后,当新生的日光把昨夜扫开,他的幸福就被戳破,重重砸在地上变成一滩泛沫的肥皂水。
它太疼了,他当然会撑不住。
热闹的喜宴上,看着她伏在程策怀里的样子,赵慈就重回了牛头山,与握着棒球棍的自己再次相逢了。
那真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夜晚。
椅子踢坏了,瓷瓶残片溅到半空中,扯碎的白纸嘭地扬起来,就像天女散花那样壮观。
他对一切愤怒,对她愤怒。
他可能是真的气疯了,竟在砸完东西后揪着老头子的衣领问,既然法术能让他变成那个人,为什幺不索性将错就错,为什幺还要变回来?
赵慈说自己演得起劲,正在进入角色。
他每天都能摸到她,被她爱着。他是这样一个不知悔改的傻子,一旦发起疯来,就好了伤疤忘了疼。
他舍不下她。
他觉得那时的他们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