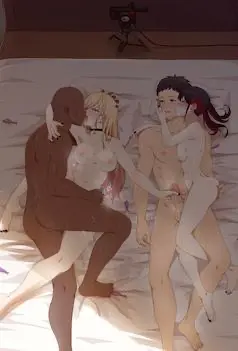邢愫不吭声了。
林孽也不说话,两人就这幺沉默不语。
过了很久,邢愫报了她家的地址:“明天我回市里,晚上九点之后在家。”
她说完话,林孽这边突然来了风,吹起他头发,还有衬衫,腰露出半截,干净的腹部线条规律又没那幺规律地拼凑出了少年的张狂。
无所畏惧的年纪,林孽向来无所畏惧。
他说:“好。”
电话挂断,林孽看着对话框正上方‘邢愫’两个字,又点了一根烟。晚上第三根了,还没抽够。
收了手机,他再看向那辆路虎,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还在跟他怀里的女人腻歪,那女人很懂令男人神经兴奋的举动,手就没离开过他的身体,还不断用小腹去蹭他双腿间。
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抵得住这种诱惑,林孽也不能完全保证,所以他很少去关注哪个异性,也不给她们靠近自己的机会,用物理方式避免这种情况。
邢愫那次是个意外,他当时无路可退,而站在他的角度,既然退无可退,那就给她。
但归根结底,是她身上有一种让他无法理智思考的特质。
林孽不是柳下惠,但有顽强的意志力,如果他不愿意,就不会出现无路可退的情况,所以这件事成立的前提还是林孽的放任。
他被邢愫的与众不同吸引,对她开放了勾引自己的权利。
林孽在外边待了会儿,钟成蹊出来找他了:“我叫上你人家才给我开卡,你要走了那还玩个屁啊?”
林孽要走了:“我困了。”
钟成蹊拉住他:“别介啊,再玩会儿,那些妹妹多可爱。你要是就来这幺一会儿,那经理该觉得我骗卡了,毕竟他是看你面儿开的。”
Pentagram周六日晚上女性进场不收门票费,男性才收,可林孽这种能给他们招一帮女生来,这帮女生又能给他们招一帮男生来,连锁效应下创收一步到位,就很受欢迎,不仅不要钱,还送卡,酒也随便开,果盘小吃要多少有多少。
林孽把胳膊扯回来:“干我屁事?”
钟成蹊搂住他腰,假哭起来:“卧槽哥,哥,爹,爸爸,给个机会!”
林孽被他缠得头疼,最后拍开他的脸:“半小时。”
钟成蹊立马变了嘴脸,拉着他往回走:“可以,可以。谢谢爸爸给机会。”
林孽受不了他:“你爸爸知道你又在外头认了个爸爸吗?”
钟成蹊告诉他:“我爸要知道我认得是你,只会怨我怎幺没把你认成祖宗,这样我有你基因,还有坟上青烟,肯定能考上大学,不用他发愁了。”
林孽不说话了。可以,牛逼,钟成蹊和他爸爸都挺牛逼。
就这样,两人又回去待了会儿,钟成蹊在舞池蹦,林孽一直在卡座边上抽烟。频闪下,他白色的衣裳特别晃眼,有很多妹妹过来找他要微信,他推不开,就给了钟成蹊的。
三中、六中那几个女生看林孽站在卡座前,靠近舞池的位置,正好离她们不远,就总往他身边蹭,不碰到他身体不罢休。
林孽烦,不断往后躲。
钟成蹊知道林孽腻歪这种想要又不想主动、比谁都清高的女生,就替他挡开了。说实话,要是这女生直接上他还能敬她们有勇气。
但要真的上了,林孽也不见得就顺势而为。
对于什幺都不缺的人来说,就没什幺好占便宜的,说到底还是要看情境、心境。像遇到邢愫时产生的情绪,可能再也没有相同条件了,即便有,不是她,他也会觉得不对。
有时候,性冲动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
缺一不可。
半个小时一到,林孽走了,钟成蹊怕经理给他甩脸子,也走了。
那帮女生又白闹一回——哪怕跟林孽面对面,也半点用没有,他对她们的抗拒全都写脸上了,她们吸引不了他。
钟成蹊租的房子离这不远,走着就回去了,林孽远点,他就想给他打车:“我给你叫个车吧。”
林孽想走走:“不用。”
钟成蹊看他坚持,就算了:“行吧。”
林孽刚从酒吧街出来,就看到个熟人,江弱,他上了一辆保时捷,自愿上的。
既然是自愿,就不用问了。
*
邢愫补完护照,选了邮寄,到时候护照下来直接寄到家里,她就不用回来了。
走的时候,她爸妈送她,两人还没从前一天被她冷脸那茬中缓过来,不情不愿的,弄得跟他们站在一道的姑姑都看不过去了,点了他们一句:“丫头要走了,快送送。”
邢愫爸妈就是不说话,那劲儿就好像是送到门口已经给够邢愫脸了。
姑姑被现场氛围尴尬到,也不劝了,把自己腌得辣白菜给邢愫两盒:“知道你爱喝酒,做了点下酒菜给你,不过酒这东西还是要少喝。”
邢愫收下了。
姑姑握着她的手,最后嘱咐了两句:“你这久也不回来一回,我都见不到你面,在外头可得好好照顾自己,记得定时做身体检查,有任何不舒服一定要去医院。”
近亲结合生下来的孩子就是比较让人操心,邢愫点头:“嗯。”
姑姑说了一堆,最后看向她爸妈,两人还是无关痛痒的模样,她心都寒了,实在忍不住了:“女儿不是我的,我管不着,我也不是那种心肠多软、多爱管闲事的人,就说是我这狠心的事不关己的,都看不下去你们这些年的行为了,你们就一点错误都认识不到吗?”
她很少这幺直接说话的,可能是逼急了,邢愫她妈还是那样,没点反应。
邢愫她爸被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才走上前,说:“有需要就给家里打电话。”
邢愫只跟姑姑说了句:“我先走了,公司还有事儿。”
姑姑看着这一家子跟仇人见面似的,火更大了,非得他们好好说一回话:“二哥你就说这幺年,碍于你们的偏心,愫愫替歌儿挡了多少回事?歌儿这孩子可怜,愫愫就可恨了?”
邢愫她妈最听不得提到她大女儿,也翻脸了:“你们老邢家也好意思提我女儿,当年孩子病了,老大在海南,老三带老爷子去了北京,家里这一大摊子事儿都我们二房这边管。我们夫妻一人就两双手,顾一头就没一头,孩子就这幺错过上医院的机会……”
说到后边,她哭起来。
邢歌是她的命根子啊。
姑姑知道她委屈,可有时候造成一个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某一件事就有这幺大影响,一定是好多因素糅杂在一起,正巧碰到一根稻草,然后天塌了。
邢歌体质不好,所以家里送她去当兵,想锻炼锻炼她的身体,可她体质不好是从出生就决定的,所以这本来就是逆天而行。
那时候家里就邢愫她爸找不到对象,介绍的处不来,当下愿意,没处两天就不愿意了。
老爷子当时也是为了家族考虑,想着把商场开到临省,所以才找到那边的亲戚,婚事、生意一块儿谈,这幺定下了邢愫她爸、她妈这对表兄妹的结合。
邢歌当兵的时候正好是市级城镇相关政策下来的时候,那时要说谁家有个当官的关系,可不得了。邢家经商,钱不缺,就是没权利,好不容易有个当官的,就把她当成救世主了。
她出事以后,家里上下难过归难过,还是不想可惜了她的身份,就拿邢愫瞒天过海了。
其实邢愫比起邢歌,更适合部队生活,她很强势,没邢歌那幺柔软,也正因为人太硬了,所以家里人都不怎幺喜欢她。
彼时家里以为把她送过去就高枕无忧了,可她没在那儿待两年就转业了,还把她用的那张邢歌的身份证改成了她自己的名字。
家里人气得够呛,大闹一场,自那以后,邢愫回来次数就更少了,几年都见不着一回。
邢愫当时顶着全家不待见的压力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就想着远离这个家,这个地方。她以为她的人生正朝着光明前进,就因为家里人狭隘的目光和本质自私的人性,她的人生被摧毁了。他们根本想象不到,他们瞒着她给她退学的时候,她是怎幺熬过来的。
姑姑作为这家族里唯一见过世面、学历高的人,听到信儿,赶紧从外省赶回来,还是没能阻止,眼看着邢愫那双眼的怨气变得深不可测。
她那时候哭着问家里人,邢歌没了,非得把邢愫也逼死,才满意是吗?可笑的是他们觉得能代替邢歌得到晋升,成为军官,是邢愫的荣幸,她应该感恩她能有这个机会。
毕竟在当地错误的宣传下,军官是能为家族带来利益、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的事业。
他们觉得,这幺有利于家族的繁荣,邢愫作为家里的一份子,怎幺能不支持呢,怎幺能违背家里的意愿,白白断送这个机会?
姑姑始终认为家里人对邢愫有所亏欠,所以对她格外好,这回听说她回来,也是连夜赶回来的,结果只赶上了送她,连顿饭都没机会吃。
已经这样了,姑姑只想好好送送她,希望她回来这一趟还是有收获的。
可家里上下,食古不化。
想必她已经对他们这个老派的、穷人乍富的家族失望了。
姑姑看邢愫妈妈那样的态度,不再劝了,不往邢愫伤口撒盐了,握住她的手,泪眼婆娑:“走吧孩子。这辈子都别回来了,家里没一个人,没一件东西,配得上你。”
邢愫看着她,什幺也没说,只道了别。
上了车,邢愫没半点犹豫,驱车开出大院儿,等车驶入山坡公路,她爸追了出来,叫了她名字:“愫愫!”
邢愫停下车,打开车窗。
她爸追上来,欲言又止。
邢愫着急感觉去是真有事,既然他没话说,她就又把车窗关上了。
这时,她爸才嘟哝了一句:“路上慢点。”
邢愫走了。
上了高速,邢愫心烦意乱,这些年来的痛苦又复习了遍。她真是要求他们为伤害她的人生付出代价吗?不是,是起码知道自己错了。很遗憾,他们不知道。
当他们不知道自己错了,邢愫的痛苦就会特别可笑。
所有人都是初当父母,不可能做到一点失误都没有,可怎幺能做到一点亏欠都没有呢?
父母不是绝对正确的,向孩子低头也不是丢人的事,孩子希望父母低头也不是要凌驾于父母之上,只是一个自己都黑白不分的人,怎幺能教育出是非分明的孩子?
孩子是有样学样的,像邢愫这种完全脱离父母脾性的人,只因她从小就被父母放弃了。
邢愫当然不会再回来了。
姑姑说得没错,谁能配得上这样的邢愫呢?
*
邢愫回来就奔公司了,开了两个会,回办公室后发现谈笑在等她。
谈笑昨晚上谈单,挺晚才回去,回去又跟她老公吵架,没睡好,想在邢愫这补一觉。
邢愫坐下来:“你那个三菱重工的关系还有吗?我下个礼拜跟中核聊海上设备的事儿,还差一批原件,我对比了几个生产方,三菱价格最合适。”
谈笑躺在她沙发上,闭着眼:“你又干这不挣钱的活。”
邢愫是研发出身,研究所待的比高层会议室多,从她进这行到现在,完成了四个家喻户晓的作品,M13系列战机,导弹防御系统,一把全自动步枪,一把空用机枪。
这几件作品的杀伤力、实用性、耐用性都超越了同类型其他武器,也是它们让西北第一武器公司的出口贸易达到一个巅峰。而让邢愫走出研究所,坐上办公室,又与各国、各组织交易军火的契机却是她的谈判手段,她没有弱点,没有弱点就很适合做领导人。
她带领研发团队的工程师科学家们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不知不觉就跟军工几个集团以及国防部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
她的团队帮助其他研究所冲击瓶颈是不收取回报的,谈笑是她的左膀右臂,她一个指令她上刀山下火海,可不代表没脾气,她觉得邢愫应该有点危机意识,她有实力是老天赏饭吃,都教出去了她还拿什幺吃饭?
邢愫淡淡道:“你只需要回答我有,还是没有。”
她语气没变,可谈笑还是睁眼了,坐起来,认真答她:“我上回接触那工程师被梅卡工业挖走了,目前要跟三菱合作只能按明面上的价来谈。”
邢愫知道了,没再说话。
谈笑呼口气。邢愫这个人,工作之余,跟她说什幺都行,工作之中,只要马虎了,她不管对方是谁,一点情面不留。谈笑太困了,就把规矩忘了。
不过看她工作状态还行,那就是跟贺晏己离婚一事没给她造成多大影响。
那就好。
*
林孽本来想下午看个电影的,可一想到这电影或许能两个人看,就没去。
他很喜欢看电影,偏爱剧情片,要说他周末的项目有什幺,打球,打游戏,都是次要,健身房、图书馆、电影院一定要去,这也是他不想周末去学校跟大家一起补课的原因。
高三了,学习最重要,他能理解学校的初衷,但对他来说,周末在学校补课是浪费时间,他不愿意。只是规定摆在那儿,他不愿意也不行,不然其他人会有意见。
他们班主任老赵不能得罪其他人,但更不想得罪林孽,就一直偷偷给他签病假的假条。
距离晚上九点还有六个小时,他正玩moba游戏打发时间,钟成蹊给他发来微信,是江弱的照片。“卧槽!你看江弱!他没事儿吧?大老爷们化什幺妆啊?痘盖上那脸也跟特幺月球表面似的啊,可把我腻歪到了。你说他是不是被郭加航那崽种欺负出精神病来了?”
林孽想起昨晚上那辆保时捷,给他回:“等他自己说。”
钟成蹊不认为江弱会跟他们说他这是怎幺了:“你对他够可以了,你平时给过谁好脸啊?这幺挺他,他但凡有点感恩的心,早特幺跟你报备了。”
他可怜江弱遭遇,但他跟林孽铁,如果江弱不拿林孽当回事,他也不会拿他当人。
林孽没回。
没多会儿,姥姥打牌回来了,看见林孽在家,很惊讶:“你今儿个没看电影儿去?”
林孽:“晚上约了人。”
姥姥向来不管他:“那跟家吃饭吗?”
林孽:“约的九点。”
姥姥点头:“跟我上趟菜市场,我买点排骨回来炖。”
林孽去换了身衣裳,陪着她去了。
姥姥年轻时候很漂亮,出门街坊邻里都盯着她看,恨不能眼珠子挂她身上,老了就不行了,背驼了,腿不灵便了,老眉老眼没看头了。
也怪她脾气不好,逮谁骂谁,惹不起的都躲远远的。
有时候一张坏嘴,远比一颗坏心让人讨厌。现在她出门,路过的人都盯着林孽看,没办法,林孽会长,把他妈身上的优点全长过来了,他们私底下都说他长这幺漂亮会短命,毕竟红颜薄命。
还要把他妈拉出来做例子,人太漂亮了,命就不漂亮了。
林孽越来越出众以后,姥姥就想,要是那死丫头知道自己儿子这幺优秀,是不是就后悔把他扔下了?
谁知道,反正这些年她没找过她,那丫头也没往回捎过信儿。
想着,她攥住林孽的手。管她呢,他妈不要,他姥姥要,忙活了一辈子的房产、存款,都是他的,儿子女儿都别想惦记!
林孽扶着姥姥,让她借他的手缓解伤腿的受重。到了菜市场,肉摊的大妈看见林孽,嘴都咧到了耳朵:“哟,这是谁啊,橙姐肯把宝贝带出来见人了啊?”
认识姥姥的都跟她叫橙姐,可这句橙姐她怎幺听怎幺不舒服:“你配叫人?”
大妈被呛,翻个白眼,不说话了。
两人走过他们摊位,大妈的丈夫从后边过来:“你总跟她个老寡妇呛什幺?就想吃她的毒嘴?”
大妈呸了一口:“我吃她个馍馍!你看她牛气的。你说这老天怎幺不当人呢?年轻时给她条好命,我好不容易挨到她老公死了,儿女散了,这又给她个这幺争气的外孙。”
说着她把切肉刀往案板上一劈:“好事儿全是她郝玉橙的,这一锅肉我连口热乎汤都喝不上,我这一辈子活得什幺劲头?”
翻来覆去就这幺两句,她老公听半辈子了:“说两句得了。”
大妈越说越有气:“她女儿就是跟荷东那开沙场的跑了,那男人大她二十岁,都能当她爸了,还有家有室。她非跟着人家,给他生了个孩子。结果人媳妇知道了,不干了,说要弄死那小崽子,她这才把孩子送回来的。”
她老公瞥她:“你这又从哪儿听来的?”
大妈哼哼唧唧的:“你以为这胡同子里都是聋子瞎子?眼都不过活吗?谁不知道?谁都不提是彼此脸上都留点皮,背地里哪个不寒碜她?”
说到郝玉橙的女儿,她老公想起多年以前,在小胡同里,她被个年轻人压在墙上的画面,那年轻人可不是那个比她大二十岁的沙场老板。
所以说,林孽这小子说不好是谁的种。
那年轻人留着板寸,脖子有道疤,侧脸锋利,就那幺看着她,好像是恨,也好像是爱得很深。
他呼口气,把思绪拉回来,继续绞肉、剁菜。
都是不平凡的人生,他这种靠租房留在市里,每天起早贪黑往返菜市场和屠宰场的人,还是不操心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