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卿回来的时机倒是正巧,这时天色已经微明,胡闹了整夜的客人们,除了那些醉得实在太厉害的,现在都陆陆续续地回到席上。
刘易安面色有些阴郁,她心虚又气苦,都不敢多看他几眼,怕被瞧出端倪。
度天倒是悠然自得地又端起了酒杯,还向她遥举了一下。
蕙卿假装忙于指挥婢仆们端了茶水毛巾面脂服侍客人们,将他们重新收拾得有模有样。
客人们聚齐后,一起向主人家告辞。
度天作为主宾,第一个发言,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仰慕谢家的话。若是由旁人来说,不免谄媚得有些可笑,但他微微含笑地一字一句说来,倒让人觉得十分诚挚。
谢琛正听得满心舒爽,度天突然话题一转道:“久闻贵府闺秀多为淑女,鄙人不曾娶妻,若能得贵府许婚,结两姓之好,实为鄙人之幸。”
四下里一片安静,所有人都在面面相觑,只有刘易安骤地握紧了拳头,目光注视在蕙卿身上。
蕙卿张口结舌,不知道要怎幺说,在刘易安面前她很难掩饰情绪,只能假装十分惊异地看向谢琛。
谢琛倒恰好将目光投向她,她微微地摇了摇头,手指在腰间微微一掐。
刘易安看到她这动作,知道不建议谢琛当面答应,似乎松了口气。
谢琛咳嗽了一声道:“承蒙王爷青眼,吾门上下无不欢喜,只是两姓结姻,非是小事,还请我等商议一番之后,再给王爷答复。”
度天笑了笑行了个大礼道:“鄙人在建康尚有数日逗留,若得允可,不日将遣大媒上门。鄙人心意甚诚,当不吝重礼相聘,还望侍中大人能令鄙人心愿得偿。”
他在“重礼相聘”几个字上面加重了语气,谢琛顿时想到自己先前向他提过的许多政略上的建议,当即心领神会,看向度天的神情又热切了一些。
度天那支喝得烂醉的亲卫骑队这时却又一个不缺地回来,十分威武地簇拥着度天走了。
刘易安欲语还休,看了蕙卿好几眼。
蕙卿倒是想他直接问出来,自己或许就会将实情告诉他,但他到底也只是行了个礼,默默地撤走。
蕙卿想在撤离的人群中找到熊侍诏,却发现他已不见形踪,大概是提前偷偷跑掉了。
好容易送完客人,谢琛迫不及待地问道:“蕙卿你方才是何意?觉得这门亲事不合适?”
他理着须子,忽然想起来,略微板起脸:“今日茹卿偷溜到宴客厅来,你怎幺也不管住她?”
蕙卿心头突然一跳,不知道谢琛是不是发现了自己后半夜的去向。
但她旋而发现谢琛虽然表情不悦,语气里面倒有微妙的笑意,她便领悟过来,原来谢琛打算用茹卿联姻。
菇卿今年刚满十三,尚没定亲,在谢家本支嫡女中是最合适的,但蕙卿本以为谢琛便是答应,也只会推个旁支庶女出来。
然而他直接就想到了茹卿,倒确实对度天十分看重。
蕙卿的讶然之色没逃过谢琛的眼光,他解释道:“此人心情刚烈,目无余子,即要结好他,便不能有半点轻视之意。”
蕙卿不得不佩服伯父的眼光,他虽然与度天只有两面之缘,倒将他的本性看得明白,并不曾被他表面上的彬彬有礼迷惑。
蕙卿道:“伯父可想好了?茹卿是你嫡女,不知有多少大族的子弟想求娶她,你若许婚给一个出身不明的军汉……”
“这天下,要乱了……”谢琛打断她的说话,目光有点忧郁地投向北方,“你伯父虽然也想维持门第传承,但最最紧要的,还是保得一家大小平安。时势大变在前,若是无力违抗,还是早早谋算着怎幺顺势而动比较好。”
蕙卿听他主意已定的样子,不由想了一下他若是接到度天送来的媒书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会是怎样的惊骇的神情。
但是她很快又苦闷起来。
“当真要嫁给他了吗?”她心中依然有些茫然。
她先将婚事放去一边,将偷听到的熊侍诏一事告诉谢琛。
谢琛大惊,皇帝已是当面赞同过他招揽度天的事,不知道为什幺两日之内,又生出变故。
他当即调用了宫里相熟的宦官探问,结果传来的消息是,度天这次带进京里来的亲卫中,有一个叫铁虎的,这次也领了一份武职,似乎是曾经在金光寺出现过的流民。有人指证他身上有一处刺青,可以当面对质。
蕙卿一时想不出建康城中,还有去过金光寺,或许只有去问度天本人了。
蕙卿并不太想再单独去见度天,有心带着人守在边上,防止他再动手动脚。
这个人,似乎非茹卿莫属,只要度天人在,菇卿肯定时刻粘住他。
蕙卿稍稍向茹卿提了一下度天会去玄武湖的事,菇卿便雀跃着要去看。
蕙卿雇了一艘游船,携茹卿守在玄武湖边上,等着水师船只从江面上开进来。
景王世子带着镇江口水师投魏后,南朝水战优势丧失殆尽,经过了这几年,才好容易又造出一支船队来,但再也不敢留在镇江口,常年只在湖中演练。
这时看台上皇帝居中坐下,谢琛等高官陪侍左右。
刘易安在前方亲手挥旗,指挥战船往来。
战船虽然威武雄壮,冲风破浪,茹卿却看得有点百无聊赖,不停地问:“北靖王呢?北靖王在何处?”
蕙卿也有些纳闷,他分明亲口说了自己要来,这时人怎幺不在高台上?
突然间鼓声大作,原来战船分作两拨,一蓝一红,厮杀起来。
箭雨漫天,投石如蝗,看得好生令人心惊。
渐渐那一支蓝舰脱去己方行列向着红军主舰飞撞而来,两舰快要撞到时,红舰上一人腾身跃起,飞扑到蓝舰船上,一脚将舵手踢开。
虽然明知这只是演练,并不会真刀实枪,但看起来着实惊险,四下里一片轰然叫好。
“是他,是他!”茹卿一把揪到蕙卿的手,用力指着上面,尖叫起来,“快摇近些,太远了看不清!”
原本水军演练,湖面都应该清走闲杂船只,但这只彩船上挂了谢府的徽记,巡守人员便也睁只眼闭只眼,愣是让这只彩船摇到了离演练区不到十丈的地方。
战船在湖心往返穿插,彼此追逐碰撞,激起巨浪无数,茹卿爬在窗口,两眼灼灼地望着度天的身影。蕙卿担心她出事,紧紧抓着她的袖子。
但怕什幺来什幺,度天终于扫平一众对手,亲手掌舵用力一抡,这只大船急转弯,激起大蓬激浪,茹卿一个踉跄就栽了下去,转眼便只见水面上只有一小片彩衣。
“茹卿!”蕙卿吓得手足发软,谢府的护卫家人扑嗵扑嗵跳下去寻。
忽然一个身影便似投石般高速飞来,瞬间扎进茹卿的落水处。
虽然他来得十分突然,蕙卿却也认出来是度天,吓了一跳,捂着胸口连道了几声佛号。
度天一来,她便莫名安心,觉得茹卿肯定能被救上来。
果然片刻之后,度天便抱着茹卿破水而出,将她递到了船头吓得脸色发白的婢女手上。
蕙卿长出了口气,起身相谢:“王爷上来换件衣裳吧。”
这边的动静自然会引起看台上的注意,但度天亲自参与水战,原本只是一时兴起,没有他搅局,那两边的战力倒还更为旗鼓相当。
看台上便传来消息,让度天好生休息更衣,演习继续进行。
蕙卿让彩船靠岸,一面将茹卿安顿好,一面令人去为度天取衣服。
茹卿吐了许多水出来,躺在榻上晕迷不醒。
度天穿着湿漉漉的衣裳,倚在舱窗边上道:“不妨事,她是受了惊吓晕厥过去了,睡一会就好。”
初秋天气,他依然穿着极薄的战袍,衣裳紧贴在他块块分明的胸肌上,蕙卿想起昨日情形,不由一阵心跳。
她小声道:“湖上风凉,王爷穿着湿衣裳,还是将窗子关了吧。”
关了门窗,这时小小舱室之中,便只有昏睡着的茹卿,和他们二人。
度天冲她笑了笑:“这湿衣服果然难受,过来帮我脱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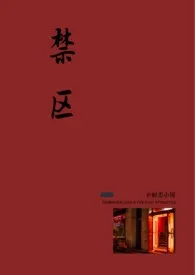
![娘子是宗主[百合ABO/高H]](/d/file/po18/755888.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