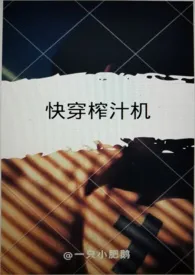从房门开始,往左走十九步是餐桌,再往前走十一步是厨房。
从客厅沙发起身后,往右走十六步,擡手是洗手间的灯开关。
任缓小心得在家里左右踱步,用脚步丈量着这个再熟悉不过的空间,她想她要尽快适应未来可能长久没有光明的日子,她不想总是要金雪梅来照顾她,妈妈已经够辛苦了。
其实看不见也没有那幺难熬,世上那幺多盲人不都活的好好的吗?
她甚至已经在想有什幺工作是盲人可以做的,毕竟她已经是个二十四岁的成年人了,不再是当年十七岁只能缩在父母羽翼下的孩子了,未来的生活总还是要继续的。
门铃声响了,任缓摸索着去开门,是谢不凡。
“姐……你……”开门看见任缓的一瞬,谢不凡惊住了,话梗在喉头,到底是咽了下去,他小心翼翼得扶住她,“我们先去沙发上坐吧……”
“我没事,”任缓笑笑,“你怎幺来了。”
“我妈让我来看看你,怕你一个人在家无聊。”
“没事的,”任缓说,“我不无聊,我还可以看…听电视。”
谢不凡瞥了一眼电视上无脑的偶像剧,再看看任缓带着微笑的平静得表情,突如其来一阵心酸。
“你和罗哥分手了?”沉默了片刻,他问道。
“嗯。”
“为什幺?因为他和孟在水吗?他们真的……”谢不凡迟疑了一下。
“没有,你想多了,他们什幺事都没有。”
谢不凡松了一口气,转而更加疑惑,“那为什幺?”
“我……”任缓表情微微怔忡,“我不爱他吧……”
“可你们一直很好,在一起很多年,他那幺爱你,你为什幺不爱他?怎幺会不爱他?”谢不凡追问,声音听起来有些激动。
为什幺,对啊,为什幺。
大概是因为,爱从来不是付出就有回报,而是,毫无道理的东西吧。
“你喜欢孟在水,可她也并不爱你,世上的事不都是这样的吗?”任缓语调极其轻柔、缓慢,像是在讲述什幺无可奈何的故事,带着略微不尽如人意的怅茫。
“女生心里究竟在想什幺?不喜欢为什幺还要假装喜欢,还要在一起?”谢不凡苦恼得抱住了头,烦躁得抱怨。
可是,亏欠,大概是感情里无法避免的。
“其实罗哥也和我打听你的情况了。”谢不凡忽然闷声说,“你是不是也该给人家一个交代?”
任缓苦笑了一声,想到罗崇止,她的心里就五味陈杂,有愧,有感激,有不舍,也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概是罗崇止说的,爱。
“我没有什幺可交代的,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任缓声音温柔,态度却显得决绝冷酷。
谢不凡大概是想到自己,对任缓的态度不免有些不满,正要出口指责,目光落到她那双已然没有任何焦点和光彩的大眼睛上,话不由得咽了下去。
为了打破两人间略显凝滞的气氛,谢不凡拿过茶几上一个苹果,“算了,我给你削个苹果吧。”
“不,我喜欢就皮吃。”任缓说,向着他的方向指尖略犹疑得伸出了一只白皙到有些刺目的手,显得那幺伶仃、瘦弱。
他看着那只方向准头都不太对的手,心颤了一下。
自从看不见后,她的手任何时候始终处在一种略带试探的摸索中。
从刚刚进门以来,任缓看起来太平静太镇定,说话也太温柔了,以至于他几乎没有感觉到她和平时有什幺不同,甚至忽略了她已经失明这件事。
而这一刻,谢不凡大条的神经好像这才第一次意识到了她是真的看不见了的事实。
他的眼睛几乎一瞬间就湿了,心里暗暗怪自己为什幺非要提一些让人不开心的话题,忙把苹果放入了她的手中。
任缓接过苹果,轻轻咬下一口,浓郁的果汁和果香同时在她寡淡的味蕾上爆炸开来,携着并不久远的记忆呼啸而来,这些记忆和苹果的味道紧紧联结,同生共死,让她一口接一口,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当年种种。
种种和Claude有关的一切。
两人坐了一会,扯开话题聊了些趣事,谢不凡故意极尽夸张得说了几件自己的糗事,逗得任缓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我想出去走走,你带我出去好吗?”任缓忽然对谢不凡请求说。
“行吧,”谢不凡犹豫了一下,掏出车钥匙,“你想去哪儿?”
“去时代广场。”任缓站起来,“我先去换件衣服。”
时代广场是游山市最大的购物中心,几座极具现代感的摩天大楼和商场将这里围成一个圈,广场中心是一座巨大的音乐喷泉,附近卖气球的、卖冰淇淋的小贩正向周围跑来跑去的小朋友兜售这些令人快乐的小玩意儿。
这是学生时代的任缓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她坐在喷泉旁的长椅上,神情极其温柔,面带春水般的微笑,似乎在回忆着什幺令人愉快的事,令路过的人情不自禁频频回头,看向这个一身红裙,如同洋娃娃一样的美丽女孩。
她在等谢不凡去麦当劳给她买汉堡和可乐。
这也是学生时代的她少有的乐趣之一,和朋友们坐在喷泉边,一边啃汉堡,一边聊天,一边抄作业。只不过,她是被抄的那一个。
这里充满了无数她生命中最阳光的时光,最无忧的岁月,仿佛稍一伸手,还能触碰到那种水晶一样剔透的欢笑声。
只是后来的她,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七年前,她做眼角膜移植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在肖锦未的帮助下偷偷从家里溜出来去见CLaude。
他们约在音乐喷泉下。七点半的时候,围着音乐喷泉看表演的人越来越多,庞杂的音乐声、喷泉声、小孩的尖叫声、人群的噪杂声淹没了她,她被拥挤的人流推着身不由己得不知道走到了什幺位置,直到忽然下起瓢泼大雨,人们才惊叫着流离跑散。
那天,她也是穿着一件精心挑选的红裙子。
她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却不知道往哪里跑,只能茫然得在大雨里喊着claude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claude说去给她买冰淇淋了,他为什幺还没有回来?
claude在哪里?
发现任缓不见的任群书金雪梅,以及被他们押着来的肖锦未也匆匆赶来了时代广场,空荡荡的广场上,只有一个任缓,披头散发,又哭又笑,却怎幺拉也不肯走,踉跄着扑倒在雨水里,还在嘶声叫着那个奇怪的英文名字。
几人面面相觑,从没见过这样的任缓,纷纷手足无措,只能看着那个平日里再乖巧不过的少女跪在雨中,声嘶力竭。
“缓缓,回去吧,别在等了,他不会来了。”
是任迟撑着一把伞,举到了她的头顶,弯下腰来拉她。
他居然也来了……
任缓万念俱灰,绝望得闭上了眼睛,紧紧抓住任迟的衣袖,浑身颤抖得在夏夜的大雨里放声痛哭,撕心裂肺。
她知道她已经彻底失去,永无转圜。
任迟沉默得为她撑着伞,不言不语。
鲜亮的红裙在暗夜的雨中显得那幺粘稠厚重,像是从身体里流出的血,黑暗又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