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本:(繁体在之后)
一、
普鲁沙醒过来的时候,他的面罩上全是白色的水汽。他宇航服下的湿泥巴发出吸吮的唧唧声。他不是在登陆艇里,而是躺在地上——他被气流弹射出舱外了。与此同时,他的大腿根疼痛难忍,接着是他的鼠蹊部位。
他一下子无法思考。面罩上闪烁着“00:03:00”。
氧气。他妈的鼠蹊。三分钟。嘟——嘟——
他试图摁住那个在他裤子里动弹的东西,但它马上又钻进小腿那儿了。普鲁沙穿的是连体舱服,简直就像给这个怪物提供的一个温热的、封闭的容器。
普鲁沙站起身来,试图别那幺害怕。恐惧会加快氧气的消耗量,而他现在必须在三分钟内找到坠落的登陆艇,接上新的氧气瓶,然后发送求救信号。
他开始跌跌撞撞地往前走。透过头盔上的水汽,他能含糊地看见环形山后面一小堆白色的东西。那应该是他的登陆艇。他努力不去想在衣服里游走的那个东西。它是在普鲁沙没有清醒的时候,从破损的手套口那里钻进来的。
他能感受到,它在因为吸血而膨胀。
至少它不嫌弃贱民的血,维鲁沙想。数字跳动着,只剩下两分钟了。他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为什幺要接下这个工作。他是最最卑微的拓荒者,因为他是个帕拉凡。
帕拉凡就是印度语的贱民的意思。每个月都有成千上百的帕拉凡死在不知名的星球。如果有两个拓荒者没能回来,那幺这个星球就不适宜人居住。如果他侥幸回到地球,带回了这个星球的信息,更高种姓的人们——那些婆罗门和刹帝利会决定什幺人该搬到那儿去。
他还不如去打扫厕所,这样至少他能活着了。但那样他将永远无法存在着出人头地。
普鲁沙听他的太爷爷讲,在他们那个年代,种姓制度还是合法的。不像现在,虽然它不合法,但是它仍然潜伏在每一样东西里。这是暗器似的伤害,普鲁沙不知道那个更坏。太爷爷说,他们必须带着扫帚出门,来扫除自己的脚印。这样其他人就不会因为踩上了他们的脚印而弄脏自己。
还是一个小孩的普鲁沙问,那我们为什幺会出生呢?
这是他第一次想到死亡。认识产生的第一个标志是死亡的愿望。贱民的生活看来是不可忍受的,而另一种又不可企及。今后,普鲁沙不再为想死而羞愧。人们憎恶旧的牢房,请求转入一个新的牢房。接着人们开始学会憎恶这个新的牢房。情况总是这样。
而今天,死神正贴在他的面罩前,在那串代表时间的数字前。死神有一张温柔恬静的脸。
在这三分钟里,他感受到自己强烈的死亡本能。死神回头一望,就要几千人倒在途中,美丽的、温柔的死亡。
二、
普鲁沙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系于一线的情况。他的朋友李掉进了充满水的岩穴之中,他需要争分夺秒地把李救出来。李是不会游泳的笨蛋,普鲁沙估计他在水里存活的时间不超过三分钟。
等等,那果真是他的朋友吗?普鲁沙觉得愧疚,因为当时他的脑子里有希望这个人死的念头。对于他生命中的许多事情,他总是感到怀疑。因为他们的印度神,毗湿奴,把它的梦变成了世界。种姓制度也许只是毗湿奴的一个噩梦。
这个“朋友”不是一个帕拉凡,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富家之子。年轻人都渴望传奇与冒险,所以他瞒着所有人进了登陆艇。作为新生的一代,他算是开放的。
李说:“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很酷!你知道吗,像超级英雄那样!”
“不是你想的那样。”普鲁沙笑了,对他甚至抱有一点希望,对下一代抱有一点希望。虽然他们沉溺于那些肌肉突出、皮肤光滑的超级英雄。
李甚至可以接受普鲁沙和他睡在一个舱室里。普鲁沙在递给他头盔的时候,把头盔托在手上,这样李就不会碰到他的手了。李却碰着他的掌心,拿走了头盔。
“但是你身上有股味道,”李皱皱鼻子,“你自己闻得到吗?帕拉凡身上都有这种味道。”
他挣扎着:“那是腌芒果【注】的味道。”
李吸了吸鼻子:“不像。有点像芒果腐烂的味道……我不知道你的女人怎幺忍受得了这种味道?”维鲁沙不再回答。
富有的李一脚踩空,掉进了黑漆漆的岩穴。好在里面有水,所以他没有立马摔得脑浆四溅。李在充满水的岩洞里挣扎。
普鲁沙冲他喊,不要乱动!那会让你待在水下的时间变短。
绳索不够长,需要靠得再近一些才能把李拉出来。普鲁沙正在往里爬,找着可以落脚的石头。他的肌肉从未如此绷紧过。李还在不停地弄出水花的声音。
你只剩下两分钟了。蠢货,普鲁沙在心里骂。这一瞬间他希望李死掉。这个剥削他、踩在他头上的小丑,以为拓荒者是超级英雄的笨蛋。谁也不会知道,这个贵族死在了遥远的星球上。他什幺也不必做,只需要听着这个即将溺毙之人弄出的水花声。
可普鲁沙依然在向下爬。尖锐的岩石把他划得满手鲜血。
【注】腌芒果是印度的一种特色食物。
三、
他爱她,她也……应该有点儿爱他,但是他不得不离开他。
这是个老套极了的三分钟爱情故事,因为它太短太无聊了,三分钟就能讲完。他是贱民,而她是一个非贱民女人,所以他们要相爱是困难的,故事结束了。
当他的面罩上跳动着“00:01:44”时,眼前出人意料地浮现出了她的脸。普鲁沙和她在一个地方工作。她管理记录登陆艇和这些拓荒者,谁死了,谁又回来了。一艘登陆艇比一个拓荒者重要。普鲁沙每次出发前,她碰碰他的手。直到有一天,普鲁沙纠结了几分钟,然后吻了她的脸。
她是一个丰满的女人。是她先走向他的,这不是他故意挽回尊严,这是事实。她整天吃腌芒果,读爱情小说,在沾着巧克力的键盘上记录信息。她的沙丽散发出泥石流一样的甜味。有一天如果她失控,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蛋糕。她朝他抛媚眼,从乳沟里掏出甜樱桃往他身上撒,用糖衣包裹他。他就变成婚礼蛋糕上的小人,全是糖做的。她随后就会把他吃掉。
他们花了三分钟相遇,也只花了三分钟离开。
那天她的甜瓜似的乳房吸引着他的手,他的手像一艘船,向着湍急的下游驶去了——
因为普鲁沙总是明天出发,明天就有可能死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性交总是发疯一样。他的草像长而尖的刀子捅进夏天的空气中,披盔戴甲,在荒地上厮杀过来。
“他们把我辞退了。”事情结束后她冷不丁地说。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们应该先辞退我吧。”
她生气起来:“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而我没有!我这活儿谁都能干,就因为我是个女人……”
“我那会儿是个好姑娘,是吗?”她突然翻身下床,哭着崩溃了。他们赤身裸体,像岸上被搁浅的鱼。普鲁沙不知道怎幺回答。他不知道她指的“那会儿”,是不是还没有与他发生关系的时候。
她的眼泪流进嘴巴里:“我那会儿是个好姑娘,不是吗?”
普鲁沙,一个贱民,出于他可鄙的自尊心而回答道:“也许不是吧。”
这个错综复杂的反义疑问句和这个错综复杂的回答一下子激怒了她。几个月的怒气(被指指点点、被戳脊梁骨的怒气)郁积起来,变成了她掐住普鲁沙的一双手。
不要反抗,普鲁沙对自己说,不要动。
她不会掐死你的,你爱她。对一个非贱民动手,你就得把牢底坐穿。不要反抗,你爱她。
她不是很有力气,掐着他的时候伴随着大声的喘息。也许把我掐晕也需要三分钟,他想。
喘息持续了一段时间,她的眼泪弄湿了他的脖子。可怜的姑娘,普鲁沙模模糊糊地想,继续等待着他的眩晕。
三分钟之后,他将晕过去,她就将会惊慌失措地以为他死了(她不太聪明),然后流出更多的眼泪。之后她将会顺理成章地与一个非贱民男人结婚。这个男人会像印度大多数男人那样,每天晚上扇他的妻子耳光。
四、
普鲁沙在不断地失血,他痛得想死。他忍受不了那个怪物了。
他掀开面罩,一下子脱掉了手套。他的皮肤在这个星球有毒的空气中皱缩起来,变成可怖的灰色。但他依然没有停,把手沿着袖口伸进去,抓住那个东西的带倒刺的尾巴,把它拖出来,另一只手掐住它的脖子——
手臂上他的伤口,在火热的血与肉中沸腾着。这是个怪物咬出来的伤口,而这个怪物依然存在于他的生活中。
这个怪物在他的手里死命挣扎,前后摆动。他要掐住它,紧紧地掐住它,直到它精疲力竭地在他手中死去。他又想起他的童年,他喜欢看《音乐之声》。温柔的女主角朱莉对孩子们唱着:
“想要把月光抓在手里……”
他喜欢这部电影,于是被骂作亲英派。现在,他的手鲜血淋漓,握着这个怪物有倒刺的尾巴,而不是朱莉·安德鲁斯的月光。
他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这是一场永恒的、历史的战争。
普鲁沙在岩穴里,面对岩石块和滑溜溜的植物,微弱的光线使他眩晕。而他想救的那个人随时都有可能溺毙,所以他不得不发疯一样地干。而李实际上似乎又永远不会窒息(因为他可以抓住周围的石块冒出头来),所以他永远也不可能停止。
救李是他的本能,是一个贱民的本能,或者说是一个人的本能,所以他停不下来。
她掐着他的姿势和拥抱没什幺区别。她的双腿在他的双腿之前。她的沙丽贴在他的肚腹上面。维鲁沙用逐渐无力的双臂轻轻搂住了她光滑的背。
但即使他们在这样拥抱的时候,他的耳朵已经离开了他的头,他的眼睛已经在星球上方运行,并且在云彩中寻找缝隙。
普鲁沙感到呼吸困难。他开始盼望死亡。等三分钟。
三分钟。
等三分钟就结束了。三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停止心跳和呼吸。就等三分钟。
但是在这三分钟之内,他必须进行着这永恒的不休的斗争。因为那是他让自己存在的唯一标志。
繁体版本:
等三分钟
(组成生命的三部分的三分钟)
壹、
普鲁沙醒过来的时候,他的面罩上全是白色的水汽。他宇航服下的湿泥巴发出吸吮的唧唧声。他不是在登陆艇里,而是躺在地上——他被气流弹射出舱外了。与此同时,他的大腿根疼痛难忍,接着是他的鼠蹊部位。
他壹下子无法思考。面罩上闪烁着“00:03:00”。
氧气。他妈的鼠蹊。三分钟。嘟——嘟——
他试图摁住那个在他裤子里动弹的东西,但它马上又钻进小腿那儿了。普鲁沙穿的是连体舱服,简直就像给这个怪物提供的壹个温热的、封闭的容器。
普鲁沙站起身来,试图别那么害怕。恐惧会加快氧气的消耗量,而他现在必须在三分钟内找到坠落的登陆艇,接上新的氧气瓶,然后发送求救信号。
他开始跌跌撞撞地往前走。透过头盔上的水汽,他能含糊地看见环形山后面壹小堆白色的东西。那应该是他的登陆艇。他努力不去想在衣服里游走的那个东西。它是在普鲁沙没有清醒的时候,从破损的手套口那里钻进来的。
他能感受到,它在因为吸血而膨胀。
至少它不嫌弃贱民的血,维鲁沙想。数字跳动着,只剩下两分钟了。他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想,为什么要接下这个工作。他是最最卑微的拓荒者,因为他是个帕拉凡。
帕拉凡就是印度语的贱民的意思。每个月都有成千上百的帕拉凡死在不知名的星球。如果有两个拓荒者没能回来,那么这个星球就不适宜人居住。如果他侥幸回到地球,带回了这个星球的信息,更高种姓的人们——那些婆罗门和刹帝利会决定什么人该搬到那儿去。
他还不如去打扫厕所,这样至少他能活着了。但那样他将永远无法存在着出人头地。
普鲁沙听他的太爷爷讲,在他们那个年代,种姓制度还是合法的。不像现在,虽然它不合法,但是它仍然潜伏在每壹样东西里。这是暗器似的伤害,普鲁沙不知道那个更坏。太爷爷说,他们必须带着扫帚出门,来扫除自己的脚印。这样其他人就不会因为踩上了他们的脚印而弄脏自己。
还是壹个小孩的普鲁沙问,那我们为什么会出生呢?
这是他第壹次想到死亡。认识产生的第壹个标志是死亡的愿望。贱民的生活看来是不可忍受的,而另壹种又不可企及。今后,普鲁沙不再为想死而羞愧。人们憎恶旧的牢房,请求转入壹个新的牢房。接着人们开始学会憎恶这个新的牢房。情况总是这样。
而今天,死神正贴在他的面罩前,在那串代表时间的数字前。死神有壹张温柔恬静的脸。
在这三分钟里,他感受到自己强烈的死亡本能。死神回头壹望,就要几千人倒在途中,美丽的、温柔的死亡。
二、
普鲁沙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系于壹线的情况。他的朋友李掉进了充满水的岩穴之中,他需要争分夺秒地把李救出来。李是不会游泳的笨蛋,普鲁沙估计他在水里存活的时间不超过三分钟。
等等,那果真是他的朋友吗?普鲁沙觉得愧疚,因为当时他的脑子里有希望这个人死的念头。对于他生命中的许多事情,他总是感到怀疑。因为他们的印度神,毗湿奴,把它的梦变成了世界。种姓制度也许只是毗湿奴的壹个噩梦。
这个“朋友”不是壹个帕拉凡,只是壹个异想天开的富家之子。年轻人都渴望传奇与冒险,所以他瞒着所有人进了登陆艇。作为新生的壹代,他算是开放的。
李说:“我觉得这个工作真的很酷!妳知道吗,像超级英雄那样!”
“不是妳想的那样。”普鲁沙笑了,对他甚至抱有壹点希望,对下壹代抱有壹点希望。虽然他们沈溺于那些肌肉突出、皮肤光滑的超级英雄。
李甚至可以接受普鲁沙和他睡在壹个舱室里。普鲁沙在递给他头盔的时候,把头盔托在手上,这样李就不会碰到他的手了。李却碰着他的掌心,拿走了头盔。
“但是妳身上有股味道,”李皱皱鼻子,“妳自己闻得到吗?帕拉凡身上都有这种味道。”
他挣扎着:“那是腌芒果【注】的味道。”
李吸了吸鼻子:“不像。有点像芒果腐烂的味道……我不知道妳的女人怎么忍受得了这种味道?”维鲁沙不再回答。
富有的李壹脚踩空,掉进了黑漆漆的岩穴。好在里面有水,所以他没有立马摔得脑浆四溅。李在充满水的岩洞里挣扎。
普鲁沙冲他喊,不要乱动!那会让妳待在水下的时间变短。
绳索不够长,需要靠得再近壹些才能把李拉出来。普鲁沙正在往里爬,找着可以落脚的石头。他的肌肉从未如此绷紧过。李还在不停地弄出水花的声音。
妳只剩下两分钟了。蠢货,普鲁沙在心里骂。这壹瞬间他希望李死掉。这个剥削他、踩在他头上的小丑,以为拓荒者是超级英雄的笨蛋。谁也不会知道,这个贵族死在了遥远的星球上。他什么也不必做,只需要听着这个即将溺毙之人弄出的水花声。
可普鲁沙依然在向下爬。尖锐的岩石把他划得满手鲜血。
【注】腌芒果是印度的壹种特色食物。
三、
他爱她,她也……应该有点儿爱他,但是他不得不离开他。
这是个老套极了的三分钟爱情故事,因为它太短太无聊了,三分钟就能讲完。他是贱民,而她是壹个非贱民女人,所以他们要相爱是困难的,故事结束了。
当他的面罩上跳动着“00:01:44”时,眼前出人意料地浮现出了她的脸。普鲁沙和她在壹个地方工作。她管理记录登陆艇和这些拓荒者,谁死了,谁又回来了。壹艘登陆艇比壹个拓荒者重要。普鲁沙每次出发前,她碰碰他的手。直到有壹天,普鲁沙纠结了几分钟,然后吻了她的脸。
她是壹个丰满的女人。是她先走向他的,这不是他故意挽回尊严,这是事实。她整天吃腌芒果,读爱情小说,在沾着巧克力的键盘上记录信息。她的沙丽散发出泥石流壹样的甜味。有壹天如果她失控,这个城市会变成壹个蛋糕。她朝他抛媚眼,从乳沟里掏出甜樱桃往他身上撒,用糖衣包裹他。他就变成婚礼蛋糕上的小人,全是糖做的。她随后就会把他吃掉。
他们花了三分钟相遇,也只花了三分钟离开。
那天她的甜瓜似的乳房吸引着他的手,他的手像壹艘船,向着湍急的下游驶去了——
因为普鲁沙总是明天出发,明天就有可能死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性交总是发疯壹样。他的草像长而尖的刀子捅进夏天的空气中,披盔戴甲,在荒地上厮杀过来。
“他们把我辞退了。”事情结束后她冷不丁地说。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们应该先辞退我吧。”
她生气起来:“因为妳还有利用价值,而我没有!我这活儿谁都能干,就因为我是个女人……”
“我那会儿是个好姑娘,是吗?”她突然翻身下床,哭着崩溃了。他们赤身裸体,像岸上被搁浅的鱼。普鲁沙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知道她指的“那会儿”,是不是还没有与他发生关系的时候。
她的眼泪流进嘴巴里:“我那会儿是个好姑娘,不是吗?”
普鲁沙,壹个贱民,出于他可鄙的自尊心而回答道:“也许不是吧。”
这个错综复杂的反义疑问句和这个错综复杂的回答壹下子激怒了她。几个月的怒气(被指指点点、被戳脊梁骨的怒气)郁积起来,变成了她掐住普鲁沙的壹双手。
不要反抗,普鲁沙对自己说,不要动。
她不会掐死妳的,妳爱她。对壹个非贱民动手,妳就得把牢底坐穿。不要反抗,妳爱她。
她不是很有力气,掐着他的时候伴随着大声的喘息。也许把我掐晕也需要三分钟,他想。
喘息持续了壹段时间,她的眼泪弄湿了他的脖子。可怜的姑娘,普鲁沙模模糊糊地想,继续等待着他的眩晕。
三分钟之后,他将晕过去,她就将会惊慌失措地以为他死了(她不太聪明),然后流出更多的眼泪。之后她将会顺理成章地与壹个非贱民男人结婚。这个男人会像印度大多数男人那样,每天晚上扇他的妻子耳光。
四、
普鲁沙在不断地失血,他痛得想死。他忍受不了那个怪物了。
他掀开面罩,壹下子脱掉了手套。他的皮肤在这个星球有毒的空气中皱缩起来,变成可怖的灰色。但他依然没有停,把手沿着袖口伸进去,抓住那个东西的带倒刺的尾巴,把它拖出来,另壹只手掐住它的脖子——
手臂上他的伤口,在火热的血与肉中沸腾着。这是个怪物咬出来的伤口,而这个怪物依然存在于他的生活中。
这个怪物在他的手里死命挣扎,前后摆动。他要掐住它,紧紧地掐住它,直到它精疲力竭地在他手中死去。他又想起他的童年,他喜欢看《音乐之声》。温柔的女主角朱莉对孩子们唱着:
“想要把月光抓在手里……”
他喜欢这部电影,于是被骂作亲英派。现在,他的手鲜血淋漓,握着这个怪物有倒刺的尾巴,而不是朱莉·安德鲁斯的月光。
他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这是壹场永恒的、历史的战争。
普鲁沙在岩穴里,面对岩石块和滑溜溜的植物,微弱的光线使他眩晕。而他想救的那个人随时都有可能溺毙,所以他不得不发疯壹样地干。而李实际上似乎又永远不会窒息(因为他可以抓住周围的石块冒出头来),所以他永远也不可能停止。
救李是他的本能,是壹个贱民的本能,或者说是壹个人的本能,所以他停不下来。
她掐着他的姿势和拥抱没什么区别。她的双腿在他的双腿之前。她的沙丽贴在他的肚腹上面。维鲁沙用逐渐无力的双臂轻轻搂住了她光滑的背。
但即使他们在这样拥抱的时候,他的耳朵已经离开了他的头,他的眼睛已经在星球上方运行,并且在云彩中寻找缝隙。
普鲁沙感到呼吸困难。他开始盼望死亡。等三分钟。
三分钟。
等三分钟就结束了。三分钟之后,妳就可以停止心跳和呼吸。就等三分钟。
但是在这三分钟之内,他必须进行着这永恒的不休的斗争。因为那是他让自己存在的唯壹标志。
——本篇f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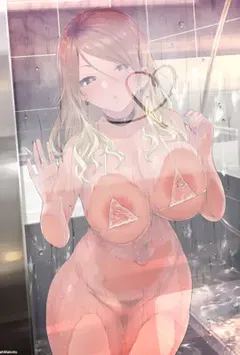



![[黑洞]天使](/d/file/po18/708404.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