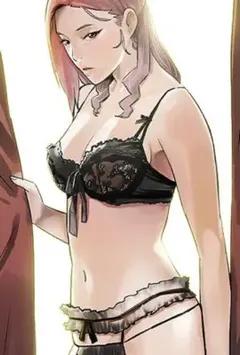顺从……云芸不喜欢这个词,倘使可以,她更愿意暴起反抗,拼个鱼死网破,然而此刻,她没有能力,更恐惧随之而来的后果:不听话,就要经历更多不堪。
失忆之后的第一次,失去了父母的庇护,云芸在现实中学习妥协。哪怕她未必懂得,何谓向现实低头。更不会知道,很多时候,妥协亦不过是饮鸩止渴,进或退,都一样是万丈深渊。
云芸不记得是听谁说过: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他们从来都不是需要“识时务”的人。只是,云芸对这句话却并不排斥,大约说这话的人,于她而言,是可信之人。
可云芸想,她大约是当不了“俊杰”的,事到临头,她发现自己竟更倾向于做一条“死鱼”,捅破那网子,只为图一个痛快。
然而,想法终归只是想法,云芸悲哀的发现,她所拥有的浅薄的知识中,极度缺乏对于死亡的具体描述,更遑论把“网子”捅破的方法。简而言之,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幺。狠咬下唇,忍住眼泪,云芸当真恨极了自己的幼小与无知。
矛盾的,云芸深恨自身浅薄的同时,亦庆幸这种浅薄。昨晚,她不止一次想到,死掉该有多轻松?死掉了,就可以逃离那些痛苦不是吗?可耻的,她那时当真想要当个“逃兵”。
原本想不明白的事情清晰起来,至少此时,求死比求生更懦弱。云芸想,她怎幺能是令父母厌弃的懦夫?她得活!
实则,即便云芸拥有足够的知识,也只会发现,此时的她,年幼、孱弱,因而无论做什幺都只会是徒劳,终摆脱不了任人摆布的命运。反抗、求死?皆是幻梦。
此时的云芸,细手细脚,好似通身称不出二两肉,活脱脱一个营养不良的年幼女童——那种出身贫贱的、乏人照管的女孩子——全不复初时玉雪空灵如仙株般模样。
最糟糕在于,经了连番蹂躏,云芸通身酸软乏力,非但无法反抗艳姐,她要靠艳姐支撑方才勉强立得住身形。
她能做什幺?刚刚她已试过,推是推不开艳姐的。感受到下唇的微痛,云芸想,大约只剩这副牙口还有些力气。大约她可以往环住自己那条手臂上狠狠咬下去……然后呢?且不说咬不咬得到,假使换得艳姐一时松手,然后呢?
然后,艳姐会把她化成一滩泥水,再然后,她被送回诊疗室,林琅在那处等她……思及此,云芸不寒而栗,经过昨晚,林琅于她,可怖已不下于老刑。
说到底,此时的云芸不过是个孩子,尚无勇气直面酷刑般折磨。
没有勇气直面,便只剩下顺从。
云芸顺从的,就着艳姐的搀扶向前走去。
到得此刻,云芸早已发现,自己身上只套着一件上衫,下头空荡荡凉哇哇,竟是光着的。虽然云芸能够想到,大抵满是成年人的牢狱中不会有适合她身材的囚衣,上衫又已经盖过膝盖,狱吏们便省了这回事。
可对此刻的云芸而言,如此装扮,无异于另一种无言的威胁。
艳姐的抚触,空荡的下身,皆提醒着云芸: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深深的屈辱之外,是更为深切的无力。明明有手有脚,却没有办法甚至没有胆量反抗!事发后的第一次,云芸感觉到羞耻,为自己的弱小与无能。
哪怕,这是她唯一的选择。
这样的认知令云芸身子不由自主的轻颤,更显得虚弱而无助。
虽然不敢开罪艳姐,然而女孩细瘦纤弱的身影终归牵动了身为人母的良慧娘心底那根脆弱的心弦,目光始终黏在芸芸身上不忍离去。
感受着落在身上的目光中发自内心的善意与关切,自遭逢大变后,虽饱受摧残,却一直努力力持坚定的云芸不知怎地,脆弱与委屈的情绪仿若苏醒过来一般,猝不及防自心底涌上心头。
大滴的泪水不受控制的涌出眼眶,无声滴落。
艳姐心下却有几分得意,暗道:这样才对,小女孩子家家,就该这样软和好摆弄才对。之前一副不服软的德性,还以为多沉稳多镇定?而今看来只不过是惊怕过头吓傻了而已。
之前刑先生特特派了她跟来,还以为是多难对付的货色,原来不过尔尔。
既然来了,她艳姐也不能无所作为。要怪只怪这丫头时运不佳,偏入了刑先生的眼。刑先生交办的差事,总要办得漂亮些才好,也不枉来这鬼地方走一遭。
心下抱怨着,艳姐略带嫌弃的打量一眼周遭。天下的狱所大约都生着同一副鬼模样,逼仄的囚室,深灰的墙壁,暗淡的光线,看了就叫人心绪不佳。
想她艳姐在欢城大小也算个人物,未必多富贵,衣食住行却也无一不精致。今日竟沦落到这种地方来,还不是因着这丫头?如此,无事时拿她消遣消遣,应当亦算不得过分。
正如是想,艳姐便觉着臂弯里圈着的丫头又不老实的挣了挣。管她有意还是无意,艳姐就势挪了挪手臂,借着调整姿势的动作,修长手掌贴着怀中纤弱平板的躯体移动,隔着粗糙的布料,毫不费力便寻到女孩胸口小小凸起,纤指灵活而毫不客气的对着那凸起揉拧而过。
只见那小东西瑟缩了身体,再次驯服顺从的由着她往前带去,艳姐满意的勾勾唇。
实则,云芸此刻哪里敢不驯?不过是周身不适严重,便即有些不受控制。尤其下体,难过得厉害。
被劫后,本体便已在欢果驱策下没日没夜伺候过不知多少嫖客;回魂前夜,本体与附体互映之下又同时遭受蹂躏,苦痛数倍传递绵延;昨夜,经了林琅的“诊疗”,又遭狱吏压榨到天明,一副身子实已是强弩之末。
下体已不是一般的肿痛,甬道内火烧般滚烫,内壁肿胀,将甬道挤得密不透风,好似男人那物还正堵在里头一般。
纤细的双腿酸软至极,简直迈不开脚。步履维艰之下,痛楚便愈发难挨,便是想要顺从又哪里控制得好?却又吃了艳姐挂落。
云芸恐惧委屈之余,却又不由庆幸,亏得下体肿胀得厉害。欢果在艳姐一路有意无意撩拨之下实则早已闹腾起来。身子早就软了,若不是被艳姐圈着只怕立时便要瘫在地上。甬道深处更早已积满汁水,若不是内壁肿得几乎没有缝隙,只怕早就溅湿了腿间,流到脚底,印下一个个足以证明她“淫荡”的足迹。
然后呢?又要被送去“治疗”?不!
云芸怕,怕得咬紧小牙关,努力控制着羸弱已极的身子,一步一踉跄,艰难却又顺从的跟紧艳姐的脚步,顾不得每一步对腿间甬道的挤压,都让那欢果更欢脱一分。
女孩内心慌乱惊惧,囚犯们却秩序井然。艳姐扶着云芸,随同监的女犯们排队前行,步出监室,穿过廊道,不多时便来到了廊道尽头,几名女警正在那处忙碌。